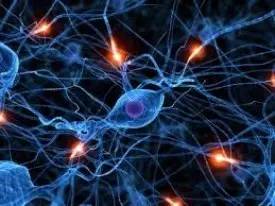本文涉及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汉代的复仇,一是汉代的经、律关系。两者都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倍受瞩目的显题,直接或间接的讨论更仆难数。这里之所以旧话重提,目的在于将这两个问题综合研究,或可补先贤之未备。
一
关于汉代的复仇,上个世纪日本学者牧野巽的研究论文值得特别指出,并应给予高度评价。正如牧野氏提供的材料所显示:汉帝国对待复仇的态度非常矛盾,并且在整个两汉时期,帝国始终都在这矛盾的两端之间盘桓。一方面,国家法典对于复仇是禁止的,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出于复仇的目的杀伤人和出于其他目的杀伤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都是对国家暴力垄断的蔑视,自然也都是违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另一方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被官方认可为“大经大法 ”的传世儒家经典之中,支持和同情复仇的文字却又随处可见。汉代复仇的盛行自然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和社会结构上的原因,然而经典文字的支持,却也是使复仇成为风俗并迫使法律让步的不可或缺的依托。
在两汉,真正从同情民间身份关系的立场出发,给复仇风俗以支持的,是《春秋公羊传》学的见解。
《春秋公羊传》本文,讲到复仇的共有5处,即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薨”条、鲁庄公四年夏“纪侯大去其国”条、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条、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条和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囊瓦出奔郑”条。这些传文都给复仇以不同程度的褒奖,是汉代人为自己复仇行动寻找根据的主要来源。但是,经典本文是一回事,汉代人具体的理解又是一回事。
不妨先看一则事例,《后汉书》卷83《逸民·周党传》:
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 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周党复仇的事发生在西汉末年,此事流播广远,并且到了东汉仍然有人在传说。这里引人注意的是他复仇的依据。据本传记载,说是因为“读《春秋》,闻复仇之义”的缘故。对此,章怀太子节引《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夏齐襄公为九世祖哀公复仇的事例,作了如下的注释:“《春秋经》书 ‘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齐襄公九世祖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也,故襄公仇于纪。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根据《公羊传》的说法,齐襄公九世祖哀公,由于纪侯的谗言,被周天子懿王烹煮而死,后来齐襄王为哀公报仇。《公羊传》对此持赞赏的态度,在章怀太子看来,周党正是因为《公羊传》的这种赞赏态度,才找昔日的仇人也就是乡佐复仇。章怀太子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错误的理由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公羊传》紧接着“虽百世可也” 还有这样一段下文:“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简单来说,据《公羊传》,所谓复九世仇云云,只能适合于诸侯国之间,次于诸侯国的大夫、卿尚且不可,身为庶人的周党自然更加不可。况且,周党本传所说的只是因为己身受辱而找乡佐报复,不牵连他的先人,和复九世仇也毫不相干。
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了章怀注的这个缺陷,所以后来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注“乡佐服其义”的时候,采纳惠栋的意见,援引了另外一个说法:“案《春秋》之义,‘复仇以死,败为荣 ’,故乡佐服其义也。义见何氏《公羊》。”确如惠氏所说,所谓“复仇以死,败为荣”, 正出自东汉著名《公羊》学家何休。何休是在注《公羊传》庄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条时说这番话的。
但即便惠栋之说符合周党本人的实际,其实也与经义不合,理由见于应劭《风俗通义》卷4《过誉篇》,“《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仇者,谓为父兄耳,岂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远《春秋》之义,殆令先祖不复血食,不孝不智,而两有之,归其义勇,其义何居?”应劭对周党的作法大不以为然,认为他的举动非但与出于身份认同复仇的儒家理念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他在报复乡佐的过程中身受重创,险些令父母绝嗣,反而是不孝的表现。他引据《春秋》复仇之义为说,为自己的违法举动掩饰,完全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应劭的这个见解,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牵强附会处,周党复仇的故事仍被广泛传颂,后来,甚至还有人将之拿来作为为亲属复仇辩护的依据。《后汉书》卷52 《申屠蟠传》:
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旌表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
同县大女缑玉为从父报仇,杀夫之从母兄李士,姑执玉以告吏也。
(杜预)《女记》载蟠奏记于县曰:伏闻大女缑玉为父报仇狱已决,不胜感悼之情,敢陈所闻:昔太原周党感《春秋》义,辞师复仇,当时论者犹高其节。况玉女弱,耳无所闻,心无所激,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奋发怒之心,手刃剌仇,僵尸流血。当时闻之,人无勇怯,莫不强胆增气,轻身殉义,攘袂高谈称羡。今闻玉幽执槛,罪名已定,皆心低气沮,怅怅长叹。蟠虽愚味,以为玉之节义,历代未有,足以感无耻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时,尚望追旌闾墓,显其后嗣,况事在清听?不加八议哀矜之贷,诚为朝廷痛之也。
尽管周党复仇的事情与《公羊传》阐发的复仇原理全不相干,但仍被申屠蟠拿来作为请求减免缑玉罪责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竟然得到了乡党舆论——用上引史料的话说就是 “乡人”、“当时论者”和“ 当时”——的“称美”,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可见,后世的人们走得更远了。
由周党复仇的事例及其引发的后果,人们不难看出,《公羊传》的复仇原理一方面鼓动了民间的复仇,另一方面,民间的复仇实践又扩张了《公羊传》复仇原理的内涵。因此,正如上文业已指出的,关键不在于经典本身的内容如何,而在于当时人的理解如何。人们关心的只是《公羊传》对于复仇的支持态度,至于细节上的文字,当它不足以支撑人们实践的时候,经典的诠释者是不惮于“误读”文字,作出合乎自己意向的解说的。
与上述对经典的误读相比,《公羊传》定公四年对伍子胥复仇的褒扬显然更具危险性。
《春秋经》:“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囊瓦出奔郑。”对这段经文,《公羊传》解释说:
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蔡昭侯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归之,于其归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楚人闻之怒,为是兴师,使囊瓦将而伐蔡,蔡请救于吴,伍子胥复曰:“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于是兴师而救蔡。曰:事君犹事父也, 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何休注:“不受诛,罪不当诛也”),子复仇可也 ;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
起初,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谗言,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杀害。子胥辗转逃奔吴国,投靠吴王阖庐,伺机报仇。吴王阖庐一开始就要为子胥发兵,但是被子胥以“事君犹事父也”的理由推辞了。按照当时人的看法,“诸侯不为匹夫兴师”,因此子胥认为,尽管吴王发兵可报父仇,但是却陷吴王于不义了。所以他说,“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父道而不顾及君道。后来,蔡昭侯因为受楚国囊瓦的侮辱,怀恨在心,表示如果哪个国家能够讨伐楚国,他可以“为之前列”。子胥认为如果此时出兵,乃是响应诸侯的号召讨伐不义的举动,和单纯为一己报仇而发兵本质不同,因此他乘机劝吴王发兵讨楚,大败楚师,自己也报了父仇。
但问题也就因此而生,既然说“事君犹事父也”,既然劝吴王为匹夫兴师是“亏君之义,复父之仇 ” 的不义之举,那么作为自己复仇对象的楚王昔日不也曾经是自己的君上吗?不也应该以父道来对待吗?然则复仇于故国故君,算不算不义呢?
《公羊传》的结论非常明确,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子报父仇都是合理的。且不说子胥的父亲无辜被杀,即所谓“父不受诛”,子胥可以复仇,即便父亲真的犯了罪,儿子为父亲报仇也合乎“ 推刃之道”。
相比普通的复仇情形,这种境况下的复仇有极大的特殊性。一般复仇的对象是平民,这里面对的却是君主和法律。如果说在普通情况下复仇者和法律之间也有某种对立,但是那种对立是间接的,是因为先有了对某个第三方的报复,而官方出于维护国家暴力的垄断权而给报仇者以某种刑罚产生的。但在子胥复仇所提示的状况之下,报仇者则与君主和法律之间有了直接的对立冲突,因为报复所指,直接就是君主和以君主名义发布的法律本身。然则《公羊传》的这个立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就非常清楚了吗?
在《公羊传》的鼓吹之下,伍子胥的故事以及由这个故事体现出来的身份伦理哪怕面对君权和律令也不屈不挠的绝对性,终两汉之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史记》卷68《伍子胥传》太史公曰: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哉?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这里太史公提到“向令伍子胥从俱死”,这说的是伍子胥兄伍尚的事。据《左传》:起初楚王刚刚把伍奢囚禁的时候,有人提醒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如果杀死伍奢而不同时将他的两个儿子剪除,一定会留下很大的后患。因此楚王就派遣使者诓骗伍尚和伍子胥兄弟,说如果他们投奔楚王,就可以赦免伍奢。接到使者的报告以后,兄弟两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个骗局,但是伍尚说:“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将复仇的重任委托给弟弟,自己去见楚王,结果被杀害。伍尚的这个举动,在太史公看来却是无异于蝼蚁的“小义”。报父仇,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烈丈夫”的行为。太史公曾从董仲舒问《公羊》学,这段议论很清楚地是站在《公羊传》的立场上而发的。
这还只不过是当时人头脑中的意识,与此种意识相映的实践,则有更加令人惊骇的一面。
本来,秦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就是天下各路豪杰报秦吏杀父兄之仇的举动。《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旦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又同传载二人随武臣略赵地时(《汉书》卷32《张耳陈余传》略同):
(张耳、陈余)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胜)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
在这两节史料中,蒯通以“杀人之父,孤人之子”作为严格执行秦法的范阳令的罪状,以“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作为恐吓他的理由;张耳、陈余则以秦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安”感激群豪,以“报父兄之怨”作为鼓动他们的说辞。由此不难看出,在秦汉之际,血亲复仇的合理性是高于君权律令体制的。
这种状况即便到了在汉代也并未随着统一专制政权的建立而立即消失,且看几个实例:《汉书》卷28下《地理志》(《后汉书》卷20《王霸传》注引《汉书》略同):
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刑杀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剌史、二千石。
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太原郡清。⋯⋯敞所诛杀太原吏家怨敞,随至杜陵,剌杀敞中子璜。
建武初⋯⋯拜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在上述诸例中,代表皇权的郡县地方长吏依法行事,给不法之徒以惩处,结果却遭到了来自宗族势力的形式不同的反弹。我无意于把所有这些事例都附会解释为《公羊》学流行的结果,但可以想见,如果《公羊》学关于伍子胥复仇问题的看法存在一天,类似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就不能完全被取消,则其存在就会有充分的理论支持。
二
鉴于《公羊》学说可能引发的复仇的泛滥,鉴于《公羊》学说对于君权和法律潜藏着如此严重的威胁和蔑视,从很早以来就有人以不同的形式对之加以反驳,强调君权的绝对性和法律的严格性。有些强调是非常直接的,对《公羊》学说的驳斥也是针锋相对的。如东汉和帝时期,张敏就针对复仇过滥的局面,意识到了在《公羊》学说的鼓动下复仇之义解说混乱的问题。《后汉书》卷四十四《张敏传》载张敏上和帝书说:“《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这里说到的《春秋》之义,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据张敏的说法,这一理论成了“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的借口,因此必须加以控制,以保证法律的严明和统一。
不过,既然被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并不主张纯粹的法治,而是侧重所谓“德教”,则更多的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反驳,就不能完全从纯粹法理的角度展开,更多地还是要借着对经典的重新解说来实现。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既然儒术已经“独尊”了,那它就是人们讨论一切问题的渠道。韩非子时代可以不加掩饰地诃诋孔子,对不合法律条文的一切现象尽情挞伐,在汉代却不能这样做。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装圣人和经典,来包裹自己想表达的政见。
反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春秋左传》学者,一是《周礼》学者。这两种学问在汉代都被称为古文经学。
《春秋左传》学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反驳,主要集矢于伍子胥复仇事件。就《春秋左传》的本文来说,对于伍奢被害、子胥逃奔吴国而后协助吴国伐楚等一系列事实,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惟独对于子胥复仇这件事情本身,始终没有正面触及。就在伍子胥实现为父亲报仇夙愿的定公四年,《左传》仅有非常简单的记载:“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只是以客观的态度叙述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事,无一字提及复仇问题,更没有象《公羊传》那样对子胥有那么多直白的褒扬字眼。在《左传》里出现的伍子胥不是充满复仇义愤的人子,而似乎只是一个奉君命行事的诸侯国将领而已。那么汉代的《左传》学者反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依据在哪里呢?
定公四年的《左传》讲伍子胥复仇的时候,重点强调了这样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吴国出兵伐楚以后,战事进展非常顺利,迅速就攻占了楚国的国都。楚昭王仓皇出逃, 投奔郧公鬬辛:
⋯⋯王奔郧⋯⋯郧公鬬辛之弟鬬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惟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汝。”⋯⋯
这里鬬怀提到“平王杀吾父”,是指鲁昭公十四年楚平王杀死鬬辛和鬬怀的父亲鬬成然。这和伍子胥的情况如出一辙,都是父亲被君主杀害,都面临着复仇大义和君臣名分的矛盾。然而鬬辛对弟弟的回答,也俨然是对伍子胥的谴责,“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这就是说,君主的命令是绝对的,臣子无论如何都只能忍受,而绝不能以父子私情摇撼君臣名分。
第二件事: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驶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取其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这个故事说的是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舍身赴秦国求救以复兴楚国的事。申包胥虽然是伍子胥的朋友,但在复仇问题上他却正好处在子胥的对立面:子胥要的是复仇,君臣名分亦在所不顾;而申包胥却要坚守君臣名分,宁可牺牲友谊也决不动摇。
就是这两个故事提供了后来《左传》学者反驳《公羊》学的罅隙。
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在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中,就出现了偏离《公羊传》而同情申包胥的倾向,对于伍子胥的行为也只是在复仇之外加以理解。两书涉及伍子胥的篇章有《说苑·至公篇》和《新序·善谋篇》。《至公篇》讲到吴王阖庐准备为伍子胥复仇,子胥以“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理由谢绝了,对此刘向评论说:“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善谋篇》讲的是伍子胥善于观察时机,能够及时抓住楚、蔡两国的矛盾,劝吴王出兵,成就霸业,强调的重点是子胥的谋略而不是报仇的决心,相反对于吴王准备为他发兵复仇的时候,该篇再次引用了“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的话。总之这两篇文献的着重点都不在于复仇,而在于伍子胥作为吴国将领所具有的干才和气度。两书涉及申包胥的篇章有《说苑·至公篇》和《新序·节士篇》。两者除了与《左传》中略同的情节之外,还增加了楚复国后申包胥谢绝楚王封赏的言辞,更加突出了他作为人臣“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的方面。
刘向是《谷梁》学家,他对伍子胥回避复仇的限制性理解显然来自《春秋谷梁传》,但申包胥的事情不见于《谷梁传》,他之强调作为子胥对立面的申包胥,无疑是受了《左传》的提示。
较早以古文学家身份出来批评子胥复仇是西汉末年的扬雄。《法言·重黎篇》:
到东汉初年,随着古文经学的进一步兴起,《左传》反对《公羊》学复仇的言论甚至成为学者主张立《左传》于学官的重要理由。《后汉书》卷36《贾逵传》载,“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名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稍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季纪、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深于君父,《公羊》多任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既久,莫肯分明。⋯⋯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贾逵是东汉古文经学的重要奠基人物,他显然不同意《公羊传》褒扬伍子胥的立场,而主张发挥《左传》中的若干否定性言论,以“强干弱枝,劝善戒恶”。
在东汉初年由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内,也明确出现了禁绝向君主报仇的文字。该书《诛伐篇》:
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父
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往来不止也。《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不复仇,可也。
和其他论述复仇的传统儒家经典相比,《白虎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转变了复仇的理念基础,在于它设定了君主的某种绝对性。根据儒家传统的意见,父子是一种比君臣更具优越性的关系。臣下对于君主的忠,从根本上是来源于对父的孝,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直就是儒家传统的意见。何休在注“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时候,也是先引用《孝经·士章》之文,说“ 《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无罪为君所杀,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义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可是在《白虎通》看来,子辈为父母复仇,其根据不是自然的情感,而是基于父与君的相似性,也就是所谓的“ 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换言之,是为君主复仇的绝对性保证了为父母报仇的合理性。既然君权成为理由,那它也会成为界限,所以《白虎通》乃径改《公羊传》文,提出了“父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和 “父不受诛,子不复仇,可也”的理论,将《公羊传》认为可以复仇的两种情形统统予以否定。
这成为后来东汉《左传》学家们反对《公羊》学复仇理论的定见,影响绵延整个东汉。徐《中论夭寿篇》引北海孙翱: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残疾厥体,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则曾参不为也。子胥违君而适雠,悖人臣之礼,长畔弑之原⋯⋯
至于徐幹本人,也认为胥有“??君之过”。
不过,《公羊》学并没有随着古文学的兴起立即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和《左传 》学之间在这一点上的争论贯穿整个东汉。《礼记·曲礼》疏引许慎《五经异义》:
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善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
许慎是倾向于《左传》说的。不过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郑玄驳斥他的见解:“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诛,坠渊不足喻伐楚。使吴首兵,合于子思之言也。”陈立认为郑玄的见解合乎《公羊》。许、郑二人都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由此可见,这个争论到东汉晚期还在继续。
三
《周礼》是一部讲职官的书,对复仇的处理问题也曾经结合官吏的职权而加以涉及。可能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对复仇见解的立场要比《公羊传》消极得多,那就是强调由一个公共权威机构对民间私人间的复仇加以控制,并试图通过若干制度设计,尽量减少复仇的负面影响。《地官》“调人”条: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雠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上面第一段材料,疑点很多,历代注疏家们的解说分歧颇大,难以定论。根据孙诒让的意见,这里谈到的对于复仇的调节,都必须放在“凡过而杀伤人者”这一个总的条件下来理解。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样一来,《周礼》本身对于复仇的调解范围就有了相当的局限。但是,汉代的《周礼》学却似乎溢出了这个局限,从而结合对于《公羊》学的批评,结合时代课题,展示了若干新的方面。《周礼·调人》疏引许慎《五经异义》:
《公羊》说:复百世之仇。古《周礼》说: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所复者惟谓杀者之身,乃在被杀者子孙,可尽五世得复之。谨案: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春秋》不讥。又定公是鲁桓九世孙,孔子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是不复百世之仇也。
这里的所谓“复百世之仇”,如上文所示,出自《公羊传》庄公四年。由于史料的限制,这个说法在汉代是否曾经有人引用来为自己的复仇行为辩护,现在已经不能详考。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汉武帝时期,为了鼓动臣下支持自己讨伐匈奴的决定,武帝曾下诏提到汉朝廷在高祖和高后时期所受到的来自匈奴的打击和侮辱,其中倒是引用过同样是出自庄公四年《公羊传》的 “复九世仇”之说。但这里涉及的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仇怨,和国内的法制问题无关。不过据《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在给光武帝的上书里面,桓谭曾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由此判断,似乎在汉代民间确实存在着仇怨持续几代而不解的现象。或许这种现象和《公羊》学之间确有某种关联?或许正是针对着这种关联,汉代的《周礼》学者才有如上限制复仇亲等范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