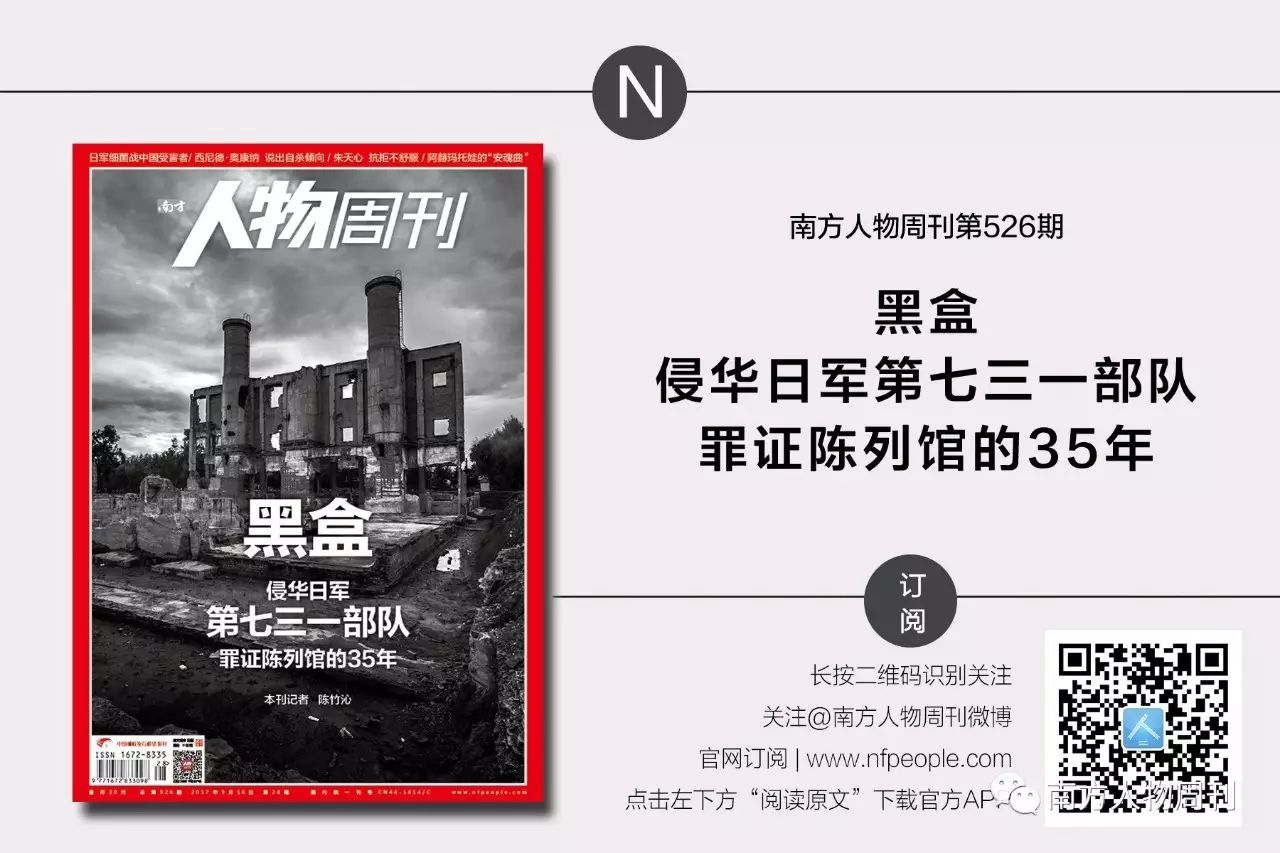阿赫玛托娃
从20年代开始,苏联 《青年近卫军》 杂志的编辑就有困惑:为什么这么多女学生和女工人写信来,表达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感到亲切”,而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连最政治正确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三四十年代,当他们从一些被划为“人民公敌”的知识分子家里查抄出上千本书时,总是偷偷把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诗集占为己有
彼得大帝在芬兰湾这片三角洲上建造圣彼得堡时,心中想的是老欧洲。如他所愿,44座岛上林立着一部欧洲建筑史,而它的93条水路,滋养着一部俄罗斯文学史。
拉斯柯尼科夫顺着运河的堤岸走,走到桥边,站住了,突然转弯上了桥,往干草市场走去。他贪婪地左顾右盼,凝神端详每一样东西,可无论看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一切都从他眼前一晃而过。“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就要把我关在囚车里,从这座桥上经过,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到那时候我会怎样看这条运河呢?——要是能记住它就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四章。写的是格里博耶多夫运河,笔直流过老城区。河水墨青,河上21座桥,站在最别致的几处,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干草市场是从前贫民交易干草、木柴、牛马的地方,现在叫干草广场(Sennaya Ploshchad),设有地铁站,三条线路在此交汇。2017年4月3日下午,一列蓝色地铁从干草广场站开往技术学院站,一节车厢爆炸,14死,五十多伤。警察很快逮捕了十个小伙子,他们涉嫌参加了国际恐怖组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干草广场附近的几栋公寓里住过。这一带曾是他的,也是普希金、果戈理的地盘。那些桥与河,自然而然带进《青铜骑士》、《套中人》、《穷人》、《白夜》里。
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里,“涅瓦河烟雾茫茫,太阳黯淡”。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晴朗李寒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全集》
涅瓦河宽度似江,城中运河也比威尼斯的大一号,桥因此宽些,子夜还有开桥表演。路过码头望见:凌晨1点上船,河上绕行1小时40分钟,看三一主教桥、铸造厂桥、布尔什奥克丁斯基桥打开通船,900卢布。“一百块!”揽生意的小伙子冲中国人竖起一根食指。
安娜·阿赫玛托娃故居铸造厂大街53号(Литейный просп. 53)就在河边,河名有好些叫法:Фонтанка(丰坦卡河),fountain(喷泉河),中国人叫它放荡河。
这本是尼古拉·普宁和安娜·阿连斯的家。阿连斯是海军上将的女儿,嫁给了艺术评论家、冬宫策展人普宁。1913-1938年,普宁策划了许多展览,其中最重要的是1932年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十五年间苏联艺术家展”,涵盖了1917-1932年间的俄罗斯先锋艺术家,像菲洛诺夫、塔特林、波波娃、罗钦科等等,还有独占一个展厅的马列维奇。马列维奇1915年创作的《黑色方块》、《动态的至上主义》,历经百年,先锋依旧。

尼古拉·普宁
2017年2月,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在伦敦再现了这场艺术展,向百年前的一场革命,也向因“谋划反苏”罪名被捕、最后死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普宁致敬。普宁的作为,部分因档案迟迟解秘不为人知,部分为情人阿赫玛托娃的光芒所掩。
1925 年 11 月,阿赫玛托娃搬进铸造厂大街53号。普宁、两个安娜和她们的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新来的安娜为她的房间付租金。阿赫玛托娃不是第一次过三边生活。1922年夏天,她住在先锋艺术家、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家里,与另一个女人共享一个情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她与她的男主角总是分头各有别人。
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的恋情发生在1922年9月。1914年他们就相识,有信件表明,在这段关系里,主动的是女方。搬进来之前,她与普宁签订了一份婚约,附带“我同意尼·尼·普宁同别的女人生孩子”的条款。
俄国女子在爱情降临时是相当果敢的,而男性通常——用几天前在明斯克拜访的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只负责浪漫和感觉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在阿赫玛托娃这里,变成了诗。
怎样形容阿赫玛托娃年轻时的以情爱为氧气都不过分。爱的惊慌、甜蜜、嫉妒、忧伤、争吵和懊悔都是她的主题。
普宁戏称她为“皇村级别的诗人”——从1岁到16岁,阿赫玛托娃生活在皇村,那也是普希金出生和成长之地。大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与她互相倾慕,亦含蓄指出:“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站在上帝面前。”

阿赫玛托娃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
穿过花园小径,走近这栋建于18世纪的Fountain Dom,一路新绿。路边一架蒙着塑料纸的钢琴,旁边立块牌子,上面有故居纪念馆的缩写,牌子上写:这台钢琴非常老了,你可以坐在这里弹奏,但不要损坏它。
从进门处的大衣、小包、旅行箱、穿衣镜、油灯、雨伞和钥匙串开始,昔日重现。
她有着惊人的美貌。身长5英尺11英寸,乌黑的秀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似的浅灰蓝色的眼眸,身材苗条,体态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轻盈。在阿米迪奥·莫迪里阿尼(1884-1920)开创先例的半个世纪里,无数艺术家为她作素描、彩绘、铸像、雕塑、摄影。至于献给她的诗歌,合起来比她自己的全部作品为数更多。
这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眼中的阿赫玛托娃。5英尺11英寸,整整1米8,大衣够长。可是,在她二十多岁住过的乡下,比如斯列普涅沃的夫家庄园,邻居们觉得她像严肃的见习修女,四肢骨瘦如柴,一双大眼睛毫无笑意,一点也不漂亮。婆家人觉得她的长相外国味太浓,老仆人称她为法国女人,当地村长认为她是埃及人,而阿赫玛托娃自己说,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阿赫玛托娃入住三年后,惟一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也搬来住。男孩正上中学。那张流传很广的三人合照原来那么小那么旧,躲在角落里,旁边是蚀了边角的旧地图——尼古拉·古米廖夫一生不羁爱云游。
14岁,在皇村,她第一次见到“灰眼睛男孩”古米廖夫,“又高又瘦,脸长长的,蒜翘鼻子,死气沉沉的样子,看上去还很高傲。”可在留存的照片上,古米廖夫看起来比她后来遇到的任何一个男人都要相貌堂堂。
几天后,我在特维尔大街一家亚美尼亚咖啡馆里见到了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副教授尤莉亚(Юлия Дрейзис,Yulia Dreyzis,中文名邓月娘),她精研诗歌,教授中国文学。去年,她翻译的余华长篇小说《兄弟》在俄罗斯出版。在白银时代璀灿的诗人谱系里,她偏爱尼古拉·古米廖夫:“我觉得他非常特别,而且他一直对东方怀有兴趣。可能我爱上中国文化,就是从爱上古米廖夫的诗歌开始的。”
17岁的古米廖夫第一眼就爱上了阿赫玛托娃,苦追7年,炽热程度随着年份下降。就在结婚前一年,古米廖夫还为了另一个姑娘跟人决斗。1910年,两个人在基辅附近小镇上的尼古拉耶夫教堂举行婚礼(娘家人不看好,一个都没来),随后去巴黎度蜜月。婚后第一个圣诞节,他送她的礼物是:一盒罩着鲜花般织物的丝袜,一瓶柯蒂香水,两磅克拉夫特巧克力,一把玳瑁梳子和一本特里斯坦·科比埃的《黄色的爱情》。当时他人在非洲。就在那个圣诞节前,阿赫玛托娃写出了她最有名的诗作之一《灰眼睛的君王》。
古米廖夫不停地离家远行,阿赫玛托娃不停地写诗,191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古米廖夫同样热爱诗歌,跟妻子和“第一车间”的同道们——曼德尔施塔姆、津克维奇、纳尔布特等等——共同确立了阿克梅派的美学原则。然而,对他来说,比起皇村的诗歌沙龙,异国旅行和探险要有趣得多。
他到埃及和东非的第一次探险是跟着骡队去的,归来时皮肤黝黑,身披兽皮。第二次旅行是到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半岛,有科学院的部分资助,拍下迷人的照片;他见到了未来的皇帝海尔·塞拉西,在烈日下横渡鳄鱼出没的青尼罗河……他还到过撒哈拉大沙漠、尼罗河、马达加斯加、地中海和拉丁美洲的安得列斯群岛。
在伦敦,古米廖夫结识了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学家、中国诗歌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留在伦敦的笔记本上,抄着一长串书名,有正在读的,有打算借的,全是关于东方文学的著述和译著。7月,他到了巴黎,停留半年之久,受同在巴黎的俄国画家冈察洛娃和拉里奥诺夫夫妇影响,愈发被东方文化迷住。
这时候,他读到法国女诗人、当时已是法兰西院士的茱迪特·戈蒂耶的一本诗集:《玉书》。茱迪特的父亲是法国大诗人特奥菲尔·戈蒂耶,三年前古米廖夫曾将他的代表作《珐琅和雕玉》译成俄语出版。
戈蒂耶先生家里,供养着一位名叫丁敦龄的中国人。丁敦龄是山西平阳府秀才,辗转流落巴黎,机缘巧合成为戈府两位小姐的中文老师。他教她们讲汉语,写汉字,吟诵中国诗歌,查《康熙字典》。
《玉书》的71首法译汉诗中,有一首叫《瓷亭》,很可能是茱迪特将李白的两首诗《题元丹山居》和《江南春怀》合译而成的,颇能满足古米廖夫对中国的想象,被他转译成俄文,且用来命名自己从英、法汉诗译本转译的诗集。
古米廖夫的《瓷亭》选译的11首中国诗里,直接从《玉书》来的还有4首:李白的《江上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秋笛》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娘说,以《瓷亭》为例,无论茱迪特还是古米廖夫,都不知陶是中国人的姓氏,以为是陶器。所以,大体说来,这些译诗跟李白原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他们独具匠心的改写。
来看语言变戏法。李白的《江上吟》——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萧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将古米廖夫从法语到俄语的《江上吟》回译成中文:
我有红木造的船,有用玉制成的笛管。
就像水能洗掉丝绸上的污点,酒会消解心头的烦愁。
一个人若有好酒、快船,
有可爱的女人相伴,夫复何求?
地地道道像个神仙。
月娘轻推一扇小门,顺着光影,我像探案一样拼出一小块绵延一个多世纪的东诗西渐图,也是对人类心灵在何种波长上能产生共振,而文化又是怎样在误读中离散和生成的一次勘探。

铸造厂大街53号,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入口处
这所大房子里,没有语音导览,只能凭每张书桌上摆的、墙上挂的照片,以及周围陈设与以塞亚·伯林描写的重合度,来猜测阿赫玛托娃的领地——
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地板上没有地毯,窗户上没有窗帘,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箱子,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
木箱在,画像也在,是1911年莫迪利阿尼在巴黎为她画的裸体素描,只几根线条,一颗低垂的头。画架上还有一幅躺着的女主人油画。桌子很小,上面的台灯、闹钟、风景画、茶杯、相框都很小。相框里,是她与一生密友瓦丽娅的合影。此外,有一具立式自鸣钟,一面印有很多人头像的大镜子——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皮里尼亚克、布尔加科夫、古米廖夫……她为他们每一位写过诗,多半是悼亡诗。
在巴黎发黑的雾中,
肯定又是莫迪利阿尼
悄悄地尾随我。
他有一种不幸的素质
将混乱带进我的梦中,
也要为我的诸多灾难负责。
另一个房间里,有一张铅笔素描支在画架上,画的是满头卷发的普希金,下面署着“格拉夫· B·马塔,1899”。十月革命以后,阿赫玛托娃在农学院图书馆工作,搬来时正怀着浓厚兴趣,开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
在那些公用空间,或别的房间里,有阿赫玛托娃跟普宁的合影,有两个安娜的合影,有普宁、阿连斯跟女儿伊琳娜的合影,有阿赫玛托娃跟伊琳娜的合影,有伊琳娜抱着玩具猴的样子——这只毛绒绒的大嘴猴,就坐在客厅酒红色布质沙发上。
阿赫玛托娃去世前说,这世上有三个人称我为“你”——瓦丽娅、伊琳娜、伊琳娜的女儿。是伊琳娜的女儿——普宁的外孙女,也叫安娜,陪她走过最后的日子。
她住在这里,离开了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可还关心他,偶尔会住到他留在彼得堡的房子里,或去莫斯科看他。她也很舍得花时间协助古米廖夫的第二位妻子撰写亡夫的回忆录。1938年正式跟普宁分手,她并没搬出去,只是跟另一位安娜调换了房间。1952 年,这栋楼被国家征用为北极研究所,她才离开,晚年住在科马罗沃的作家之家……我忽然意识到,无论在彼得堡还是莫斯科,她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个房间。她只是被苦难推着,从一个男人到下一个男人,终于站在上帝跟前。

在一个过道的角落里,有一个圆桶形木箱,箱子一端是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合影,挨着几张残缺的地图
过道里有面墙,糊着1930-1940年代的《真理报》,一直伸到天花板。报上有模糊照片,位置都高,须仰头辨认:斯大林、赫鲁晓夫、丘吉尔、罗斯福……最多的还是斯大林开会讲话的样子。在有些部分,报纸朽落,露出原先的墙面,一种玫瑰红与草绿色相间的马赛克。这两种质地相配,加上过道里的昏暗,看起来相当穿越。
1933年,阿赫玛托娃21岁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被捕,关了十天,放了。1935年10月儿子第二次被捕,她写信给斯大林,又放了。尽管从1925年起她没有获准发表一行诗歌,但斯大林还是对她颇为照顾。
第三次是1938年3月。第四次是1949年11月。囚禁或者流放,前后一共13年半。像大清洗年代的许多俄罗斯母亲那样,阿赫玛托娃不停地奔波、求助、探监,直到她自己也成为“人民公敌”。
1945年9月的一个早晨,在涅瓦大街著名的作家书店,访苏(停留七个月)的俄裔英国学者以塞亚·伯林遇到了同在翻书的苏联文学批评家兼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攀谈之后,奥尔洛夫就在书店拨通了阿赫玛托娃的电话。下午3点,他们一同来到这所大房子。此前,伯林没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一行诗。
这场会面有四个人在场,第四位是阿赫玛托娃的一位女学究朋友。他们的谈话是被冒失的伦道夫·丘吉尔打断的。他是伯林的牛津同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记者,临时来到列宁格勒。他之所以站在院子里大叫“以塞亚以塞亚”,是想找懂俄语的老同学帮忙跟宾馆服务生说一声,他刚买的鱼子酱应该放在冰上。而奥尔洛夫跟小丘吉尔握手之后,表情由不知所措变成恐惧,飞快地逃走了。
流言就此传开:小丘吉尔在列宁格勒侦察一项救援行动,有人要将阿赫玛托娃秘密送往英国。
伯林向阿赫玛托娃电话致歉并再约时间,她说:“今天晚上9点我等着你。”
当她再次为他开门的时候,并不是独自一人。另一位女学者,一位亚述古文专家,也在。他俩单独相对,已是午夜了。阿赫玛托娃关注的重点,是那些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的朋友们的情况,而伯林,充当了两类被隔断的俄罗斯文化人之间的信使。
谈话进行到凌晨3点光景,释放归来的列夫·古米廖夫进了房间,递给伯林一个盛着煮土豆的盘子。他比伯林小两岁,读过原版的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从未出国。伯林记得,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他们三个坐在炉子旁边,把那盘土豆分着吃了。

以塞亚·伯林
他俩是在谈论各自喜爱的作家时发生争执的。他不喜欢她热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则对他欣赏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最后的分歧发生在托尔斯泰那里,她说,让安娜·卡列妮娜被追逼致死,是托尔斯泰向他声称要谴责的那种庸俗社会风尚的投降。
伯林发现,她也有轻蔑、嘲讽、略带恶毒的一面,女王般的高冷此时被某种更幽默、更人性化的东西替代,这让伯林很高兴。而当她论及对祖国的不离不弃——和人民在一起,和民族语言在一起——他肯定自己“从没遇到比她更会装腔作势的天才了”。
伊格纳季耶夫记下了那次通宵长谈,伯林从阿赫玛托娃房间出来后的“神魂颠倒”,以及,一头栽倒在旅馆房间床上时的嘟嚷:“我爱上了,我爱上了。”
阿赫玛托娃为这一夜写下了《诗五首》,没有一个读过它们的人会相信这两位相差20岁的男女这一晚上没有同床共枕。然而,根据亨利·哈代(伯林著作管理人)的伯林档案,在1994年的一次访谈中,伯林明确说出那一夜,“他呆在房间的一边,她则呆在另一边”,两个人几乎没碰过对方——告别时,他也只是很欧洲地吻了吻她的手,未行俄式亲吻双颊礼。
阿赫玛托娃在伯林离开列宁格勒的第二天拍了一张照片,眼窝深陷,侧脸线条依旧,下巴和脖颈松驰,紧抿嘴唇。这张照片被收进《伯林传》。翻过一页,是伯林在1940年代丰润的脸。他们会面时,她穿着破旧的衣服,身形臃肿,深色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仍然保有那种高冷的尊严。
一种类似于爱情的化学反应,确实产生了。那两年间,阿赫玛托娃从塔什干回到二战后的列宁格勒,儿子列瓦从西伯利亚提前获释,去德国的苏联红军服役后刚回家。她最近的亲密男友,一位列宁格勒的验尸官,告诉她已经决定跟别人结婚。所以,当56岁的阿赫玛托娃冒险跟36岁的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临时一秘伯林会面之际,正被一种清清寂寂了此残生的悲戚笼罩。
而伯林此时,陷在一场与有夫之妇昏头昏脑的恋情中已经两年。他是带着某种仰慕、同情走近她的。这种同情,阿赫玛托娃接收到了——
我早就不喜欢
让人怜悯,
而带着你的一点怜悯之心
走着,犹如体内带着一片阳光。
这就是为何周围闪着霞光。这就是为何我每走一步
都创造一个奇迹。
这次会面生成的涟漪荡漾了很久。伯林在离开列宁格勒两个月后还在信中说,造访阿赫玛托娃“是发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4个月后,他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阿赫玛托娃在这儿的每句话都是说的——你。真是件富有戏剧性的神秘的事情!”
这次会面的后果是严重的。除了伯林自己,每个相关的人都因他的闯入付出代价。伯林回国前向阿赫玛托娃告别时发现,便衣警察出现在她家的楼梯口。一天后,她家的小客厅被秘密警察安上了窃听器。“半是修女,半是妓女”的侮辱性定义和更糟糕的境遇从此包围着她。许多年后,列宁格勒安全总部的三卷文件共900页被披露了,全是围绕阿赫玛托娃的告发材料、电话窃听报告和关系密切者的口供。这些档案建于1939年,名为“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联姿态”。
以塞亚·伯林1946年写成的《关于 1945 年最后几个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亨利·哈代将它收入《苏联的心灵》),是他受激发后对原任务——写一份外交政策备忘录的置换,相当于一部 20 世纪上半叶的简明俄国文化史,是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它与罗曼·罗兰、纪德、本雅明、瞿秋白、约翰·斯坦贝克等等富有洞察力的人留下的记述一起,汇成那时苏联真实面貌的一束文献。

尼古拉·普宁家的厨房。皂架上还有半块干裂的肥皂
阿赫玛托娃仍然一首接一首写着,但诗的内容渐渐被替换了。她在《哀歌》里说——
改变了我,仿佛一条河流
严酷的时代将它改变。
有一次,母亲听完她朗读的诗后开始啜泣,对旁人说:“我不懂诗,只知道我女儿心里不好受……”
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有17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的。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能。”我说。
这是长诗《安魂曲》的代序,交待了一个诗人转向的背景,她开始为相似的苦难写作。这也体现在她对普希金诗歌的研究里,她自觉不自觉地调动自己和他人的经历,去体验普希金因十二月党人被处决而永远受伤的记忆,去追踪诗人心灵的运动轨迹。
这也是几代俄罗斯读者保持着对阿赫玛托娃的热爱的原因。在莫斯科,我问尤莉娅,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她更喜欢谁的,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阿赫玛托娃。在她看来,前者想象力惊人,始终游弋在她个人建构的世界里;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更贴近人的生活——“更接地气,”她说。
从20年代开始,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的编辑就有困惑:为什么这么多女学生和女工人写信来,表达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感到亲切”!连最政治正确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三四十年代,当他们从一些被划为“人民公敌”的知识分子家里查抄出上千本书时,总是偷偷把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诗集占为己有。古拉格的犯人们把她的诗刻在桦树皮上,装订成手工书,藏在破衣服里随身带着。
对阿赫玛托娃的打压从很早就开始了,她诗歌中的情绪,被视作来自一个“垂死的世界”,而她,是“纯粹的室内资本主义女诗人”。1930 年代,她几乎从未公开发表诗作。卫国战争期间,她参加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了《起誓》、《勇敢》和《胜利》。
1944 年 5 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和列宁格勒、和前线相关的消息。跟其他诗人一样,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我也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
5月之后,她被批准离开塔什干回家,途中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朗诵会。朗诵结束时,观众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她吓坏了,因为事后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她,斯大林曾问日丹诺夫:“是谁组织了这次鼓掌?”

一进门,就是她穿过的大衣、戴过的帽子、背过的小包、用过的箱子……正对它们的是一面穿衣镜
一个缓慢、低回、带有某种音乐性的声音,从前面幽暗空间传来。这是一个全由照片和手稿布置的展厅,陈列着许多像是从照相簿里直接取下来的照片:母亲怀里的女童,斜倚在公园长椅上、围着狐狸披肩的女士,工作证上的俊俏人儿。工作证编号44,逐行填着姓名、父姓,最下端有代理主任签名。年轻的阿赫玛托娃滑冰、俯卧、扶腰站立,优雅中微含俏皮。她颀长苗条的身姿即使出现在克雷斯底监狱的围栏前,也只与美相关。
来之前,我在涅瓦大街的一家书店里买到了她的诗集,记住了《安魂曲》的俄文形状——РЕКВИЕМ。在展厅的一个图标前,我意识到它指向《安魂曲》的手稿,然后,一位会说英语的大姐告诉我,那低低的女音就是阿赫玛托娃本人在朗诵这首长诗。我被这哀而不伤的调子迷住了。我听到了Neva(涅瓦河)的发音。
这首长诗从大清洗开始的1934年末,一直写到1964年左右,1987年才在前苏联《十月》杂志上发表。在此之前,它一直保存在诗人和她七位密友的记忆里。
其中一位叫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诗人,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安娜来看望我时,给我读《安魂曲》中的片断都得小声,在她自己的屋里连小声读都不敢,她总是在谈话中突然停下来,用眼睛示意我注意天花板和四壁,随即拿起一小片纸和笔,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想喝茶吗?’或者‘您晒得可真黑呀’,然后迅速在小纸条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太早了,’安娜大声说,划着火柴,在烟灰缸里把纸条烧掉。”
我高声哀号十七个月,
千呼万唤你回家,
我匍伏在刽子手的脚下,
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
……
如今要让你明白,
你一生的境遇又将如何——
你要站在克列斯特铁窗旁边,
排在三百号,手托探监的物品,
滴下你滚滚的热泪,
烤化新年的冰层。
像监狱的那株白杨摇曳,
无声无息——而大墙里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在死去……
1963年前后,《安魂曲》的“口述本”流传到西方,在慕尼黑出版了部分章节。在此之前,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总谱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通过微缩胶卷被带到西方首次发表的——以塞亚·伯林对后者颇有贡献。
这首诗像“域外之雨”,击中了英国作曲家约翰·塔文纳(John Tavener),他创作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81年由BBC交响乐团在伦敦逍遥音乐节上首演。
在澳大利亚天主教作曲家克里斯托弗·威尔科克(Christopher Willcock)的版本里,非凡的女高音莫琳·奎夫(Merlyn Quaife)引领我们进入诗中的黑夜、树木与河流。
鲍里斯·季先科谱写的安魂曲片断,应该是阿赫玛托娃生前惟一听到的。季先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意门生,他对那个时代的紧张、苍凉、荒诞和黑暗质地有更切己的把握。1968年,季先科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问世,此时诗人已离世两年。
阿赫玛托娃是惟一活着看到命运重新发牌的白银时代的诗人——她在《火枪兵的月色》中写下“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这样的句子,竟没被抓起来。晚年,她写出了苦难对她的加持——
诗人不是人,他仅仅是灵魂——
即便他是盲者,如荷马,
或者,他耳聋,像贝多芬——
他依然能看见,能听见,能引领所有人……
1963年12月27日,她在写给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死于流放)遗孀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们都曾经想到我们一定要活着看到那一天——那哭泣和光荣的一天。我们还需要一起度过一些时日——那种高悬的日子。”

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
离开这所大房子的时候,我留意看了看门。门牌号是44。那黄铜铭牌上写的什么?懂俄语的朋友告诉我:尼古拉耶维奇·普宁。
园中空气清润,草木绿得挤得出水滴。一个男孩在看书,一个女工正在油漆木质长椅,漆是纯白的。那架蒙着塑料纸的钢琴前面站着几个人,它被打开,正被弹奏。
(本文参考了晴朗李寒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伊莱因·范斯坦《俄罗斯的安娜》;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俄罗斯“1917自由历史”项目发掘的资料;现居巴黎的刘志侠对丁敦龄的研究;诗人阎逸对《安魂曲》音乐的研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6期
文 / 特约撰稿 李宗陶 发自俄罗斯
编辑 / 杨子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