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琢如磨
 这篇文章选自龙应台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但愿你能有耐心读完一个中年人给你的温柔提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对你有用。我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但,兼听则明,过来人给你漫无目的的行走,一张人生的地图,一路上能少一点沮丧多一点顺畅。
这篇文章选自龙应台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但愿你能有耐心读完一个中年人给你的温柔提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对你有用。我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但,兼听则明,过来人给你漫无目的的行走,一张人生的地图,一路上能少一点沮丧多一点顺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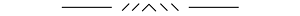
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
我会比较多地提到钱穆先生,做为我从素书楼走到新亚书院对他的个人致敬。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二、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 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 no.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五、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征,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从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经被压迫的反对者以“自由”的旗帜来排斥反对者的反对者。
也就是说,我的“中年迷惘”其实就重复了胡适之的发现,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的十周年纪念会上回答殷海光的问题,说,他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不仅只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自由”的人说的。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