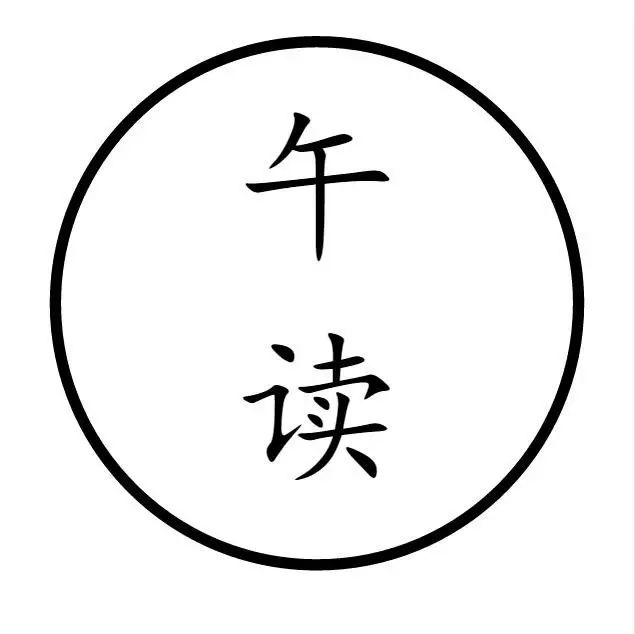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中外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创办。本平台旨在传递国内外优秀文艺理论、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订阅及赐稿
※ 一场精彩智趣的“世界级播客”,“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生前最后的对谈__ 思想碰撞,棋逢对手,从不同侧面描写人类的生存境况:新中产的不稳定感、互联网同温层……
※ 畅聊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爱情、家庭、身份、权力、当下与未来……记录1933—2016年重要事件,“二战”“经济危机”“数字时代”“新穷人”……以冷静的局外人与炽热的参与者双重视角,洞察这一流动、变化的世界。
※ 一本小书,关于鲍曼毕生工作的珍贵谈话 __ 从军队少校到大学教授,从实践者到思想者,鲍曼从未停止思考。他并不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鼓励我们更好地认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实和真相。
※ 辛辣的幽默感,史诗般的世界观,化阴郁为光明的罕见天赋 __一直活泼敏锐,始终心怀希望,做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是鲍曼通过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力量。“即使知道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
※ 卡夫卡、弗洛伊德、莱姆、昆德拉、艾柯 在对谈中纷纷现身冒泡
哈夫纳:
在批判当今猖獗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您讨论过身份认同如同时尚配饰的想法。您说,消费社会使人难以幸福,因为它依赖的,就是我们的不幸福。
鲍曼:
在这个语境中,“不幸福”这个词太大了。但每个市场经理都会坚称,他的产品能让消费者满意。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不会有消费经济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满足,那就没理由搞产品迭代了。
哈夫纳:
1968年的左翼把这称作“消费主义的恐怖”。消费和消费主义有什么区别?
鲍曼:
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则是社会的特征。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
哈夫纳: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想理解这点,需要对历史进行考察。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工匠失去他们的工坊,从而陷入贫困。但新的工厂所有者——正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发展——又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工人。只要每天还有面包吃,他们就不会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现代市场经济的先驱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费经济畏惧的鬼怪就是传统的消费者,因为传统的消费者满足于她/他购买的产品。而确切地说,与先前的消费形式形成对照的是,消费主义把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而非需求的满足——关联起来。这个增长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营销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新的商品,而是创造新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片刻之前还是最新样式,还被广告描绘为欲望对象的产品,突然就会被嘲讽为“过时”的东西。下至五岁大的儿童,就被消费社会朝着不知足的消费者的方向训练了。星期天,他们会和父母一起,去一个充满有趣的、令人激动的、诱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购物。一旦厌倦,他们就会把买回来的东西扔掉。
哈夫纳:
市场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费者。就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被商品化了,这又把我们带回认同问题。
鲍曼:
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哈夫纳:
今天,许多年轻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发视频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还可以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没有具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
对他们来说,出名意味着登上成千上万份报纸的头条,或出现在成百万上千万个屏幕上,变成人们谈论的对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们自己想要的光鲜亮丽的杂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儿。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能增加一个人在竞争中获得最多关注、名声和财富的机会。这就是编织今天的梦想和童话的材料。
哈夫纳: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说法,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根的问题。相反,他用了锚的隐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从社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不一样,起锚既非不可逆转,也不是什么决定性事件。您不喜欢这种说法,为什么?
鲍曼:
只有在我们不再是我们现在所是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变成别人,所以我们必须永远抛弃我们先前的自我。因为新的选择源源不断地出现,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当前的自我过时了,令人不满意,让人不舒服。
哈夫纳:
改变我们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仍是人们的箴言:重新发明你自己!
鲍曼:
当然,这一策略并不新鲜:遇到困难,掉头逃跑。人们总试图这么干。不过,新鲜的是,通过从产品目录中选择一个新的自我来逃离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线迈出的自信脚步,很快就变成强迫性的常规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变成别人”,变成了强迫性的“你必须变成别人”。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
哈夫纳:
自由意味着什么?
鲍曼:
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流动现代性的时代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艺术许诺了这个自由,却未能履行承诺。
哈夫纳:
那么,我们为我们享受的自由牺牲的安全是什么?
鲍曼:
如今,我们要负责寻找并非我们创造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点上,我总会回到已故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说,今天的个体必须用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来为社会的问题寻找个体的解决方案。与先前的时代形成对照,这些问题不再是地方性的,产生于巴黎、柏林或华沙,相反,它们是全球性的。我们无处可逃。就像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空间”。一切都在流动。问题也在流动,它们的原因是超领土的,并且它们不受地方的规则和法律约束。觉得自己受到限制的企业家可以随时跑到别的地方,或把自己的资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哈夫纳:
对雇员来说就不那么对了;他们的流动性没那么高。这就是人们抗议全球化的原因。
鲍曼:
因此在大多数国家,我们都听到了期盼强政府的呼声。人们受够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附带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个体化了。按法律规定,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无法摆脱个体的义务;我们被要求承担这些义务。一方面,这是好事。我们能为自己服务,能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持续地受挫。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不足。这使个体成为孤儿。

【内容简介】
“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没有被发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作者,鲍曼在世最后访谈。
【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
出生于波兰,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
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者”。
一生出版 50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现代性与大屠杀》《社会学之思》等。
彼得·哈夫纳(1953— )
记者、作家。长年在美国、波兰和德国工作。
他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学位。之后,成为一名自由记者,为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媒体工作。1994年获埃贡·欧文·基施奖。1994年获苏黎世新闻奖。
【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渎神》《潜能》《为什么是阿甘本?》《散文的理念》《导读萨义德》等。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