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王国斌
来源:私木合伙人
本文为王国斌先生在安信证券投资策略会上发表的演讲。通过生动的小故事,提醒大家顺其自然接受一年四季的更替,不必为经济周期感到烦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去用情感,更需要用理智来判断,要正视经济周期的更迭,不必庸人自扰。
对目前市场情绪的探讨
今天很凑巧,当时高善文问我演讲取什么标题,我说“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
刚才李勇说我这个题很扣题,实际上我确确实实没有和高善文商量,因为这是我对近几年经济情况的判断。
我想首先谈谈目前的市场情绪。
实际上这一两年来,对大家影响最大的是舆论。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有句话,“日子难过年年过,一年还比一年好过”。这两年,我不知道大家的日子是不是特别不好过,反正经济学家说这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的。
但是从微观层面上,我只看到出门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出门坐飞机比几年前买机票是不容易的,坐高铁也是常满的;你如果出去旅游的话,不管国内国外,那都是人满为患。
所以明年如果有什么巨大的风险的话,我认为那都是“头条风险”(Headline Risk)。
你看这两天的标题,《2017年的悲观因素》,这是比较温和的,只是说悲观因素,还有《从金融周期看,调整尚未开始》,我就不知道他从哪个角度得出来的结论。我看了一下标题,我基本上就不会读下去了。昨天晚上更“可怕”的一个标题:《今夜加息,全球冲击波来临》。明年所谓的“黑天鹅”,应该也会有很多很多。但从稍微长一点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更多的是“头条风险”。因为今年我亲身经历:脱欧公投时我是在伦敦,美国大选那天我在北卡,没有感受那么剧烈的冲击。就像当年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觉得世界末日到了。结果一起床,出去上班的时候看到路上行人匆匆,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走,我就想,世界还是这个样子。开盘后我就从跌停板买到涨停板。
人们往往高估事件当下的反应,低估它的长期的影响。

现在大家心理上不大能正视面对,很有可能就是“第五纵队理论家”越来越多,什么叫“第五纵队理论家”呢?回溯远点,比方说10多年前国企改革那一次理论讨论,就是某些所谓的外来理论家发起的,结果拖延了国企改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越来越多的反市场、反竞争、反开放的论述,各种各样的这种舆论比较多。但这些都是噪音。我认为未来5到10年仍然会有很多噪音。
其实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5到10年内增长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科技创新;10到20年之间是制度变革;30年左右是社会变迁。我们这个时点,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制度变革、社会变迁三个点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从我的观点来说,
科技创新、制度变革、社会变迁目前在中国,三者都在一个正的方向汇集的。
那之所以这两年大家情绪不好,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不接受经济周期。
《共同基金常识》里面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个故事,园丁对总统说“在花园里,草木生长顺应季节,有春夏,也有秋冬,然后又是春夏,只要它们根基未受损伤,草木的一切都将会恢复正常的。”总统感慨到“我必须承认,格纳德先生,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的最令人振奋和乐观的看法。我们中的很多人忘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通之处。正如自然界一样,从长期看,我们的经济体系保持着稳定和理性,这就是我们不必害怕自然规律的原因……我们坦然接受不可避免的季节更替,却为经济的周期变动更烦恼,我们是多么愚蠢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很坦然地去接受一年四季的更替,但是我们却为经济周期感到烦恼。实际上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去用情感,更需要用理智来判断。

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有些东西是能预测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预测的。
比如说,什么气候我们是可以预测的,但今天多少度是没法预测的,第二天的天气温度是很难预测的,但处于什么样的气候是很好预测的。所以我来这里(海南)的时候,我一般会带一件外套;如果夏天来的时候,我带个西装来肯定脑子犯毛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判断处于什么气候条件下。你不要处于冬天你就情绪不好,我们应该坦然地去接受春夏秋冬。所以我们目前的情绪如果不恰当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人不接受这个四季的更替。
另外,
因效率和公平引起的情绪也有周期属性。
平等和效率的周期大概是三十年左右,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有时候是矛盾,这个矛盾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爆发的。其他东西我不阐述,但有一点很简单,30年前美国的金融业占整个工商业总利润的八分之一左右,现在差不多到五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
金融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但也拉大了两极分化。
川普的很多竞选口号和当年里根的竞选口号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里根当年竞选的时候,他的口号就是政府是最大问题所在,他上来是要推翻现有政府政策的。30年前,不管是中国的改革、美国的改革、英国的改革,实际上本质都一样,过于“左”的平等,会出现很多效率方面的问题。效率低下,所有人生活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要进行一些促进效率的改革。那现在是大家看到了,这个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政治上也是一种不可持续。在英国脱欧、美国竞选,我感受到同样的情绪,包括国内情绪,对平等的需求,平等的呼声非常强烈。这是一个30年周期。
还有一类案例也可以解释我们当前的情绪。这个案例是什么呢?托马斯·沃森在二战的时候接受任命去调查那些遇难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出飞机事故。结果他的调查牵扯到一个非常高级的将领,那个将领和驾驶员出去飞行时,将领是一边唱着歌、哼着调子,放松的、很开心的。驾驶员一听他哼调子、打拍子,在没有完全助跑足够时,就拉起飞机,结果这个飞机就失事了。调查者问他,你那么专业,明明知道飞机不能起飞就起飞了?他说,他以为这个将军命令他要起飞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大部分的混乱,大部分大家觉得莫名其妙,都是因为在这种垂直的指挥体系里,揣摩上意造成的。
我们这几年这种案例比比皆是。企业中如此,社会中也如此。在一个垂直社会里,揣摩上意,会让所有专业人士失去判断力的,甚至他不说专业的话。我们投资人,或者经济工作者,其实有基本的商业常识的。但是出现很多违反商业常识的事,你会觉得很沮丧很悲观。这种沮丧悲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你在企业中也是这样,你明明让员工做某件事情,结果他事与愿违,都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正如我今天的标题,所以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这些都是“荒草”实际上没有挡住我们前往“春天”的路。

今天因为涉及到我们讲投资,所以我在这里讲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对同一个标的来说,不同人性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做权益类市场总体上来说,要相信人类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时间是朋友。那如果你是做对冲基金的,那你的人性因素可以不在乎明天比今天好,不好也可以,好也更好。你可以不作任何预测。所以人性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后面要讲的假设前提之一。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期。乐观人看到的是转型期巨大的机会,悲观的人看到的是转型期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所以对同一件事情,取决于你人性的看法。投资也是这样。这是一点。
第二点,一般而言,我们每天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每月都要遇到从来没遇到的事情。
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从来都存在的。
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我经常说投资考虑问题你要四个维度放在一起:趋势还是周期?信号还是噪音?同样一件事情发生,比方说美国加息,有的人会把它看成信号,有的人会它看成噪音;有的人可以把它看成趋势,有的人只是看到一个周期。这两个维度下面,你再去考虑社会是出现恐慌还是贪婪状态,最后的维度是价值和价格,你的评判。
对一个长线的投资来说,不改变是投资的朋友。
巴菲特说的,我希望把所有不可预测是事情留给别人,不留给自己。所以稍微长远投资来说,他希望是不改变的,希望我吃的口香糖, 5年以后还是这个味道;希望喝的可口可乐,口味10年以后还是这个口味,不会变的。
不改变才是投资的朋友,改变是社会的朋友。因为改变可以带来很多商业的变化,产品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好的,对于社会来说是好的。比方说互联网,互联网的改变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是降低他利润的。所以在股市里,我们稍微扯开一点的,我们是需要有投机力量的,没有投机就没有改变。如果一个市场整天要求你做价值投资,不让你做投机的话,社会就不会有创新,社会是不会有改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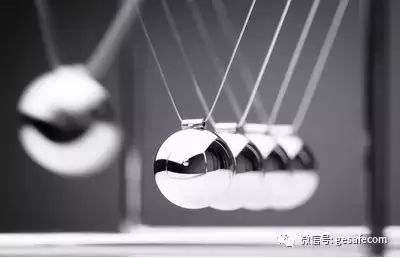
经济转型的冲击因素
以上是我今天讲的第一部分,对目前市场情绪的探讨。第二部分是经济转型的冲击因素。
经济转型对中国的冲击其实是挺大的,但这是必然的。我认为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萧条是对过去繁荣的惩罚。
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3年使用水泥的总量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世纪使用的量(数字来源:《材料简史及材料未来:材料减量化新趋势》)。2011年到2013年我们水泥的使用总量是66亿吨,美国在过去100年,1901年到2000年使用的水泥才45亿吨。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就可以清楚的了解,我们过去那样的发展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方面,我们过去很多政策,都是用来解决燃眉之急的。
我们企业经营方面,很多企业家都是短期化,功利性、投机性思维,习惯短缺经济下的经营。
董明珠说,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将消费者需求作为概念,放大来欺骗消费者。这是讲以前中国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如果可持续,那天理难容。所以对这些企业的冲击是必然的,很多企业在生产产品,明知存在缺陷,甚至有社会危害的情况下也会推向市场,这怎么可能可持续呢?怎么可能不对他进行冲击呢?
我在13年内部讲话时就提到,中国正在开始结束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那些高污染、低人权、高能耗的企业,受到冲击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整个世界经济的版图、认识整个中国经济的版图。从哪个时点开始,只要绿色、低能耗、高技术的企业,其实从13年14年开始就逐步地走向坦途。所以中国的转型,对那些企业冲击的都是应该冲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过去如果大家情绪有不好的话,很多因素都来自于这方面。
我前几天和一个朋友交流,他说他们那里关了几千家企业,他日子非常好过,利润不断上升。我说那关了几千家企业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吗?他说对社会太大影响没有,第一,那几千家企业可能是很多人失业了,但是我们利润提高了很多,税收增加了很多。我们增加的这些税收解决那些失业的问题也是可行的。真正的不得意的是那些无良的企业主,因为他们受到了影响。这就是整个社会在这个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飞机、火车、出门旅行仍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个社会在重整。

冲击这边我就不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机会。我对未来是很乐观的,对未来5到10年。原因很简单,我们60后是2.2亿人,70后是2.2亿人,80后也是2.2亿人,90后1.7亿人,00后是1.5亿人。
我们整个社会已经或者即将进入70后80后走向主战场的经济。
不管是作为创业者、劳动者还是消费者。这样的一个群体,不管从他的经济实力、知识结构,他的素质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跟高博讨论过,我说我在北大刚进校的时候,每个月担心的是到月末粮票不够用,怕吃不饱,粮票一直用到92年。我们60后是这样一代人,小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我75年上学的时候,天天喊“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坏坏坏”。我们小时候没有好好受教育,上街搞这种运动的。那70后80后,无论是经济基础、无论是学识、无论是素质、无论是社会给的舞台,都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对未来的10年很乐观。基础就是这个人口基数。至于20年以后,咱们可以做预测,
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相当悲观。
到00后、10后作为社会主战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4、5亿人要养多少65岁以上的人。宏观经济增长到那一天会结束,除非机器人、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机器人比得过30个现在的人,50个100个都可能。但是从人均的角度来说,到那点压力非常大,这是宏观层面。微观层面没问题,微观层面就是说哪个年龄段的人还有1.5亿的人。宏观层面20年后是不乐观的,但是未来5到10年可以非常乐观。

我们五代人不同的创业观,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有次演讲的时候某个人说的,我把他罗列一下, 50后说我做你们的顾问;60后说世界上有很多低成本的钱、先进的企业,中国未来是全球最大的中产市场; 70后说未来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抓住机会适应社会,80后说移动互联网世界有很多机会,很多痛点要解决,满足小痛点成就大未来;90后说互联网思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互联网时代;00后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长大后存在什么社会我们真不知道,也许他们身边有很多栩栩如生的机器人陪伴着他。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口结构,我们从微观上去分析,还是有很多变化的。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现在为止仍然是很穷。
所以小康梦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到处在开会,到处有论坛,到处有读书会,现在年末走到哪里都是。其他国家也有,但没有中国这么多。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我们前面说了,我们有足够的人群追求有品质的生活,消费升级动力非常非常强劲。
我这里有一张图,我们有两个发动机,一个是消费拉动,一个是技术革命。这两个发动机足以把我们从一个传统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经济。
我们从总体的结构上来说,我们很多人刚刚结束温饱状态,我们仍然有更美好生活的需求。
消费升级仍然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所以从经济上来说,我是60后,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70后、80后的,60后的企业家我现在打交道的比例急速的下降,新一代已经快速成长起来。还有我们中国这个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决定中国的产业是多样化、多场景、多系统的。我们的新技术有特别特别多的应用场景。技术使用最重要的不是说技术本身,它要有好的应用场景。这是为什么很多技术能在中国迅速推广的原因。我今年去剑桥呆过几天,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英国基础的研究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突破,很多最初来自于英国。但是他那些技术应用场景不够,到最后不是被美国买了,就是卖给其他国家。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案例。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有这些应用场景,技术可以得到迅速的推广。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中国即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3%到4%,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将能产生大量的经济需求。我们可以确信,未来10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这个第二大经济体,一定比当年日本第二大经济体要大的多。
高博刚才说了汇率问题,汇率一定是个问题,
我们知道二级市场不能让某种预期形成,一旦让某种预期形成,价值就会暂时失去意义。
所以在二级市场里面,预期是最可怕的东西,预期的力量比价值本身的力量大。但是大家回过去看,我们汇率从8.28一直上升到6点多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了多少。汇率上升了50%,中国增长从占世界3%的出口,一直到14%。所以虽然汇率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不认为会最终影响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这样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企业家是大有可为的。
再一个,我们工业门类非常齐全,产业链非常完整,这样一个市场,使我们的韧性、弹性非常强。这就是这几年我们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始终能保持6%、7%的增速重要的因素。而且,我是非常认可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对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企业家来说,都是巨大的创造的机会。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运输方式、新的市场原料、新的组织方式在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层出不穷。我们绿色、低能耗、可持续的企业高速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屋内老人垂垂老矣,屋外孩子呱呱落地,你取决于怎么去看待。
这几天和美国出现很特殊的关系,其实我们强大的国防需求,对技术的提升、产业竞争提升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美国所有的技术进步来源之一就是国防研究。我第一次去美国,还是2000年前,我当时就感觉到这点。我们对中国创新要有信心,我今年去Google,我和一个同学在Google吃了饭,他就不想多聊,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听讲座。我说什么讲座?他说我们今天下午请了英国的一个教授做讲座。Google每天,只要是上班时间,每天都有一两个讲座。他们会请全球各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做讲座,然后所有的员工可以随便去听。我们现在很遗憾被封掉了,如果不封掉的话,我们进到那些网站,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讲座的。那天请的教授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创新的教授。他们那天那个讲座就是讲中国创新的,介绍里面就说中国创新是被其他国家所低估的,这就是他的结论,也是为什么google邀请他去讲。
麦肯锡的报告,其实非常清晰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在聚焦客户和效率创新方面,我们是有极大的优势的。这里面报告说了,我们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4倍的供应商体系,1亿5千万的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在效率驱动创新上,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约15%至20%的成本优势。但我们还需要在基础工程的创新和基础科学的创新方面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如医药研究,其实它一定是基于基础研究推动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医药方面的进步。医药一定不是相关关系,一定是要因果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的创新实际上目前也有很多方面在迎头赶上。因为我有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北大很多同学,09年10年回国,现在他们的企业状况非常好。从09年做到现在,他们的研究水平非常好。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别的证券公司的策略会,第一次是申万,06年,在那个会上我开玩笑说过,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对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原因不是因为独生子女不好,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没人传承,所以做企业的动力不一样。如果有几个孩子,从组合的角度来说,总有一个孩子喜欢父母创的企业。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万一他不喜欢,这个企业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现在,我们反过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创新创业非常的好,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独生子女只要出国读书的、工作研究的,他必然回来。极少数概率留在当地。也许他们回来只会住在北上广深、杭州这些地方,不会到其它地方去。他们回来有很多做基础研究的、很多做科研的,对中国下一步技术的基础研究会起很大的作用。这虽然有点胡乱联系,但是我自己的直觉判断是可行的。

还有一个的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的组织模式并没有形成顽固的根基,国内企业家的也没有严重的惯性和需要克服的思维习惯,在组织上我们是能够有很多创新的,这就是我们能够产生那么多互联网企业的组织上的因素。
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受一些书的影响,《从0到1》这本书对中国企业界的影响很大,但是我这么多年的结论,尤其我们做权益类投资的,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要反过来看问题。
0到1在中国其实并不难,但中国缺乏大量的把1做到n的企业家。
由于政治、历史、文化、制度,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社会心理的因素,我们缺乏能把1做到n的大量的企业家。因为那样的企业家是要有组织能力、分享精神,有很多很多要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中国做天使投资时,失败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讲供给侧改革,最大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创造供给企业家的环境,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提供就业、提供税收、解决社会问题真正的人是企业家。就连川普上台,他要做这样的工作,他如果不能创造美国大量企业家的涌现,他所有政策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要珍惜那些已经成功企业的。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过去这些年二级市场容易高估的原因之一。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仅以感情,而要以理智来判断。我们要通过洞察那些创造性的破坏和驱动力来看待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增长。

我想这两张图是很有意思的。1931年人们挤在伦敦街头看电视,因为我自己差不多经历过,我们当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我们镇上街上就这个场景,我在学校里那时候看女排夺冠时,都是一个电视,下面一排一排凳子,凳子上再站人上去。

这是微软1994年用33万张纸告诉世界,一张光盘容量比这33万张纸都多。我们现在连光盘都不用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改变是有利于社会的,但是改变不是投资的朋友。另外一点,连接全世界也是中国企业巨大的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统计一下日本过去20年涨的最好的公司的话,因为过去日本20年是衰退的,但有很多股票涨的非常好,其中有一部股票涨的非常好的,就是它业务在国际化、全球的公司。因为互联网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连接全球的机会。我们企业家要去想想,满足这50亿人群的消费,我们可以围绕这些消费可以有很多创造发明。
最后一部分是最近一些权益市场统计数据,不一定对,但数据都做了,因为我脑子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突然发现这些数据和我判断的吻合,所以强化了我有一些的观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起那个标题的原因。过去几年,中国在10年到16年之间,整个市场总市值的分布越来越倾向于业绩差的公司,扣非净利润2亿以下总市值公司的占比是越来越大的,融资买入额也体现投资资金的流向,整个市场剔除那些金融房地产的融资买入额,大幅集中在业绩较差的公司。即使看相对排名,也可以看出业绩前2%的公司融资买入额越来越低,中国整个资本市场从资金的使用效率来说是非常低的。从经济演变的角度来说,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周期的,看美国行业权重演变的图,在能源泡沫、还有互联网泡沫、还有金融危机时相关行业占比情况。
03年至今,中国行业资金占比变化,大家可以看见,中国金融行业的万德全指数的金融占比已经有所下降了,但是仍然还超过20%,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金融占比太大,这社会始终是两级分化的一个结果。也许可能是原因,但反正是一个问题。周期性行业的占比在08年之后持续下降,而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可选消费市值占比则不断在上升。这是一个过去总体的图表。总体股市上来说就是我们资金使用效率上其实是不高的。这里面就预示着,另外一些机会的开端。

总体上我认为做空力量已经变得比较迟钝。
比较迟钝的原因,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头条风险”,“标题风险”很多;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做空力量有时候可能是政策。因为各种政策实际上一直在希望这股市是不涨不跌,往上的冲动非常大,但是上去动不动就要给你一巴掌。资金供给整个非流通股的解禁压力就没有原来那么大,流通市值占比稳定在70%左右,趋于稳健的下降通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