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丨golo
童年的时光,在小屋飘香的炊烟当中悄然消逝,外公的身影也渐渐佝偻,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似乎也有许多的不能。
人间有味 | 连载18
我出生在余杭的一个小镇上,东苕溪正好经过我家门前,东流至太湖。说来奇怪,从小混迹在河边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吃水产,却偏爱山里珍味,这或许和我住在山里的外公有关。
小时候,每到清明,山里的杜鹃开得正旺,扫完墓,我总是央求母亲带我去外婆家,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外公一定在准备做豌豆糯米饭了。
清明时节,豌豆刚长出来,正是最嫩的时候。外婆带着我和表弟去地里采摘。细长的豆荚里裹着一颗颗珠圆玉润的小豌豆,每次我都忍不住扒开几个,将一把鲜嫩的豌豆塞进嘴里,咬破薄薄的外皮,清甜的汁水瞬间迸射出来,满满都是春天的味道。
摘完豌豆,我们就在溪边将豌豆洗净,一边等外公从山里挖笋回来。几个人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道,直到外公瘦小的身影挑着一个鼓鼓的蛇皮袋出现。
外公卸下蛇皮袋,倒出满满一堆的春笋,再从中翻捡出几根又大又白的,笋尖泛红,乌漆漆而又饱满的身子,加上被齐根截断,裸露在外的雪白根部,汁水饱满。
这是最好的春笋。
外婆心疼被挑出来的这几根笋,想着明天一早拿去街上卖掉。
“最好的不留给自己人,留给谁吃?”外公总是笑着这么说。外婆也就没话了。
佐料准备齐了,外公将笋去壳,洗净,切成丝,同刚摘来的豌豆一起放入糯米中,再切下一块肥瘦相间的咸肉,切成丝,洒在糯米上面,用以调味。然后盖上厚重的木质大锅盖,在灶膛里加入晒干的竹子,慢慢烹煮。
这时,我和表弟会算准时间,跑出去玩,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便回到灶膛边。
褪去剩余的火,焖上三四分钟。外公一把掀开锅盖,随着热腾腾的水汽,香味便一股脑地铺散开来。饱满的糯米粒泛着油光,夹带着白中透着金黄的笋片,冒着油的咸肉,以及镶嵌其中的豌豆,我和表弟不禁吞了口口水。
糯米饭以底下金黄的锅巴最为美味。外公拿起锅铲往下深深一铲,将糯米饭翻搅均匀,给我和表弟各自盛上满满一碗,里面夹着几块金黄的锅巴。
或是觉得大人们尚未过来,两个小孩却先吃了,有种偷吃的紧张感,我和表弟端着碗,一定要飞似的跑到屋后的小溪边,躲好,这才开吃。
不一会儿,一碗满满的糯米饭就见底了。待我和表弟都将最后一块锅巴慢慢嚼碎,咽下品完之后,忍不住慢慢回味齿间的留香,同时感受着胃部暖暖的充实感。
这时,小舅回来了,走过小溪,看到我们端着碗站在溪边。
“你们两个小鬼头,又在偷吃什么东西?”
我和表弟相视一下,赶紧一哄而散。
江南水网密布,浙北又多山地,延绵的山地不适合播种,也不像东北山林那般多山珍野味,那一个个隆起的小山包,除了竹子,啥也没有。一家人的生计,便全都指望着这一片竹林。
每年初春,是竹笋上市的季节,这对于山民来说是一笔稳固的收入。外公要跑遍一个个大小山头,每一步都弯着腰,低头仔细寻找隐蔽在满地竹叶下,才露出个小头的笋尖。外公扛着装满竹笋的编织袋,弯着腰几个小时,只希望编织袋能沉一些,再沉一些。
除了鲜嫩的竹笋,小山丘对于山民的馈赠远不止于此,但勤劳者得之。在外公的双手下,一把把竹扫帚,一个个竹编篓,竹椅、竹凳、竹篮、竹扁担,一切能用竹子编起来的,外公没有不会做的。甚至可以用竹子搭起大棚,铺上尼龙纸,种植起反季节蔬菜。在一个成年人弯腰才能进出的大棚里,外公往往一干便是一上午。
在那物资贫乏的山沟沟,外公硬是盖起了村里的第一幢砖瓦房,而且一盖还盖了俩,毕竟两个儿子都等着娶媳妇。
● ● ●
在儿时的我眼中,外公的无所不能,不只在于粗大双手摆弄下的精致物件,更在于锅中常年飘香的地道美食。
外公做的臭豆腐便是其中一绝。江浙的臭豆腐,不是街上卖的用油炸的,而是用腌制霉苋菜梗的汤水腌制的。
外公自幼丧母,少年丧父,独自在山里拉扯一个年幼的弟弟长大,一生勤俭,生平最爱吃的便是这霉苋菜梗。就算等到儿女们全都成家立业了,也不舍得享半点福。
外公常常去地里找来老苋菜,去叶留梗,洗净,切段,泡在水中一整天。外婆等不及,想要拿出来腌制,这时外公总会摆摆手,“莫急,莫急,再等等。”
等到水中微微出现气泡,菜梗端开裂时,外公捞出菜梗沥干水分。拌上适量的盐,然后密封在陶罐中两至三天,待菜梗中出现白沫,打开闻见一股霉臭的味道,这就成了。
中午,外公捞出霉好的菜梗,放在盘子里,淋上香油,再加入剁碎的红辣椒,上饭锅蒸熟。等到饭煮好,这霉苋菜也就蒸熟了。
腌制霉苋菜梗剩下的汁水,外公舍不得倒掉,这时候我最爱的臭豆腐就要上场了。
炎炎夏日里,每当我无精打采,食欲不振,外公就会问我:“臭豆腐要吃伐?”
我一听,立马直点头,“要要要哟。”
第二天一早,外公上街买来几块新鲜的老豆腐,放入腌制霉苋菜梗剩下的汁水中,密封几天,等到豆腐表面结出黄绿的一层外皮,臭豆腐便算是腌制好了。
用霉苋菜梗腌制臭豆腐,最操心的便是腌制时间,有时候精心料理,却往往适得其反,一如外公这一生,总在为别人操心,却得不到一句褒奖。
外公年轻时,父母早逝,独自一人将年幼的弟弟拉扯成人,操碎了心。等到弟弟成家立业,外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本以为日子就此安稳,没想到外公又被推举成了村长。村里事物繁杂,东家长李家短的,就算外公再操心尽力,也总有人不满意。
等外公的威望建立起来,村长逐渐当稳之后,外公的弟弟又意外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孤儿寡母,平日里全凭外公照顾。外公自己膝下还有三个子女,日子过得更加捉襟见肘。
外公生性好强,一生气便暴跳如雷。虽然这使他颇具威严,但也导致就算他尽心照顾两个侄儿,他们也对外公颇有怨言。甚至就连外公自己的两个儿子,外公给他们尽心尽力盖了房子,娶了媳妇,他们也成天嚷嚷着要分家,没有一句好话。
我母亲气不过,“这两间房都是你盖起来的,他们两个没出什么力,凭什么要一人分一间?”外公却只是坐在屋前,吧嗒吧嗒地抽着烟。
我母亲急了,“爸,你任由他们这样,分了家你们两个住哪呀?”
外婆则抽泣着埋怨道:“以前脾气那么大,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
外公猛地抬起头,瞪着眼对外婆吼:“你懂什么?他们要分家就让他们分,闹来闹去他们两个以后怎么在村里做人?”
最终,我的两个舅舅还是分了家。外公搬出了自已一手盖起来的两间砖瓦房,和外婆两个人,在后院砌了两间低矮的小屋,自己吃住。从头到尾,外公没有对两个儿子提过一句埋怨,只是变得沉默了许多,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容易发脾气了。
童年的时光,在小屋飘香的炊烟当中悄然消逝,外公的身影也渐渐佝偻,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似乎也有许多的不能。
● ● ●
等我上了初中,两个舅舅决定要盖新房,“咱爸妈这小屋子就推了,以后盖好了新房有的是地方住。”于是将两间老屋连同外公的小屋一起推倒,扩大面积,并排新造了两层洋房。洋房宽敞而又气派,我想这次外公总算是能够享福了。
可等到新房完工,我却发现大舅根本没有准备外公外婆的房间,好在小舅舅的新房里,还是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间。
没过几个月,两个舅舅因为院子的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人都继承了外公的暴脾气,又摔碗碟又甩脸的,我们在一旁不敢上前。最后还是外公过去拉架。不知怎么地,帮着大舅说了句话,小舅顿时火冒三丈,当即对外公吼道,“你觉得他好就跟他住吧,别住我的屋,两个老人一人养一个,妈就我来养,别说我不孝顺。”
这一下把外公呛得说不出话,大舅也一身不吭地回屋,重重地关上了门,将外公一个人晾在了院子里。
那天之后,外公自己偷偷砌了两间小屋,和我外婆两人,依旧一间做饭,一间睡觉。
外公新砌的小屋虽然狭小,但烟囱里飘起的炊烟,依旧是带着诱人的香味,童年也似乎不曾走远。
数九寒冬时,外公会亲手擀起面皮。
那时我正在念小学,每天要早起上学。往往天不亮,外公就会起床,和外婆两个人,在小屋昏黄的灯光下,擀好面皮,烧好水,下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外公家的厨房是独立在外面的单独一间,每次等到我起床,打开门,便会一溜烟地匆匆穿过江浙寒冬熬人的湿冷,一头扎进那弥漫着温热的水汽当中,闻到空气中诱人的食物香味,我便知道面条已经下好了。
白滑的面条上,覆盖着切得薄薄的笋片,浸泡着细细的冬菇,上面撒上几粒葱花,香气扑鼻。到面条吃尽,再喝一大口暖暖的面汤,足以抵挡骑自行车上学那一路的降霜。
外公的面条我从小学吃到初中,又从初中吃到高中。
等到了大学,从杭城到哈尔滨,30个小时的火车,回家的机会寥寥无几,外公的面条更是吃不到了。吃惯了水乡温润的菜系,东北凛冽的寒风以及厚重的口味敲打着我的味蕾,入学一个礼拜,我竟然开始怀念起高中食堂的饭菜。
本科快毕业时,我和一帮室友整天出去聚餐。饭桌上,一瓶接着一瓶吹着哈啤,撸着烤串,嘴里嚼着锅包肉的我,俨然一副东北汉子的模样。可是每每到深夜躺在床上,梦到的却是家乡鲜嫩、甜美的油焖笋,柔软、香滑的黄豆炒茭白,以及外公最拿手的豌豆糯米饭,记忆中的味道能把人在梦中馋醒。
大四上学期,我通过保研面试,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月,还未把这个喜讯告诉外公,外公病倒的噩耗却先一步传来了。
诊断结果是胰腺癌晚期,我从未想到癌症有一天会发生在他身上。但联想到外公这几年迅速苍老的容颜,日渐疲惫的身体,一切又似乎有迹可循。
外公剩下的两个多月是在痛苦的化疗当中度过的,吃不下饭,夜不能寐,身体更是骨瘦如柴。
母亲说,最后的那几天里,外公似乎精神了许多,也能进食了。在去世前第三天,外公竟然能够下地走路了。由于外公一直嚷要回家,医生批准了。
一回到家,外公便像个小孩一样,叫嚷着一定要吃西瓜。当时正是十月中旬,母亲特地去超市买来一个西瓜。外公兴奋地要剖开,拿起刀却使不出力气,只好让我母亲帮忙。母亲想帮外公把西瓜切成块,外公却眼巴巴地盯着整个西瓜,硬拿勺子自己吃。但是,吃了几口,外公就再也吃不下了。
过了两天,外公便在那低矮的小屋里去世了。
而今,外公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又从东北转战西北。
春节时,我回到外婆家,没有了外公的小屋,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显得昏暗而又落寞。外婆问我晚上想吃什么菜,几天来流连于满是油腻饭局的我,忽然好想吃多年前外公的那碗笋丝冬菇面。
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一碗,和外婆一起擀好面皮,烧开水,凭着两个人的记忆,先将肉片下锅爆炒,待肉片泛白,洒下笋丝翻炒,如此三两分钟便起锅。此时面条正要好,浇下笋丝肉片,熄火,倒入碗里,撒上葱花。
昏黄的灯光下,面条冒出腾腾的热气,外婆有些兴奋,“你快尝尝好吃伐?”我轻轻将面条搅开,夹起一大筷子,哧溜一口吃下,温暖的味道弥漫开来。
“好吃好吃。”我连连点头。
外婆欣慰地笑着说道:“等开春了,再给你做豌豆糯米饭,你最爱吃了。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回来啊。”
“到时候一定回来,我还要学呢,咱家的手艺可不能失传。”我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在外待上几年,但我知道,今后我只会越走越远。可能我偶尔还会回到江南水乡那个枇杷长巷,只是巷子一头那个翘着腿抽烟的老人,以及他亲手做的那些美味食物,却再也看不到,吃不到了。
我想,如果连外公的手艺都失传了,那外公就真的永远离开我的生活了。
编辑:任羽欣
“人间有味”系列长期征稿。欢迎大家写下你与某种食物相关的故事,在文末留言,或投稿至 [email protected],一经刊用,将提供千字800的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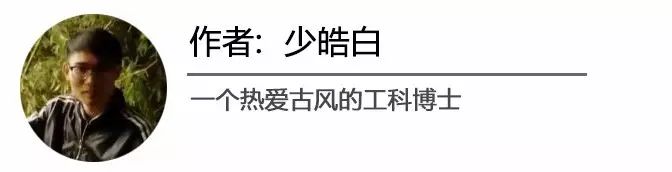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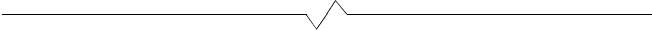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相关文章(点击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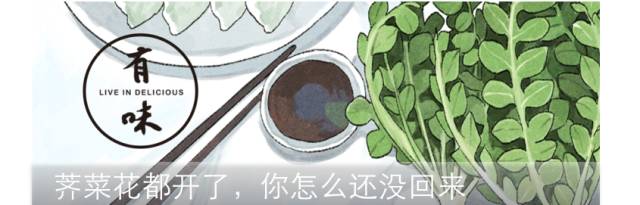

网易新闻 非虚构工作室
只为真的好故事
活 | 在 | 尘 | 世 | 看 | 见 | 人 | 间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坡井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年薪十二万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传销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血潮 | 失联 | 非洲 | 何黛 | 饥饿1960
毕节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空巢老人 | 马场的暗夜
行脚僧 | 失落东北 | 狱内“暴疯语” | 毒可乐杀人事件
打工者 | 中国巨婴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老嫖客 | 十年浩劫 | 中国版肖申克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北京地铁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