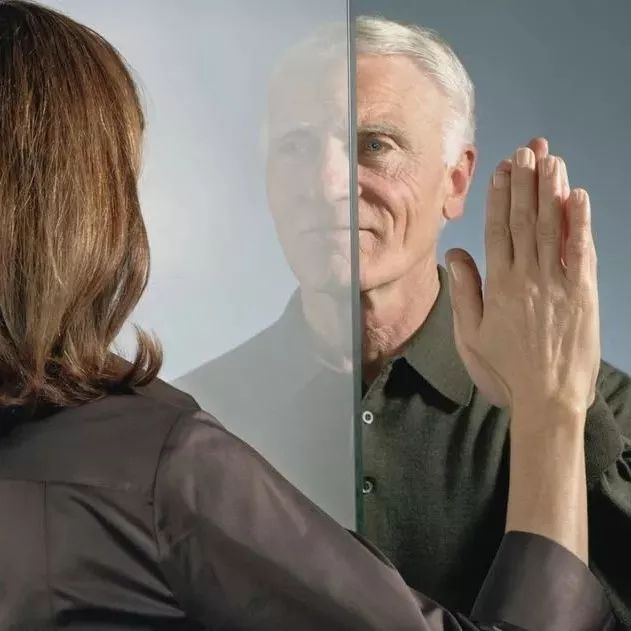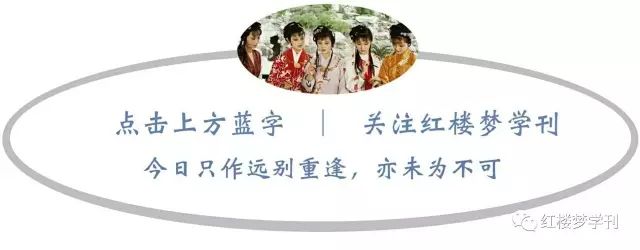

作者简介:刘上生,1943年生,江西新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已退休),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1993年出版)《走近曹雪芹——心理新诠》(1997年出版)《曹寅与曹雪芹》(2001年出版)等。
内容提要:“礼”“利”灭“情”,贾母之变导致黛玉之死。受传统婚姻制度观念及家族利益支配的家长意志及世态炎凉、情感阻隔诸因素复合叠加悲剧构想的突破意义。
一
“黛玉之死”历来是研红谈红的热门话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概而言之,大体有两种取向:
一种是“唯曹观”。因为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i]中的“黛玉之死”并非曹雪芹的原作,出于种种不满意,学者们热衷探佚,出现了一批探佚著作和以“脂批”为依据,重写“黛玉之死”的续红之作(小说影视)。
一种则是文本观。不论续作者是谁,从程高刻印本问世至今,绝大多数读者和文学评论者都认可“黛玉之死”的文本。许多人更是像笔者一样,以“黛玉之死”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为起点,产生了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终身热爱。这种震撼和感动,即使面对学界企图还原曹雪芹笔下的“黛玉之死”的热闹纷纭,也不曾改变。因为它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审美感受。
上述情况,深刻反映着《红楼梦》接受流传中学界与读者,探佚与欣赏,小众与大众的距离。专家们对后四十回的“黛玉之死”非议不止;民众则对探佚续写“黛玉之死”反应冷淡。学术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考证探佚,却很少有人研究后四十回“黛玉之死”的魅力所在,其结果,就是上述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红学研究也越来越脱离大众。
这种状况,很值得注意和思考。
笔者认为,由于续作“黛玉之死”是唯一流传的文本,而对立观点又聚焦于此,当前强调研读文本很有必要。当然这种研读,不能是“唯文本论”,必须吸收当代红学包括作者研究和探佚研究的成果。它主要应该回答两个问题:怎样客观评价续作“黛玉之死”的得失成败?怎样看待续作与原作(佚稿)的关系?
二
在讨论之前,先应该有一个共识。判断续作“黛玉之死”的成败得失,究竟是以其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为标准,还是以其为读者接受的思想艺术创造的成就为标准?回答无疑是后者。因为文学接受,归根结底是作品接受,而不是作家接受。当然,由于是续作,人们自然也期望与原作的衔接与吻合。但这是第二位的,不能是首要标准。
毫无疑问,续作“黛玉之死”并不符合曹雪芹原作的设计意图。第四十二回“钗黛和解”以后“金玉”几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也不成为宝黛钗之间的心理障碍。可是,“黛玉之死”恰恰由于“金玉”成婚而致。这一变化来自续作者的悲剧新构想。这一构想的中心,是要强化家长意志与自主爱情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扩展为包括家族利益、世态炎凉和当事人的情感隔离诸因素复合叠加的对爱情和生命的摧残,成为“悲剧中之悲剧”。
就回目而言,“黛玉之死”的完整过程应包括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三回。从情节脉络上,“黛玉之死”远接前八十回中第七十七回的“晴雯之死”,近承后四十回第八十二回的“潇湘噩梦”。如果说,“晴雯之死”只具有某种暗示性;那么,一进入后四十回,宝黛悲剧就开始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这是因为与前八十回的后半部重点写贾府盛衰而淡化爱情描写不同,续作艺术构思的重点转到了爱情描写,强化了爱情追求与家长意志的矛盾,特别是最高权威——贾母态度的变化被凸显出来。这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改变。贾母是父母双亡的黛玉的唯一血亲依靠,贾母之变直接导致黛玉之死。让曾经抱着“心肝肉儿”痛哭的外祖母成为罪人,这是与家族有着千丝万缕情感联系的原作者曹雪芹不忍做也无法做到的事,却成为了续作“黛玉之死”构想的最大突破。[ii]而这一转变过程,虽似突兀,却又合乎曹雪芹所强调的“事体情理”。
在前八十回,贾母对宝玉婚事的态度一直令人难以捉摸。尽管元妃和王夫人有明显撮合“金玉”的意图,但从第二十九回回答张道士提亲,到五十回向薛姨妈打听宝琴,想给宝玉说亲,老祖宗似乎都是在钗黛之外考虑未来孙媳的选项。这也许是她面对家族联姻和至爱亲情矛盾困境的策略性处置手段。正是这种模糊,给宝黛留下了微茫的希望。以至于第五十七回薛姨妈承诺向老太太提宝黛亲事,人们都充满期待。然而,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贾母曾不止一次当众夸奖宝钗,甚至有一次宝玉想有意引起贾母夸黛玉,贾母还是夸了宝钗(第三十五回),而这种夸奖林黛玉一次也没有得到过。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对女孩子爱情心理的抨击:“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虽然不是针对黛玉,但其表露的传统保守观念,与自由爱情尖锐对立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本质的对立,它暗示了宝黛恋爱绝不可能得到贾母保护支持。这些描写,为贾母态度变化——由模糊到明朗提供了事体情理的逻辑线索。第八十二回“潇湘噩梦”的意义,就是通过梦的预示性功能隐喻这一变化的严重性质。
贾母态度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家族利益与至爱亲情权衡的结果。贾母并不强调家族联姻,一再说不论对方家底贫富,这是与王夫人等倾心“金玉”不同之处。作为贾史两家联姻的代表,她长期撇开钗黛寻找未来孙媳,可能包含某种利益考量:不希望通过家族联姻造成别家(王家薛家)独大的局面。她强调的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二十九回)“姑娘的脾性儿好”(第八十四回),即有符合传统闺范适应环境要求的“性格”“脾性”。在这方面,“孤高自许”的而又病体恹恹的黛玉显然不合要求。在对外寻找无果后,舍黛取钗已成必然之势:
“我看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那给人家做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
(第八十四回)
“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
(第九十回)
从贾母的观念、地位和家族责任看,她的认识无可厚非。一直回避“金玉联姻”的贾母表示了对“金玉”的认同,贾府家长们对宝玉婚事的意见取得了完全一致,并背着宝黛开始议婚,这使宝黛爱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另一方面看,宝黛却从未改变被动依附的态度,贾母的宠爱一直是他们唯一的亲情和精神依靠,这种依靠至此完全崩塌。而黛玉对婚姻前途疑虑重重,对外来信息高度敏感,以致出现“绝粒”这样暴露内心隐秘的事件,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心重”“病重”都强化了贾母对她的疏离嫌弃,并且多次表露于言辞态度,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亲情销蚀殆尽,爱情面临危机。一场爱情追求者与婚姻决定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已不可避免。

三
宝黛悲剧不是孤立发生的,围绕着最后一搏,作者描写了一系列事件:元妃薨逝,薛蟠出事,王子腾病死,贾政升官外差,宝玉失玉,使家族联姻有着更大的紧迫性。
宝玉失玉疯癫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设计。续作者显然从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宝玉通灵受到启发,意识到通灵宝玉对于贾宝玉肉体和精神生命的“命根子”意义。这一情节几乎贯串第九十四回以后直到书末,首先作用于宝玉婚事。失玉使宝玉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和反应能力,并且病势日重。为了便于看护,宝玉被移出了大观园,从此与黛玉隔离。黛玉不了解失玉对宝玉的严重影响,完全失去了与宝玉沟通情感的机会。
失玉疯癫的另一后果,是促使贾府家长们加快实现“金玉”联姻为宝玉“冲喜”,尽管正处于元妃国丧期间,只能完成一个仪式,还使薛家和宝钗蒙受屈辱,但却必须服从保宝玉这一更高利益。元春薨逝已使贾府失去政治靠山,宝玉生命和婚姻更成为家族未来血缘所系。从袭人进言透露的爱情信息中,贾府家长们已经估计到他们强行完成的“金玉”联姻,是对贾宝玉追求爱情幸福权利的剥夺,并将导致他所至爱的林黛玉的死亡。但在他们的观念里,家族利益高于一切,恋爱非礼非法,黛玉生死已无足轻重。特别令人心寒的,是“金玉”成婚消息走漏,导致黛玉吐血病势加重。贾母前来探望,贾琏请医生看视。王大夫说:“尚不妨事。这是郁气伤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气不定。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方可望好。”既有希望,贾母却不尽力诊治,而是对凤姐等说:
“我看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冲一冲。或者好了,岂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么样,也不至临时忙乱。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
这番话表明她已把林黛玉从“咱们家里”剔除出去,并提前宣判了黛玉的死刑。聪明的黛玉早已感受到这种冷酷无情。当他喘吁吁地说完“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果然慈祥的外祖母就打算彻底抛弃林黛玉了:
“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第九十七回)
在家族的“礼”与“利”面前,亲情已不堪一击,爱情则是不可饶恕之罪。因为宝黛之爱已背离了家族期望的轨道。黛玉无疑成为了家族利益的障碍,贾府家长决心用黛玉的生命换取他们所期待的宝玉婚姻和家族幸福。
由于宝黛这对恋人心心相印,宝玉的任情任性和对黛玉的痴恋,以及宝黛与贾母的亲情关系,贾府家长要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可能引起强烈的反抗和严重后果。为此,他们利用宝玉失玉呆傻的机会,让凤姐设计了“调包计”,完全欺骗宝玉,又瞒住黛玉,同时把宝钗作为顶替工具,达到造成既成事实,使宝玉无法反抗和改变的目的。但由于消息走漏,黛玉知情而宝玉不知,使黛玉产生对宝玉背弃爱情的极大误解和怨恨。敏感的黛玉本来就对多情而软弱的宝玉无法完全释然,第八十二回梦中的宝玉剖心,第九十一回的疑阵谈禅本质上都是心灵试探,一个弱势女子对男权的潜意识疑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黛玉最需要的是不断的情感沟通交流。宝黛爱情本来是在不断的情感沟通和纠结中走向成熟的,然而,贾府家长借失玉制造的情感阻隔却从根本上窒息了有情人的生命通道,误解无从解释,阴谋借以得逞。其结果,贾府家长们最害怕的宝黛联手反抗或双双殉情的局面没有出现,“金玉”联姻成功,一对生死情侣关键时刻分手,由黛玉一人承担亲情彻底冷漠、婚姻期待破灭、爱情被抛弃毁灭的全部痛苦。爱情追求者与婚姻决定者的冲突,竟然转化为爱情追求者自身的情感怨恨,而且由于生死睽隔永远无法化解。
令黛玉无法承受的,还不止是贾府家长的绝情,误解中宝玉的背弃,还有面对的世态势利冷漠。“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自尊的黛玉本来就对寄人篱下的身份处境特别敏感,从刚来不久的送宫花事件(第八回),宝钗送燕窝前的倾诉(第四十五回),到“惊噩梦”中“平时和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的感悟和误听婆子骂人后的晕倒(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三回),可以看到她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贾母态度明显变化之后,整个贾府上下都看老祖宗的脸色行事,如果不是傻大姐泄密,没有谁向潇湘馆透露“金玉”联姻的消息;就连颇有同情心的鸳鸯,也懒于向贾母报告黛玉日趋严重的病况;病危之时,林之孝家的还威逼紫鹃去做伴娘欺骗宝玉,以讨好贾母:
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今见贾府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自知万无生理……
黛玉几乎被整个世界抛弃,这是足以摧毁一切生命热力的凛冽冰霜。
四
家长权力意志,和由此导致的贾府的世态炎凉,恋爱者之间的情感阻隔,如三座大山,是柔弱病重的黛玉的不堪承受之重。尽管黛玉并没有像“绝粒”(第八十九回)那样自戕其身,贾府表面上也没有断绝医药料理,但面对绝望的世界,她的病体和精神生命都已无法支撑。人们谴责贾母,王夫人,凤姐甚至宝钗,然而她们之所作为,都是为了维护没落家族命运之所需,并且是在那个时代规定的正常伦理和人际关系秩序中实行和完成的。
王国维正是在《红楼梦评论》中分析一百二十回本的“黛玉之死”时,提出了《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的著名论断。他说:
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期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iii]
这种“悲剧中之悲剧”的意义,正在于对社会世俗认可的“通常之道德”“人情”“境遇”的暴露和批判。
在没有爱情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父母之命”对当事人情感意愿的剥夺是造成爱情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的儒家孝道文化又强化了对当事人的压力。现代社会虽然恋爱婚姻自主已经实现,但从“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两个家庭的联姻,家庭利益和家长意志还是起着重要作用。决定家长意志的则是传统婚姻制度和观念之“礼”和家族利益之“利”,它们共同形成对“情”的压迫,不但压迫当事人的爱情,还改变和销蚀家长的亲情,使之变得冷酷无情。慈爱的贾母就这样沦落成为黛玉之死的罪人。“礼”“利”灭“情”,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人世命题。除了家长意志,传统婚姻制度和观念还外化为环境压迫,通过世态人情以至当事人的内心冲突作用于爱情追求者。续作“黛玉之死”强化了家长意志与自主爱情的冲突,同时融合了家族利益,人情世态和当事人的情感隔离多种因素,几乎概括了人类爱情婚姻悲剧的基本类型内容,又提供了特别适合当时和后代接受语境的悲剧话语,这就很容易引起处在现实相似语境下各种遭遇的青年男女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