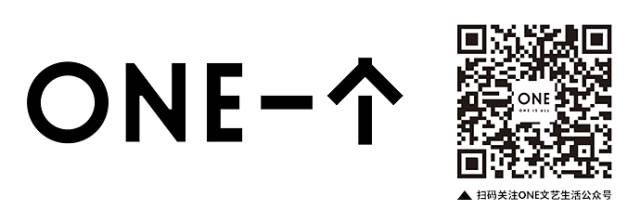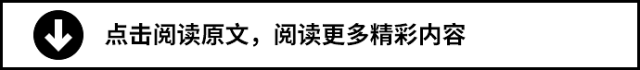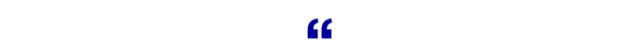
我仰头喝光了酒,那一刻,真想马上回到北京,回到我还没被击碎的人生中去。


每当回想起二十三岁的那一天,我都会怀疑它是否真的值得被纪念。
大概就像身体里的细胞,单一存在时不具备任何意义,只有经过亿万次的复制粘贴,如同沙丁鱼迁徙一般大规模地跋山涉水,最终栖息在某个重要位置,能够维持皮肤光洁如新,支撑眼球周转、嗅觉灵敏,或是长期负责手指的灵活,诸如此类,它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无论是这些时刻发生的当时,或者运转直到死去,没有任何一个细胞会被保留、记录、命名。
而那一天,不过碰巧是我另一段人生的开始,它就像一个开关。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开关的命运,它被销毁、弃置,还是装在盒子里小心收藏,都不会阻碍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如期发生。
大学毕业,面对两个同样糟糕的机会——要么去有着庞大对韩业务的航运公司做翻译,要么去三线城市的高中职业学校当韩语老师,我选择了回家待业。八个月后,除了二十四斤多余的脂肪,我一无所获。
回到北京,我投了五十份简历,用仅剩的钱租了一个不到十五平的房间,窗户朝北,每天只有下午两点多晒得到太阳,晚上盖两层被子还是冷得睡不着,短短半个月就挂上了再也没能消下去的黑眼圈,去面试时总被误认为经常熬夜。
E&M的面试官在诸多同行中显得尤为不同,一边说“这样你就不用重新适应我们公司的节奏了”,一边非常愉快地在我的面试评估表上签了字。我大概是被她职业性的“nice”打动,在第二天就迅速入职,成为了这家韩国娱乐公司中国分公司电影分部的项目专员。
一个冗长的、面目模糊的、看上去像那么回事的职位,但仅仅是看上去。
当时我并不知道,所谓项目专员,大概就跟实习生差不多,只要对方能接受低廉的薪资,什么人都可以。
我成了那个“什么人”,却连复印这样的事也不如实习生做得熟练,谁也不愿意委派给我任何工作。第一周的KPI考核,满分是10分,我只拿到0.9分,这点可怜的分数还是来自按时出勤。
在接到离职警告后,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组长,他让我负责监控所有进行中项目的数据,每日更新并向他汇报。数据截止时间是晚上十二点,这意味着我必须凌晨加班,在平均五个小时的睡眠后,照样爬起来去上班,打着哈欠,无事可做。
两年后,在一次中韩电影论坛活动中,我碰到了这位仅仅共事三周的组长。他开玩笑似的告诉我,他从未打开那些邮件,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我的KPI关联着整个组的奖金。我说,可我就是那样才留了下来,不是么?他拍拍我的肩,意味深长地说,你看,人生总是这样,我们都没有选择。
怎么不去死、我也无所谓、祝你好运,三句话依次出现,我却只说了再见。我当然明白,那时候,我的工作愉悦感不值得被任何人放在眼里。
那年北京的倒春寒格外漫长,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忍着困倦勉强上班。某天打着呵欠路过会议室,门突然从里面被撞开,一个看上去十分焦躁的男人探出头来,从上到下迅速扫了我一眼。
他问我,在这里最快多久能找到一个会韩语的人?
我想了想,说,或许……我就可以试试。
我被他一把拉进会议室,里面烟雾缭绕,正处于一场会议的中场休息时间。桌子周围坐着七八个人,全都表情严肃,眉头紧锁,小声讨论要如何说服导演同意删掉电影里一分钟暴力血腥戏份的事,这一分钟来自由我们公司引进国内、两周后就要在院线上映的韩国电影《末日列车》。
将我拉进来的男人跟我解释,他们请的翻译临时请假了,现场没有人会韩语,导演坚持要保留这一分钟,但我们无法抗拒审查意见,需要我做个临时翻译,跟导演沟通。
电话迅速被接通,我替在场的人们简略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当导演听到“必须删掉一分钟”时,马上打断我,激动地说,必须删掉一分钟的理由是什么?我重复了一遍,太过血腥暴力,不符合我国……
他再次打断我,大吼,我不相信你们的观众连基本的真实都承受不了!
我手里已经没有别的安排好的话可说,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争执起来,我说这就是争取中国市场要做的妥协,您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一分钟,就失去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机会等等。
然而我那幼稚的、书面化的理由并不能够打动他,导演撂下一句,如果一定要删,那就别上映了!对话彻底陷入僵局。
导演的声音被功放出来,沙哑、疲惫、歇斯底里,像是蹲在角落里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可他的一字一句,却变成砸在墙上的拳头,遗留的力量还在空气里回荡。
公司花了不少力气和钱,才买下这部电影的国内发行权。在我翻译完最后一句话之后,会议桌上再次掀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讨论,不时扫过我的目光中透着责备的意思。
曾孟川推门进来,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搞砸了,差一点就要哭出来。
他用流利的韩语安抚了导演,紧接着却问,说干脆别上映,您一定是开玩笑的吧。
导演没说话,似乎是默认。曾孟川话锋一转,说,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选择,是删掉二十二分钟涉及极端国家意识形态的戏。如果您觉得一分钟的删减和二十二分钟的删减同样不能容忍,那么从排片的角度考虑,我们现在建议删掉更长的。
电话那头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屋子里的人也被隐形的紧张感钳制着。摆在面前的,要么努力说服导演,要么继续跟审查部门僵持、对峙、博弈,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让人感到轻松。
不知道过了多久,导演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同意了删减一分钟。
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知道,那二十二分钟早在第一次审查部门给出意见时,就被公司说服通过了。曾孟川将它搬出来,不过是给导演一个不得不妥协的理由。
《末日列车》上映前,公司为这位导演做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小型影展,专门放映他此前的作品。我被意外调入影展临时事务小组,组长是曾孟川,他安排我在放映现场拍字幕。
这算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接手的第一件正式工作,我生怕出错,精神高度紧张,最后一天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还剩最后一场时,我走出放映厅透气,双脚发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
曾孟川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塞给我一个面包,问我要不要进去看一场?不用干活的那种。
我不解,反问他,为什么?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他摇摇头,看你这样,怕出错,我安排别人了。你的下一个工作就是看电影,走吧。
回到放映厅,曾孟川跟我一起坐在最后一排。他开玩笑说,很久没跟女孩一起看电影了,感觉还不错。
可惜了,这电影叫《杀人回忆》,不怎么适合跟女孩看。
现在嘴挺利,怎么那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转头看我,我避开他的目光,不敢再说什么。
他却正色道,我准备离职了,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为什么?我不解。
我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找我?那天我可是差点把事情搞砸了。
那天,我让他们找一个会韩语的人,并没有打算让这个人解决问题,只要在我来之前拖住导演,让会议进行下去就可以了,你不是做到了吗?
直到真正离职的时候,我才从别人口里得知,曾孟川带我走,是因为有经验的人全都不肯跟他离开。他年轻,能力又突出,绝不可能留给团队太多的机会,无论是谁,注定都是为他作嫁衣罢了。可对那时的我来说,哪怕只是一个为别人作嫁衣的机会,也理当珍惜。
我作为曾孟川团队的一员入职新公司,却丝毫不知道,他前来任职前就谈好的两个筹码——以不可思议的低价拿下了日本一部当红悬疑推理小说和一个经典系列漫画的影视改编权,不知是在何时完成的。
不久之后,这位小说作者的其他作品被中国各家同行迅速瓜分,但因为水涨船高,其他人成交的价格都是曾孟川谈判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之高。而那个系列漫画,也很快被某新晋知名导演相中,主动上门合作,迅速开始筹备。
公司强行塞了一队老员工跟曾孟川一起工作,并以精简项目组为由,强行将他唯一带来的人——即缺乏经验的我,踢出了团队。在他连续几个月去韩国出差期间,我被调去做字幕翻译。
夏天最热的时候,我披着毛毯通宵坐在机房里赶工,听着三台电脑一台空调轰隆隆运转的声音,不记得一晚上要喝掉几罐咖啡,又要趴在桌子上睡着几次,再醒来几次。等到早上离开的时候,肩膀僵硬得像是刚从冷冻柜里拿出来的生肉,胃里像有一台默默运作的绞肉机,它们却无法彼此消解。
当没有字幕需要翻译的时候,公司就差我去盯成片校正,跑腿送审,并在最终一遍一遍地核查各类错误,包括穿帮镜头、跳帧、漏词错字等等。如果不巧是韩国方面负责制作,还需要充当“人肉闪送”,一天之内往返首尔和北京,连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都赶不及。
看上去,我就跟所有人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每个月不定期出差,吃过公司楼下早晨六点才出摊的小馄饨,坐过北京机场当日离港的最后一班飞机,见过刚露头的太阳。可我做过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没有任何人会记得。
偶尔在公司碰到曾孟川,他忙得连走路时都在同时打电话和编辑邮件。只来得及问我一句“最近怎么样”,下一个电话就马上打了进来,我只能把那句“不怎么样”再吞回去。
七个月后,我终于决定辞职,给曾孟川发了邮件,算是走形式,也是打招呼,感谢与抱怨藏在字里行间,不是非让他了解透彻不可。
当天下午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刚回北京,约我下班一起吃饭,他说,你要走,我得跟你吃顿散伙饭,应酬已经推了,你可别拒绝。
他带我去吃川菜,是一间藏在安定门胡同里的脏馆子,远远就能闻到掺着辣的烟火味儿。据说门口常年坐着一排人等位,高峰期能持续到晚上十点。
几个菜上来,我各尝了一口,迅速灌了半杯酸梅汤下肚,辣得直喘气。他跟我说,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不能吃辣。
他穿着西装,对着一盆毛血旺大快朵颐,像是走错了片场的演员。
我摇摇头,说,没事。反问他,看不出来,你是四川人啊。
他说,也不算,我爸四川人,我妈韩国人,后来,我妈习惯待在四川,三天不打麻将就浑身不舒服,闻不着火锅味觉都睡不着。我爸呢,自从被调到釜山,就没怎么回来过,过得也挺自在。
所以他俩?
分居很久了,一个不想回来,一个不想回去,只是没人提离婚罢了。
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像是信手拈来一段别人的故事。我却最怕在天将黑的时候,听别人敞开心扉。我打断他,先声明,我不可能因为你分享了一段身世就留下,说白了这跟我没关系。
他放下筷子,说,你放心,留你的话,吃完饭再说。
晚上十点,我跟曾孟川坐在团结湖公园门口,陪他理发。
那是个露天的、格外单薄的理发摊,只有一个铁皮凳子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师傅话不多,只问剪到哪儿,比划两下,迎着路灯的光就开始“咔嚓咔嚓”地干活。
我问曾孟川,为什么非得来这儿?
我头发长得快,半个月就得收拾一次,刚来北京的时候,只在这儿剪得起。那时候是真穷,去菜市场买两条排骨都心疼,好不容易下决心买了,刚回家就被叫去加班,排骨忘了放进冰箱,等半夜回来一看,早就馊了。
我没吱声,他看着我,把手搭在我肩上,拍了拍。
我知道你不好过,你是我带来的,我该负责。我也真不是那种,只顾着自己混好的人。前段日子自身难保,你再等等,我争取给你一个项目独立负责,如何?
我没被他的苦日子打动,也不算真正相信他说的话,可他拍我那两下,却是真的难受。这座城市太大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辨认不出该往哪里走,难过在夜里随便就哭掉了,没有人知道它来过。
我被重新调回曾孟川手下,工位跟他的办公室隔着一道玻璃墙。
他很少迟到,哪怕公司并没有对穿着提出任何要求,也一贯保持可以妥帖见客的样子。从早到晚,数不清他的办公室里来来往往多少人,大概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他会挽起衬衫袖子,露出一些疲惫来。
跟他一起工作,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待遇。而对我,甚至是格外苛刻的。许多次开会,我准备的内容被他批得体无完肤,开始时还会因此惭愧得面红耳赤。后来习惯了,就会厚着脸皮跟他争执,直到有一次,终于说服了他,我拿着自己的提案,跨越半个北京城,跑到顺义,独自谈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项目。
春节前的最后一周,公司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的行程被工作耽搁,甚至加班比往常还要凶猛。那天晚上做完ppt,已经十一点半了。回头才发现,曾孟川也还在加班。我把ppt发给他,蹑手蹑脚地准备走,他敲了敲玻璃墙,让我看邮件。
我打开邮箱,他回复我的是: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转头,他露出极少见的轻松表情,站在那儿歪着头等我。
北京有许多开到三更半夜的火锅店,无论几点,都人声鼎沸。
我们吃到一半,碰上他的一群朋友。他们正好准备去附近喝酒续摊,叫曾孟川加入。我坚持要回家,但拗不过他非要让我“加完班放松一下”的提议,硬着头皮跟他一起去了。原本打算抿两口就走,却被不认识的人挨个灌了个遍,昏昏沉沉地醉倒在了沙发上。曾孟川大概也喝了不少,跑来坐在我旁边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话。
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身体的感觉是清晰的,牵引着记忆。
在开始头疼之后,有一瞬间非常想吐,他扶着我去了洗手间,在门口守着我,等我吐完一轮,帮我擦了嘴,还灌了一杯热水下肚。我难受地伏在他肩上,他拍着我的背,用我最怕的那种拍法,一下就把我拍哭了,于是他又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眼泪。最后只记得,他把我塞进到车里,关门前,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过年那几天,我们不动声色地给对方发“新年快乐”,在工作群里互相调侃、抢红包,直到回来上班,再见到彼此,也没有任何改变。
又一个春天来的时候,我终于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进组,跟着剧组跑到冷飕飕的青岛,一呆就是三个月。
那也是一部中韩合拍片,剧组里同时能听到韩语、粤语、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不拍戏的时候一团和气,简直是一个多语言交互学习班。可当一个镜头拍了二三十条还过不了时,韩国导演会气得跳脚,然后手舞足蹈地跟台湾演员讲戏,演员却一知半解,来自香港的摄影指导在一旁直摇头。因此耽误了收工,灯光、造型、道具,各个岗位干活的人都一肚子埋怨。片场像是闷了一口气,风雨欲来。
而我,因为制片人前面有了“执行”二字,也就比打杂的优渥一点儿,每当这种时候,夹在制作团队、公司、演员各方之间,想要推动进度,就得轮番劝说,实则领受所有人的气,在精神上还不如打杂的。
杀青后,剧组在北京郊区补拍零星镜头。曾孟川来探班时,演员还在绿幕前吊着威亚,他带给我的消息却是,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将无限推迟。理由很简单,女主角参演的两部电影前不久均以惨淡票房收场,男主角又惹上了出轨丑闻,如按照原计划在年内上映,想想也知道只会是个糟糕结果。
他最后留给我的一句话是,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上,无论如何先拍完再说。转身就上了那辆GL8,甚至没去拍摄现场瞧一眼。我不明白,他是如何变得如此冷酷无情的呢?又或者他一直如此,我只是将偶然的温柔错当成日常。
回到公司以后,我正式接到该项目暂停推进的指令。而要执行这个指令,无非是面对一系列关于合同、协议、原定计划的撕扯。其中,早在开拍前就签了约的宣传公司,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的工作,并且垫付了不少费用。但因为这部电影还没有宣发预算,甚至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笔预算了,跟他们的款项结算,就变得格外艰难。
对方至少一天三个电话催我,作为我的上级,曾孟川却三番两次地将我的付款申请驳回。一气之下,我把催款电话转接到了他手机上。他不知情,大概是接起来习惯性地先做了自我介绍,对方积累了多日怨气,索性变本加厉地开骂。曾孟川打开办公室的门叫我进去的时候,功放里的难听话穿透走廊,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
等对方撂了电话,他问我,这下满意了?
我否认,说,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也不容易。
曾孟川不屑地笑了笑,跟我絮叨了一遍他今天所有要开的会、要处理的事情,反问我,所以你觉得我就容易了?我说过,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给你这个项目,它变成什么样你都得管到底,我又从来没保证过,它一定会顺利上映,你有什么理由觉得委屈?
走进办公室之前,我正在打印辞职信。等曾孟川说完,我将辞职信放在他桌上,请他准许我离开,当然,同时希望他也能顺便通过付款申请。
曾孟川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一个说“不行”的台阶都没留给他。他背对着我,明显看得出很生气的样子,迅速在辞职信和付款申请上都签了字,扔了笔,用力把两张纸丢给我。
没有假惺惺的祝福,也真的没有丝毫挽留。
走出办公室,我不敢回头。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机辞职,他一定有办法轻易让我留下。可我们该告别了,哪怕是暂时的。
我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曾跟随曾孟川工作的履历,让我轻松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并且拿到了相当优渥的职位和待遇。
我学着他当年的样子,在做了充分的数据分析和背景调查之后,找到了此前他亲口拒绝过的一部电影,将制片方与现在的公司牵线,迅速签下合同,定档上映,变成我任职的筹码。
这部电影上映前的首映礼上,我特意邀请了曾孟川,我们仿佛只是许久未见的熟人,他礼貌地抱了抱我,问我,辛苦吧。
我回他,为自己做事,辛苦也值。
他笑了,带着些许讽刺,看来是埋怨我,以前对你不够好。
我说,怎么会呢,是你教了我太多,谢谢还来不及。
他有些要卸下伪装的意思,我赶紧转向另一人客套寒暄,等再回头,他已经不见了。女人是最奇怪的动物,明明想得到答案,却又怕猜错答案,于是宁愿始终忐忑。
电影上映后,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曾孟川特意发来邮件来恭喜我,我表示感谢,却很难不疑惑,又不是工作往来,干吗不发微信呢?
他回复,怕一发微信,就说多了。也怕有些事,你会怪我。
后来,当我去找这位导演聊下一个项目的时候,终于明白,曾孟川说的“有些事”是指什么。原来,他们见这部电影大卖,早已主动找上门,拿下了导演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出品合约。导演在咖啡厅跟我见面,诚恳地表达了歉意,虽然我们此前雪中送炭帮他拿下了现在的成绩,可曾孟川那边出的价格更高,他只是顺势而为。
我心平气和地喝完了咖啡,临走时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出去之后却直接杀去找曾孟川。再次站在那间办公室里,我劈头盖脸地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就像我辞职与他无关一样,他去谈项目,也与我无关,只是工作而已。
“只是工作而已”,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是啊,我走得毫无留恋,又怎么能指望他顾念旧情。
去年八月,“限韩令”传得沸沸扬扬,中韩合拍片的市场,一夜之间就变冷了。我们公司参与的一部合拍片,马上要签合同,迅速叫停止损,转而投入了跟香港导演以及一系列老牌电影公司的合作。
三年多来,我所积累的行业经验,也算能够彻底抵消最初入行时凭借的那点儿语言特长,成为了公司新业务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每周都要去香港出差。香港人有种天生的客气,开场的寒暄总是他们回忆哪一年来过北京,对风沙、干燥和雾霾印象深刻。习惯以后,我也会随着他们抱怨几句,顺便感慨每次来香港,一落地就觉得皮肤滑滑润润,就这样在双方都保持心情愉悦的时候,马上切入正题。
有一次,从香港回北京,不巧碰上航空管制,等了两小时才起飞,发了一条朋友圈,抱怨快要溺死在香港机场过分充足的冷气之中。落地一开机,却意外接到曾孟川的电话,他说,可算找到你了。
我问,怎么了?
我妈来北京,也晚点了,我要见一个重要的人,实在脱不开身去接她,不巧司机家里也有事,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你们落地时间差不多,就想拜托你,帮我这个荒谬的忙。
不好意思,我也觉得这很荒谬。
我打算挂电话,他在那边大声叫住我,认识这么久,就求你这一次,都不答应么?
我是禁不住拿感情深、时间长这种理由要挟的人,于是就答应了他。
出了到达口,凭借照片,我在咖啡厅找到了曾孟川的母亲。我惊叹于她的皮肤如此之好,根本看不出已经是年近六十的人。而我,假装是曾孟川的同事,顺路帮忙来接人,却被这位阿姨一眼识破,她说,孟川向来怕麻烦别人,肯定不会要求同事帮这么私人的忙,你一定是他的女朋友,对不对?
我差点脱口而出,也许曾经差点是了。可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那一瞬间,说不定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曾孟川的母亲跟他的性格很像,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我只能任由她误会,只求把她送到目的地就马上脱身。可谁知,曾孟川给我的地址,是他家附近一间可以吃宵夜的餐厅。他和他父亲早早地站在餐厅门口候着,下了车,顺手就迎着我一起往里走。我小声问他,这算什么?他连说抱歉,让我就当演场戏。于是,我就这样见证了他父母二十年来第一次正式谈离婚的过程。
没有想象中的不堪,甚至他母亲还亲热地问起他父亲在韩国相处多年的那位年轻女朋友,关心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我对此目瞪口呆,曾孟川却习以为常,他那晚穿着短裤拖鞋,只顾埋头啃兔头。饭局结束时,他爸妈约好明天上午十点去民政局办离婚,我陪曾孟川把两位送到各自的住处,陪他在路边抽了根烟。
他问我,婚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说,我还没经历,没有资格回答。
他又问,那你想结婚吗?
我假装无所谓地耸耸肩,叹了口气,说,先来个恋爱谈谈吧,我的生活,现在全是工作,都快枯燥死了。
我转过头,发现他正盯着我看。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藏在树叶深处的一双猫的眼睛。我被他看得发毛,生怕他问出什么逾越当下关系的问题,摆摆手赶紧走了。
第二天醒来,却又为自己的逃避感到一丝后悔。我发微信问他,离了吗?他说,没离,他爸睡过头了,他妈一气之下买了张票回成都,只有他在民政局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也不知道下次再离是什么时候了。
我脑海中浮现出他昨晚的那个问题,好像突然知道了,婚姻是怎样一种东西。
我和曾孟川断断续续地联系着,偶尔在同行的聚会中碰到,无论线上线下,我打招呼的方式固定为同一个问题——“所以,离了吗”。而问题的主人公,他的父母,非常稳定地保持着现状。
今年三月,我去香港参加电影节的活动,得知曾孟川也在,问他要不要见一面。他说,正好手里有两张开幕片的票,可以一起看。我没问他原本计划要一起看电影的人是谁,见面时,就像光明正大约会的情侣,他抱着爆米花和饮料等着我,我皱起眉头嘲笑他,都快三十的人了,还带爆米花进场。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上次跟我一起看电影时,忘记买了,这次就当补上。
他说的上次,还是四年前我们一起做影展的时候。我又怎么能想到,还有补救一盒爆米花的机会。那别的呢,还有机会缝补吗?
今年的开幕片,是一部香港爱情片,粤语。因为常年来港出差,我听起来倒不算费事,可曾孟川却是靠着字幕才看完了整部电影。
他说,这片子下个月要在内地上映,原声大家肯定嫌听不懂,配音又会少了很多乐趣,怎么都不对。我不解,当年韩国电影还不是全都原声上映,为什么换作香港,就一定强求要听懂。他说,不一样的,人们心理上觉得,香港人没什么不一样,所以对相应的语言,也格外缺乏宽容度。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就这样站在街边,讨论了许久。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们是可以做普通朋友的。可过马路时,人太多,我很自然地抓住了他的手臂,他反手握住我的手,到了马路对面也没有松开。我此时才知道,他落在我额头上的那个吻,从来都没有真正消失过,怎么做所谓的普通朋友。
三天后,我和曾孟川带着各自公司的电影在同一天开了发布会,记者们参加完上一场,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对面的酒店,继续出席下一场。时间错开固然容易,可版面只有那么大,谁上谁不上,难免要博弈一番,硝烟味顿时又浓重了起来。我们各自公关记者,钱和人情一个也没落下,当晚好不容易喘口气跑去茶餐厅吃饭,却发现大街小巷的电视上都在放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的双方是中国和韩国。在政局紧张的时候,一场球赛也有了别样的意味。此时不分香港北京,无论哪里都屏息凝神,祈求比赛的结果能够给人们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
我在茶餐厅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进球,也等到了比赛在1:0的比分中顺利结束。周围关注比赛的人都掩不住激动和喜悦,可对我来说,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此失去了意义。
明天,所有的头条都将被这条激荡着胜利喜悦的新闻占据。没有人会关注任何一部电影,哪怕我争取到了头条,也是无效的。
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接到“限韩令”传闻的当天,公司立即取消了一场马上要举办的发布会。韩国导演已经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我却不得不打电话让他从飞机上下去,所谓原地待命,结果却是再也不会登上这一班飞机。我原本做好了被痛骂一顿的准备,可那位导演除了“好的,理解”,什么也没说。也许就像我的第一位领导曾经对我说的那样,人生总是别无选择。
直至今日,这句话再次来临,一语成谶。合上电脑,第一次确认要离开这个行业。可是去哪儿呢?无论去哪儿,都一定还会有感到无力、无法继续付出热爱的那一天。爱一份事业,并不比爱一个人更容易。
曾孟川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准备回酒店好好睡上一觉。但他说,大家都在狂欢,你怎么能不来蹭一点别人的快乐。
我几乎是翻着白眼被他拉进了酒吧,我们离得很近,但依然需要对着对方的耳朵大喊,才能聊天。
我借着酒劲,迅速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当初你让我跟你一起离职,除了觉得我一定会答应,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第二,为什么亲了我又不肯跟我谈恋爱?第三,现在你要不要跟很丧的我谈恋爱?他定定地看着我,很久都没有说话。音乐切换的时候,现场突然安静了下来,他说,你看那边那个女孩,值不值得我过去要个电话?
我随着他的目光扭头,原本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却真看到了一个穿着吊带和超短裤,皮肤白皙五官出众的女孩,她也正在看着我们。
曾孟川跟女孩用目光交锋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说,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没听清。
我说,没什么,喝了这杯我就走了,不耽误你的正事了。
我仰头喝光了酒,那一刻,真想马上回到北京,回到我还没被击碎的人生中去。
至于曾孟川,我们就此别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