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萧红的呼兰河,到汪曾祺的大淖,乡土世界里上演的平凡故事经由作家之笔显出其怪异荒诞,鱼龙乱走,风沙四起。他们冷锐地写着生死,叩问月光为何如此冰凉,又不自已地流溢柔情与儿时的欢欣。
90 后作家郑在欢对世界的领悟同样源于他的家乡,河南驻马店。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他从自己的记忆出发,对亲人、伙伴、乡邻进行了细腻而又克制的描写。他解释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身边的人们,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自己,解释着这个时代。本期推送作者回忆中的奶奶,他以成人的目光穿过层层雾霭,回望孩提时代紧密相连之人。

疯狂原始人
郑在欢
这样的晚上,外面雾霾大得要死,刚吃完饭,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人总得遛遛食吧,既然没法走路,我就只好写作了。
今天我打算讲讲我的奶奶,刚刚不知怎么突然想起她,就越想越细,细得连她脸上的皱纹都看见了。说起来,我又有很长时间没跟她打电话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久,也许一个月,也许一个月多几天,如果我现在给她打个电话,马上就会得知确切时间。接到电话,她会先问一句吃饭没有,继而佯装责怪我:“怎么那么久不来电话,你上一次打电话还是某月某日。”
她会直接说出一个确切日子(农历),每次都是,简直比日历还准。当然她是没有日历的,即使有她也看不懂,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这恐怕是文明在她身上烙下的唯一印迹。她不听戏,不看电视,不听音乐,在她看来,电视就是一些人在上面晃来晃去,说个不停。小时候她不让我看电视,一到七点钟就轰我上床睡觉,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她管不住了,就用劝的:“有什么好看的呢,今天看是那,明天看还是那,啥时候看不都一样。”
她根本不知道有剧情这码事,看到偶像片,她就啧啧称赞,夸里面的男女长得漂亮,看到武打片,她就连连惊叫,替演员们担惊受怕,心疼他们挨打,怕他们死掉。甄子丹是她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演员之一,一看到他,她就大骂坏蛋,责怪他老打人,一打就打死一大片。我们跟她解释多少遍都没用,我们告诉她甄子丹演的是好人,打死的那些才是坏蛋。她不同意,说就算是好人,老二话不说就把人往死里打也好不到哪去了,谁的命不是命呢。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用这句话把她轰走,让她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我们看电视。她多半是在做饭的间隙或者等待收拾碗筷的时候才会靠在门边看一会儿,她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看完过一整集,所以她根本不知道电视里在演些什么。她看到死人就会惋惜,看到爱情就会高兴,从来不在乎死的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抑或那对卿卿我我的男女其实是一对奸夫淫妇。她不问前因后果,只看眼前事。
“咦!这个人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在说话?”
她总是突然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这是序幕、这是闪回、这是另一部电视剧。
“那这不是骗人吗。”
“电视当然都是假的了。”我们告诉她。
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明知道是假的还要去看,还要与里面的人物同喜同忧,既然他们怎么打都不会死,既然他们挣多少钱都拿不到,既然他们结了婚也不生孩子,那还有什么可看的,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什么可为他们担心的。这就是她的意思,虽然偶尔看到甄子丹打人还是恨得牙痒痒,但回头一想这些都是假的,她也就不那么担心了。
所以她从来不主动去看电视,也不听戏,她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生活中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我们家——她哪还有心思去关注那些虚构的热闹。

她有四个儿子,我爸是老大,我是我爸的老大。我妈生了我没几个月就死了,我爸很快又给我找了个后妈。四个儿子,五个儿媳妇,一堆孙子,究其一生,她都在和儿媳战斗,具体一点,就是我爸的两个老婆。他找的这两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厉害,虽然我妈已经去世那么多年,邻居提到她还是记忆犹新。
“她是个乐天派。”邻居跟我说,“见到人不笑绝不开口说话。”
“她很有力气,那么大一袋化肥,男人都不一定搬得动,她扛起来就走。”
“她的拳头握起来就像个小肉锤,这么个拳头砸到身上就可想而知了,幸亏你奶奶那时候年轻,经得起揍。”
他们说得很夸张,但是经我奶奶证实,那个小肉锤只砸过她一次,大多数时候,她更喜欢砸的是东西。
“还不如打我呢。”奶奶总这样说,“她砸的都是钱啊。锅碗瓢盆就不说了,她最喜欢的就是揭我的房瓦,竖个梯子爬到房子上去,把瓦片全都扔到地上摔碎。一边摔还一边喊,让我这个老壳子没地方住。亏你姥爷还是个念书人,竟然教出一个这么野蛮的闺女。”
虽然抱怨,但她并不觉得我妈是个坏女人,她说她只是脾气暴,只是不懂得控制。
“她讲理。”奶奶说,“等脾气发完知道错了,她就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她,如果我不松口,她就跪着不起来。哪像那个女人(指我继母),完全不讲道理,想什么时候闹就什么时候闹。”
虽然讲道理,她还是没少跟我奶奶生气,她死了,我奶奶还很怀念,每年都去给她烧纸,春节还接她的灵魂回家过年,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儿媳妇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对她可以说没有任何感情,我根本不认识她,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曾经一度还怪她为什么不早死几个月,那样我也就不用出生了。别人在我面前说起她,就像说起一个古人那样遥远而陌生。

和所有老年人一样,我奶奶也很迷信,得了病她第一时间不是去找老刘(街上的医生),而是到庙里包点香灰回家兑水喝,这么做第一是为了省钱,第二确实是出于对神的信任。有一次不知道哪尊神给她治好了什么病,她还买了一面锦旗送了过去。
既然信神,信鬼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妈死后,一直是她带着我。她总跟我说,我妈的“魂”很强,比她遇见的所有“魂”都厉害,每一天,她都能感到她在我们身边。
“给你冲奶粉的时候,碗就开始乱转,里面的水打着漩涡,跟个无底洞一样。她可能是想把你带走,她放心不下你。”
这些话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小时候我都不敢走夜路,老觉得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妈一得势就得把我拐走。
“我就大声骂她,日恁娘,死了就死了,到你该待着的地方去,来这里折腾活人干什么,再不服气你也活不过来了。”
“一骂,她就听话地走了,她就是这么讲理。”

奶奶一直有骂死人的传统,她老觉得死人不甘心死去,在跟活人捣乱。如果我们说腿疼,她就骂我的祖奶奶,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摔断了腿,觉得生活不便就上吊自杀了;如果有人说头疼,她就骂我爷爷,他是脑溢血死掉的;即使有人哪里都不疼,只是过分兴奋,闹腾,她也会骂,因为我祖爷爷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最常用的词是“摸索”,意思和鬼上身差不多,只是没那么严重。形容鬼这种行为用的是我们那里的方言“勺道”(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本意指多嘴多舌的,延伸出来就是多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正在安心看书,你打了我一下,我多半会嘟囔一句:“勺道!”
我奶奶驱鬼多半用得是这一招。
“勺道货!”她骂道,声厉惧色,“又回来干什么,我们都过得好好的,别摸索孩子了,要摸索就来找我。”
她这么骂一通,然后问我们还疼不疼,也许她的咒语真有效,也许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大多数时候都药到病除。小时候看到她这么一本正经地骂,我还有点害怕,后来长大一些,反倒觉得有趣。有时候实在无聊,我会装疼让她骂,有一次我说脖子疼,她想了一大圈不知道该骂谁,后来她突然灵光乍现(那感觉就跟写小说的人突然得到灵感能把烂尾的故事继续下去一样)。
“一定是你老太(祖奶奶)。”她说,“这个死鬼是上吊死的,就是了,上吊肯定勒得脖子疼……”
看她说得那么可怕,还没等她骂我就说不疼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脖子疼,即使有一次马蜂蜇了我的脖子,肿起一个油亮的大包,我也没有喊疼。那一次,她慌慌张张放下正在擀的面条,去邻家的产妇那里接来一小碗奶水,给我抹在受伤的脖子上。那不是她第一次替我央求奶水,却是最后一次,等我终于长大,她像完成了一个浩大工程一样满心欢喜,功成身退。

还是得说到我妈刚去世那会儿,那时候我才七个月,正是奶水的消费大户,可是我没有妈了。所有没妈的孩子都一个命运,就是吃奶粉,更惨一点的,买不起奶粉就只能吃羊奶牛奶或者随便什么奶,反正是赶上什么吃什么。比如隔壁村的一对双胞胎,母亲生他们时难产而死,因为他们个头太大了,那时候穷,连三鹿都没有,幸亏他们家有一头壮年母羊刚刚下崽,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家饿死了羊羔养活了两兄弟。二人长得非常壮实,只是因为吃羊奶长大的,人们总是开玩笑说他们身上有一股羊膻味。这成了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印迹,虽然他们身上的味道和所有庄稼汉一样,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冠名为大老骚虎和小老骚虎。(注:老骚虎,方言,指公羊。)
我出生在 1990 年,那时候正是三鹿大行其道的时候。奶奶养蘑菇卖了钱,然后给我买奶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死活就是不吃,灌都灌不进去,也许是我对三聚氰胺过敏,也许我喜欢的只是真实乳头的触感,反正是让我奶奶伤尽了脑筋。没奶吃的日子,我就没完没了地大哭,幸亏我们一墙之隔的邻居也是个产妇,并且是个好心的产妇,她女儿只比我小两个月,夜里听到我哭,她就让奶奶把我抱过去,一咬到乳头,我连屁也不会放一个,只顾着埋头大吃。仅凭她一个人的乳汁当然养不活两个孩子,况且她也麻烦事一大堆,她为丈夫生了三个女孩,和我年纪相仿的这个是老三,叫婷婷。丈夫在她怀孕的时候和一个女人去了外地,再也没有回来。生完婷婷,她很伤心,一等孩子断奶她就走了,几年之后她改嫁到别的村庄,又生了一个儿子,再也没管过这边的三个女儿。奶奶一提起她,就又是称赞又是叹气,“她是个好心的女人,她是个苦命的女人。”
虽然吃她的奶最多,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因为奶源珍贵,奶奶只让我在夜里吃她的奶,白天就带着我四处蹭奶吃,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是和我同吮一颗乳头的好兄弟,搞得我无论到谁家玩,热情的妈妈们总是对我说,“欢欢啊,你小时候可没少吃我的咪咪。”
作为一个懵懂的少年,她们的话总是让我感到羞涩,但在内心里,我是感激她们的,那时候我还想,以后挣了钱给她们每人买两箱奶粉以示回报,现在想来幸亏没有挣到钱,那样做的话简直就是对她们的侮辱,无论放到哪一天,乳汁都是无价的,我能做的,只能是怀着感恩的心,把她们当做我的半个妈妈。

就是这样,乞丐们吃的是百家饭,我吃的是百家奶。不光在同一个村子里,有时候遇到过路的产妇,我奶奶跟人陈述详情,她们多半也会慷慨解怀,让我饱餐一顿。
“这是个没娘的孩子。”奶奶多半会来这么一句。仅此一句,就会引得妈妈们的同情心汹涌而来。有一次她带我到街上去买衣服,为了便宜两块钱,她又一次使出杀手锏。
“我们是没娘的孩子。”她说,“再便宜点吧。”

卖衣服的是个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也许是因为还没当妈的缘故,她无动于衷,再也不肯让步。倒是我,听到这话立刻走开了,那一刻我简直恨死她了,为什么到处让人可怜我,可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看不起,意味着别人比我要高上一等。少年时的自尊心太强了,况且又是在一个女孩面前,我打心眼里看不起她这一点,都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两块钱就可以出卖尊严。即便不要尊严,女人起码的虚荣心总该有吧,可是她没有,她总是把自己当做最卑微的存在,不与人攀比,也不四处炫耀。不过话说回来,她也没什么可炫耀的,除了那位天下无双的暴力儿媳。
试问谁有她挨儿媳的打骂多?没有。

我妈刚去世那会儿,奶奶很是愁苦,觉得我爹年纪轻轻就成了鳏夫,还带着一个孩子,下半生没有女人可怎么过啊。她一直是这种想法,包括我长大点挨了继母的揍,怪我爹找了个这么狠毒的女人当初还不如不找,尽管对继母恨之入骨,她还是不同意我的假设,“没有女人怎么行呢。”她老是这么说,搞得我总以为女人是一种生命能源,离了她们就不能活,可我又看到不少光棍照样活得好好的,没有女人和他们吵架,日子别提有多自在了。所以她的话让我非常困惑,当然现在长大了,我已经完全能理解她的担忧,并且也不那么恨我老爹了,虽然我苦了一点,他也不怎么好过,我奶奶就更惨,但相比那个女人给他带来的快乐,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直呼其名,叫她花。
奶奶的担忧没持续多久,我爹就找到了花,紧接着生了个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奶奶那个高兴啊——同样没持续多久,我爹在广州因为贩卖黄书被捕入狱,花一个人在家照顾襁褓中的孩子,她把生活的诸多不便全算在奶奶身上,动不动就打她一顿,骂人更是家常便饭。因为没有钱花,她在奶奶家四处搜刮,我爷爷那时候还在世,实在受不了就骂了她,结果她立刻使出杀手锏——离家出走,扔下哺乳期的弟弟给奶奶照顾。她在外面浪荡了一年,奶奶托人去找,一直没有找到,后来我爹出狱,她自个儿又主动回来。
因为没有看牢让她跑了,奶奶引咎自责,惶恐不安,日日念叨留下两个没娘的孩子该如何是好。花把这个当做她的软肋,有什么不能满足或者受到顶撞,她拔腿就跑,奶奶自然在后面紧紧相追,小时候她老跟我说这个,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那个女人动不动就跑了,我把她的腿都抱细了。你爸坐牢,她天天跑出去胡混,你爷爷说说她就往外跑,我在河岸上抱住她的腿,死活不松手,那个女人多有劲儿啊,她用脚踹我,抓着我的头往石子路上撞,我就是不松手,最后她见实在没办法,就拖着我往前走,我的膝盖都磨出血了,但我就是不松手。”
每次听到这我就替她着急,“你还不如让她跑了呢。”
“她跑了怎么办,你爸还那么年轻。”她说,“没有女人怎么行呢。”
这就是她固守一生的观念,她认为有女人有孩子一个家才算完整(这两年她同样闲着,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而维持一个家的完整就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不管受再多的苦与累,只要孩子们都“熬成一家人”(奶奶语),她也就死而瞑目了。
后来我三个叔叔陆陆续续结了婚,她们矛盾更突出了,花总是说奶奶偏心,打骂变得更为频繁。奶奶一直默默承受,甘做出气筒。这样的生活起码过了二十年,直到我们长大,花也慢慢变老,奶奶的日子才好过一点。当然我们这口气松得有点早,一个斗士老去了,新一代的斗士又来了,那就是我的四婶子。
我四叔只比我大十岁,就跟我的哥们差不多,而我这位四婶就更小了,只比我大五六岁。她进门的时候,正是我叔最穷的时候,所以她打奶奶多半是因为没钱。这也都是奶奶跟我说的,每次都把我听得义愤填膺,奶奶又不让我告诉叔叔,她跟我说,大概也只是为了说出来好过一点。她总是重复说同一件事,好像完全忘记自己曾经说过,抑或是心中积压的事情太多,不知道哪些说过哪些没有。
“她直接打我耳光,那个妮子,她真是野蛮。”奶奶说,“俗话说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花那么厉害也没有打过我的脸。她年轻力壮,手劲那么大,一巴掌就能把我的脸打肿,手上还有戒指,把我的脸都能划出血。”
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媳妇,她挺了过来,但生活的难关对她来说远远不止这些。是的,除了媳妇,还有我们这些孙子。

她一共有过十一个孙子孙女,其中有两个已经夭折——这在我们家属于禁忌话题,还是不谈为好。十多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她经手带大的,我是她第一个孙子,也是最让她操心的一个,直到十四五岁,我还和她同睡一张床,小时候我有脚凉的毛病(现在也是),她总是把我的脚放在身上,慢慢捂热。

十来个孩子,一个长大,一个又出生,总是有五六个孩子在她身边萦绕,每天叽叽喳喳,不是磕了就是碰了,抑或是打起来了(我和弟弟最为频繁)。小的需要紧紧看护,大的同样不让人省心。她每天活在孩子们的聒噪中,又累又烦,常常气得无声啜泣。不过每当一个孩子出生,她又总是比谁都要高兴。前年,我的弟弟生了个儿子,我说恭喜你啊,这么年轻就荣升为祖奶奶了。她马上说,我最想当你孩子的祖奶奶,吓得我赶紧转移话题,我知道没法跟她解释我根本不想要孩子这回事,那非把她气死不可,她肯定会说,不要孩子你还活个什么劲儿?
虽然,她最羡慕的是一个住在茅草屋里的孤寡老人,“每天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用说话,每天只刷一个人的碗,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做饭,不饿就不做,那样多好,等你们都长大了,就给我盖一间那样的小屋,谁也别来烦我。”
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最小的一个都六岁了,她还是没办法完成那样的梦想,因为她的重孙子又出生了,照这么看,估计那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她这个家长做得太尽职了,所以她的子孙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继续着出生的喜悦,也继续着生活的磨难,这些都不算什么,对她来说,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受再多的苦也值得。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应该就此打住了,大家会觉得我奶奶是个为家庭无私奉献、对孩子充满爱心的好人,虽然确实是这样,但我不得不说,她也有极度冷酷残忍的一面,那就是面对动物的时候。
刚刚过上吃饱饭的日子,乡下是很穷的,农村孩子根本没有像样的玩具,只能就地取材,有什么玩什么。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但是玩泥巴总有厌烦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玩具,永远是可爱的动物,毕竟,它们会动,会和你互动。即使不会动的,比如说猪的胆囊,吹大了也可以当做气球玩。不过这个太稀有了,一头猪只有一个胆囊,一群孩子只有一个人能得到,相比之下,小鸟似乎就比较容易得到了,特别是麻雀,乡间到处都是,而且又是害虫,除四害的时候没有搞彻底,广大人民的热情已经消减,但对它们的偏见依然存在,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抓来给小孩玩又何乐而不为呢。
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座空房子,常年没有人去住,只是用来堆柴禾,那里很自然的成了麻雀们的大本营。房门上全都是鸟屎,已经看不见木头。一打开门,里面群鸟乱飞。小伙伴们知道那里有鸟,已经培养出一种默契,“走啊,找欢欢逮鸟去。”然后我就去找奶奶要钥匙,带着大伙去掏鸟窝,她刚开始还由着我,后来就不让了,说那些鸟是留着给我玩的,都让别人掏走了还玩什么。也是,每次去背柴她都顺道给我带只幼鸟回来(有时候则是几只鸟蛋),让我随便玩,想怎么玩怎么玩。其实鸟能有什么好玩的呢,刚开始大家只能想到喂鸟,让它长大,听自己的话。可是喂鸟的过程太漫长了,谁也没有成功养活过一只鸟,既然它们早晚都得死,那还不如死在我手里比较好,于是喂养很快转化成虐待,看谁让手里的鸟死得更有创意,死得更惨,或者死得更彻底,反正是围绕着死进行一系列活动。我们试过活埋、焚烧、注射药品、剖腹、水淹、钝器击打,还有一次,我们把一只鸟的羽毛拔光,然后放回大自然(说到这里我们的罪孽似乎太深重了,我会好好忏悔的)。
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杰作拿给奶奶看,她不置可否地笑笑,然后骂我一声淘气,第二天又会给我带回一只全新的小鸟。
在她看来,既然我爱玩,那就玩好了,反正又不用花钱。
这些都是我对小鸟干的,她充其量只能算个帮凶,但是后来,她亲自干了一件我从来没干过的事情。
那时候我又长大了些,应该有十二三岁,兴趣早已经从小鸟身上转移到别处去了。有一天,我们听到屋顶的树上传来八哥的叫声,这种鸟还是很少见的,况且它又有能说话的本事,这严重吸引了我们。我和弟弟爬上房顶,用竹竿把鸟窝捅了下来,幼鸟已经很大了,差不多快会飞了。我们本来想养着教它们学说话,但是经过邻家老头鉴定,这些八哥是哑巴,学不会说话。我们白忙活一场,就把鸟丢给堂弟堂妹们玩了,他们都还很小,从三岁到八岁不等,正是对小鸟感兴趣的时候,一个个高高兴兴抱在怀里。
“等等!”奶奶突然大喊,不让他们拿那些八哥,她嫌八哥的嘴太尖太长,怕啄到孩子的眼睛。她从窗台上拿起剪刀,很利索地剪掉了所有八哥的嘴巴。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残忍,她倒是驾轻就熟,干完了像没事人一样回去做饭,丝毫不顾及八哥的感受。也许是因为伤口,也许是因为受到的凌辱,那些八哥在一顿饭的工夫全都气死了。越高贵的鸟气性越大,它们的尊严丝毫不容践踏,如果不能再翱翔蓝天,它们宁愿一死了之。在这一点它们跟我奶奶的处世哲学真是截然相反,鸟儿的生命在于翱翔,我奶奶则在于熬。
我突然明白我爸弟兄四个的名字中为什么都带着一个“敖”字,原来我的祖辈崇拜的不是鳌拜,只是一个熬字。
生活就是熬日子,看谁能熬到最后,像那只兔子,它熬过了全家死去的浩劫,熬过了我奶奶的灭门钉耙,终究还是没有熬过她的夺命铁锹。

那时候我七八岁,奶奶在田里刨红薯,一钉耙下去,击中了一个兔子窝,一柄钉耙三根齿,就像串羊肉串一样,中间最长的那根穿着两只小兔子,边上那根穿着一只老的,只有一根齿上面没有血迹,也只有一只小兔子活了下来。那天我们家吃了一顿索然无味的野味(全拜我奶奶的厨艺所赐),我得到了一只瑟瑟发抖的小野兔。
它是灰的,还不怎么会跑,奶奶本来准备连它一起炖了,看到我充满期待的眼神,就把它赏给我玩了。那是我第一次全心全意养的一只宠物,我真的很喜欢它,还给它起了个很没有想象力的名字,叫小灰。为此我们的邻居光辉老跟我捣蛋,他父母也是这么叫他,每天我们两家隔着院子小灰来小辉去,他觉得是侮辱他,非要让我改个别的名字。我当然不答应,和他据理力争,
“它叫小灰怎么了,凭什么只能你一个人叫。”
“我先叫的,你学我。”
“谁学你了,它是灰的所以叫小灰,你是灰的吗。”
“我是光辉的辉。”
“那不就得了,我是小灰的灰。”
“可这个灰和那个辉都是一样的灰啊。”
“……”
我们就这样把架吵成了绕口令,虽然小辉对我的小灰恨得牙痒痒,但还是会忍不住来看看它,有时候还带点萝卜缨子什么的喂它。在我的悉心照料下小灰慢慢长大,直到突然学会了跑步,并且一跑就奔着逃跑去了。有一天它从我用来给它作窝的破筐里爬出来,径直朝下水口跑去,眼看着就要跑出门去,我赶紧去追,这时候奶奶刚好拿着铁锹在铲鸡屎,看到我追兔子也帮着去栏,一追追到门外,眼看着小灰就要跑进树林的草丛里去了,她一铁锹拍死了它。
“为什么要打死它。”我当场就不干了,“你赔我小灰。”
“不然它就跑了。”她显得很有理,“兔子跑得草堆里就再也找不到了。”
“跑了也比死了强,”我哭起来,“你把它打死了。”
“不打它就会跑……”她的回答真是苍白,好像只有这么一个解释。看见我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仅仅是因为一只兔子,它活着,跟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它死了,同样关系不大,她只是关心我才这样做,当初没有炖掉那只兔子是为了给我玩,现在打死它是为了帮我拦住它。她根本不关心它叫小灰还是小白,在她眼里,那仅仅是一只兔子。就像一只鸡或一只羊,养着它们就是为了吃的,为了给人吃。
我不知道动物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以及各种大自然的崇拜者看到这里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我奶奶是个冷血的动物杀手,会不会觉得她不够仁慈,我只知道,她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就在刚刚,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七十多岁了,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常常拿起这个就忘记那个,但她清楚地记得我上一次打电话的日子,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
“欢子吗,怎么那么久才打电话,上次还是九月十七打的。你吃饭没有?”
“吃过了,你呢。”
“我还没做。”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于是我只得循例向她打听各个家人的情况。
“俺二叔哩。”
“他在山西。”
“他给你打电话没。”
“打了,九月二十八打的。”
“俺三叔哩。”
“他和你四叔去俄罗斯了。”
“去干什么?”
“干建筑。”
“啥时候去的。”
“十月初六。”
为了考考她,我又问了其他几个堂弟堂妹,不管是他们离家的日期还是打电话的日期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包括他们的生日,就像印在她脑子里一样张口就来。九个孙子加上四个儿子的生日,她全都记得分毫不差,可是当我问起四月二十七日是什么日子的时候,她想了好久都没有回答,最后连这个问题一起忘记了。我告诉她,你记住了所有人的生日,却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身份证上都是瞎写的。
挂掉电话,我对着远处的雾霾说,祝你生日快乐,没有生日的人。
▍文章由出版社授权发布,插图来自阮义忠摄影集《失落的优雅》、《人与土地》。


作者: 郑在欢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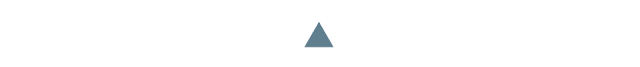
编辑 | 嫌仔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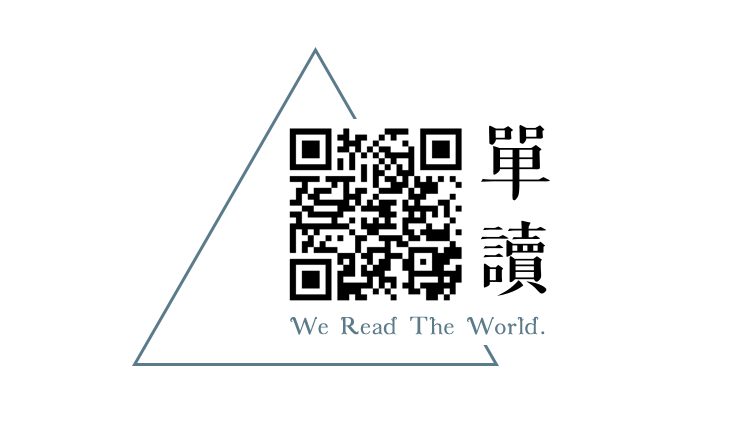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郑在欢新作《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