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每日精选一篇书摘的小栏目
从译文社的书中,摘一些有趣或无趣的内容 今天是第五十七篇 也欢迎看到您发来的个人建议 告诉我想读哪位作家的作品 |
- 57 -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噎在他的喉头,他刚才还感到这个世界像水晶一样明亮,发出悠扬的声响,为柔情蜜意和缠绵爱情所笼罩,沉浸在一种善意和信赖的旋律之中,可是蓦然间,这大批群众钢铁般的进军步伐,把一切都踩得粉碎。系着武装带,千万人千百种姿态,却汇成一种呼喊,凝聚成一道目光,里面是仇恨,仇恨,仇恨。
文|茨威格
“疯狂!他们想干什么?再打一次,再打一次仗?”
文|斯特凡·茨威格 译|关惠文 等
摘自|《昨日之旅》第三章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咱们走吗?”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走,咱们走,”夫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无助地站着,一动不动,仿佛他们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粉碎。然后,他们才犹疑不决地,迷惘慌乱地向出口处走去(他忘了挽起夫人的胳膊)。
他们走出火车站。可是刚到车站门口,一阵喧嚣便像风暴似的向他们袭来,鼓声隆隆,哨音尖利。喧嚣震耳欲聋——各种老兵协会和大学生们在举行爱国游行,他们犹如活动的城墙,四人一排,一排又一排,旌旗招展。一群穿着军人制服的男人,踏着铿锵有声的行军步伐,按照同一个节拍大步前进,整齐得就像一个人。他们脖子僵硬地向后挺起,一副竭力下定决心的样子,嘴巴大张,高声歌唱,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步伐,同一个节拍。第一排走着几位将军,白发苍苍的显要人物,身上挂满了勋章奖章,旁边是年轻人的队伍,他们以运动员的顽强劲头,笔直地高举大幅的旗帜,上面印着骷髅、带钩的十字指纳粹标志。各式各样古老的帝国旌旗迎风招展,他们胸膛绷紧,额头向前直挺,仿佛冲着敌人的队伍向前挺进,群众仿佛被巧妙的指挥的拳头驱使,像几何图形一样精准地、整齐地迈步向前,像用圆规划定,精确地保持距离,和着脚步,每一根神经都严肃地绷紧,目光咄咄逼人。每当新的一队——老战士、少年团、大学生——从高高垒起的检阅台走过,打击乐在那里有节奏的顽固地把视而不见的铁砧上的钢铁砸得粉碎,这一大堆脑袋突然一震,摆出威风凛凛的神气:他们似乎服从于一个意志,所有的人脖子都往左边一甩,所有的旗帜都像被绳子一拽,在大队伍的首领面前一亮。首领把脸绷得像块石头,神情坚毅果决,检阅这些平民:没有胡须的、刚长绒毛的,或者皱纹满面的工人、大学生、士兵或者男孩,所有的人在这一时刻都有着同一张脸,顽强坚定,下定决心,怒气冲冲的目光,桀骜不驯地昂起的下巴,握住看不见的剑把的手势。一排一排的队伍像阵雨落下似的敲着鼓点,因为单调,愈发使人感到内心狂躁,愈发使人脊背挺直,目光坚定——战争和复仇的制造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和平的广场上站好队伍,正凝视着天空。天上温柔地布满了淡淡的白云。
“疯狂。”他深感意外地嗫嚅着,“疯狂!他们想干什么?再打一次,再打一次仗?”
战争把他整个人生击成齑粉,再进行一场这样的战争?他怀着一种陌生的颤栗仔细看着这些年轻的脸,眺望着这黑压压的前进着的人群。四人一排的队伍,从狭窄的小巷中不断涌出,就像方形的电影胶卷一段段地从黑匣子里抽出。他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是同样坚定不移,怒气冲冲,形成一种威胁,一种武器。为什么这股威胁要剑戟铿锵地直伸进这温和宜人的夜晚,为什么要一直砸进这座在和平山地里做着好梦的城市。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噎在他的喉头,他刚才还感到这个世界像水晶一样明亮,发出悠扬的声响,为柔情蜜意和缠绵爱情所笼罩,沉浸在一种善意和信赖的旋律之中,可是蓦然间,这大批群众钢铁般的进军步伐,把一切都踩得粉碎。系着武装带,千万人千百种姿态,却汇成一种呼喊,凝聚成一道目光,里面是仇恨,仇恨,仇恨。
他不由自主地挽住夫人的胳膊,为了感觉到一点温暖,感觉到爱情,激情,善意,同情,一种柔和的使人宁静的感觉。可是,那暴雨般敲击不停的鼓点,把他内心的平静全都破坏。此刻,成千上万个嗓音轰响起来,汇成一首难以理解的战歌,大地随着节奏鲜明的脚步声震颤,空气由于这庞大的群体突发的乌拉声而爆炸。这时他感到,就仿佛他内心深处那些娇嫩脆弱、音韵铿锵的东西,碰到这现实生活中的暴戾粗野、尖利刺耳的轰鸣而突然碎裂。
他身边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他一下,让他惊醒:夫人戴着手套的手轻柔地提醒他,不要这样使劲地把手握成拳头。他把紧盯着游行队伍的目光移开——夫人默不作声,祈求似的凝视着他,他只有在胳膊上感到,她的手在轻轻的催促他。
“好,咱们走吧,”他振作起来,喃喃地说道。他耸起肩膀,像是在抵御什么看不见的威胁,拼命挣脱那挤成一堆的人肉之墙。这些人和他自己一样正默默无言的、专心致志地凝视这些武装军团不停地大步前进。他不知道想挤到哪儿去,只想离开这阵喧嚷、鼓噪的混乱局面,离开这座广场,这里有一只咚咚作响的研钵,以无情的节拍把他心里一切轻柔的、梦幻般的东西研得粉碎。他只想离开这里,单独和她在一起,就和她一个人待着,被黑暗这个拱顶包围着,为一层屋顶遮盖着,感觉她的呼吸。十年来,第一次不受别人监视,不被别人打搅,望着她的眼睛,充分享受和她单独相处的时光,这可是他在无数的幽梦中唤起的情景,如今几乎被这猛击战鼓、喊声震天、齐步前进的汹涌奔流的人潮冲刷得荡然无存。他的目光急躁地掠过前面的房屋,它们几乎为各色旗帜遮挡,当中只有几间上面有金色的字,写着公司的名字,有些字是一家旅馆的招牌。他蓦然间感到手里拎着的小皮箱轻轻往下一坠,提醒他:该到哪儿去休息一下,回到屋里,单独待在一起!买一点点宁静,买几平方米安静的空间!突然间,他发现在一个高高的石头门面上突显出一家饭店金光闪闪的名字,竟仿佛给了他一个回答。旅馆的玻璃大门向他们迎面打开。他的脚步变慢,呼吸急促。他几乎神色慌张的站住脚步,他的手臂情不自禁地和夫人的手臂松开。“据说这是家不错的饭店,人家向我推荐过,”他结结巴巴地撒着谎,企图掩饰急促不安的窘迫。
夫人吃惊地倒退一步,苍白的脸涨得通红。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要说点什么——也许是和十年前同样的话,惊慌失措的一句:“别在现在!别在这里!”
然而此时,夫人看见了他凝视她的目光,胆战心惊的、六神无主的、惊慌失措的目光。于是她低下头,默默无言的表示同意,跟着他迈着迟疑不决、心虚胆怯的步伐,跨进饭店的大门。
……
他们走进房间。在这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空气混浊甜腻,发出橄榄油肥皂和冷凝的香烟味道,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残留着陌生男女无形的痕迹。
房间当中放着一张双人床,被子凌乱,肆无忌惮,也许还有人的体温,这房间的意义和用途显而易见,这样露骨,他感到恶心:他情不自禁地快步走到窗前,把窗推开,潮湿的软绵绵的空气夹杂着街上蒸发出来的喧闹,从往后倒退的摇摆不定的窗帘旁边慢慢地涌入。他伫立在敞开的窗前,使劲地望着窗外已经渐渐变黑的鳞次栉比的屋顶: 这间房间是多么丑恶,待在这里是多么令人羞惭,多年来他梦寐以求和她双双相聚,是多么令人失望,这样的聚会既不是他,也不是夫人的愿望,这样突然,这样毫无羞耻的赤裸裸的单独相处!他眼望窗外的时间,达连吸三五口气之久,他数着呼吸的次数,没有胆子说出第一句话。不行,这样不行,然后,他迫使自己转过身来。完全像他所预感的那样,像他自己所担心的那样,夫人像尊石雕僵硬地站着,一动不动,穿着她那灰色的风雨衣,两臂下垂,就像折断了似的。她站在房间当中,就像一样不属于这房间的东西,而只是由于突发的偶然事件,由于一时失误才被放到这间令人反感的屋里来了。她脱下手套,显然想把它放在哪里,可是想必放在屋里任何地方,她都感到恶心。于是,手套便像空壳似的在她手里晃动。她的眼睛发直,就像蒙在一层惊恐的面纱后面。现在,既然他转过身来,夫人的眼光便央求似的向他射来,他明白了。“咱们是不是,”——呼吸不畅,他的嗓子也说不下去——“咱们是不是再出去走走?……这里闷得要命。”
“行……行……”这个字像获得赦免似的从她嘴里迸出——恐惧的锁链终得解开。说着,她已握住房门的把手。他稍稍慢一步,跟在她的身后,看见她的肩膀正拼命颤抖,就像一个动物脱离了死亡的铁爪。
街上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节日游行队伍的尾部依然把街上正常的行人往来弄得躁动不宁。于是,他们拐进旁边比较安静的小巷,走进通向树林的道路。十年前那次星期天的郊游就是这同一条路把他们带到山上的宫殿。“你还记得吗?那是个星期天,”他情不自禁的大声说道,夫人心里显然也在想着这同一段回忆,她轻声答道:“我跟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没有忘记。奥托和他那个同学快步冲到前面,我们几乎要把他们丢失在林中。我叫他的名字,叫他赶快回来。我这样叫其实是违心的,因为我迫切想要和你单独待在一起。可是当时我们彼此之间还很陌生。”
“今天也是这样,”他想开个玩笑,可是她不吭声。我其实不该说这句话,他心里朦胧地感到:什么东西逼迫我老是进行比较,今天如何,当年如何。可是为什么我今天跟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灵:“从前”那过去的岁月总是夹在我们当中。
他们默默无言地向上攀登,他们下面的房屋在微光中已经缩成一团,从氤氲迷蒙的山谷里已经越来越明亮地拱起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河,树木沙沙作响,夜幕低垂,笼罩在他们身上。没有人向他们迎面走来,只有他们的影子默默地在他们前面移动。每当一盏街灯从斜里照亮他们的身影,影子便在他们面前融成一片,拉得很长,就仿佛他们在互相拥抱,互相渴求,身子依偎着身子,化为一体。等他们自己疲惫地慢慢地向前迈步,他们的影子又重新分开,然后再重新拥抱。他像着了迷似的望着这奇特的游戏,这两个没有灵魂的身影彼此逃离又复捉住,然后互相拥抱,这两个影子组成的身体只是他们自己身体的返照。他怀着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看着这两个没有实质的形体彼此逃离而后又纠缠在一起,只顾观看这黑色的流动逃窜的图像,简直忘记了他身边的这个活生生的人。他并没有清楚地想到什么东西,可是朦朦胧胧地感到这怯生生的影子游戏提醒他什么事情,提醒他深埋心底的什么东西,如今这东西骚动不宁地翻动起来,就好像回忆的水桶急促不安、咄咄逼人地摸索着靠近。它到底是什么呢?——他凝聚心神,想弄明白在这沉睡的树林中,影子伴随着前行,到底提醒他什么:想必是一些话,一个情景,一番经历,听到的什么,感到的什么,包含在一段旋律中的什么东西,深埋在心底的什么东西,尽管岁月一年年过去,他从来没有触及过这个东西。
突然间,豁然开朗,在遗忘的黑暗中出现一道闪电般的缝隙:是一些话,是夫人有一次在客厅里向他朗诵的一首诗。一首诗,不错,是首法文诗,他记得这些字句,它们像突然被一阵热风卷起,一直吹到他的唇边。十几年过去了,他又听见夫人的声音,在朗诵一首外文诗里的被遗忘的诗句。
Dans le vieux parc solitaire et glacé
Deux spectres cherchent le passé.
这两行诗刚在记忆中涌现,一整幅图画简直像幻影似的迅速附在诗上:在昏暗的客厅里,夫人有一天晚上向他朗诵魏尔伦的这首诗,一盏灯放射出金色的光芒。他看见夫人进入灯影中,像披上深色的衣衫,她当年就那样坐着,既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为他所爱,却不可企及,他一下子感到,他自己的心又和当年一样激动地怦怦直跳,听见她的嗓音在诗歌的音韵铿锵的波涛里震颤,听她在诗歌里,虽然只是在诗歌里,说出“相思”和“爱”这样的词,虽说是用外文,指的也是外国人,但是听这样的嗓音乐——她的嗓音——说这样的话,依然令人陶醉。这些年他怎么能够忘记这首诗,那个晚上,他们单独留在宅子里,没有旁人,于是心慌意乱。为了避免危机四伏的谈话而逃到书籍这一更为随和、更无风险的天地,在那里,含有情感和深意的自白,有时候躲在词句和旋律后面,会突然闪亮,犹如灌木丛中的磷火一闪而过,无法捕捉,虽无踪影却使人欣喜。隔了那么多年,他怎么可能忘记这事?可是这首遗忘的诗歌怎么突然间又不招而至?他不由自主地朗诵起这首诗,翻译了这些诗句:
古旧的园子,冰冷,孤寂
两个幽灵追忆着往昔。
他刚念出这两句,立刻就明白了含义,钥匙就沉甸甸、亮闪闪地握在他的手里,联想把这段回忆形象鲜明地、轮廓清晰地从沉睡的坑道里,一下子猛提出来:刚才路上投下的影子,它们触及并且唤醒了她自己的话,是的,可是还不仅于此。突然间他浑身颤栗,感到这令人吃惊的认识的意义,词句具有寓言的意义:难道不就是这些影子自己在寻找他们的往事,向一个不复真实的往日提出阴郁的问题,影子,影子想要复活,但又不可能再复活,无论是她还是他,都已不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还在徒劳地寻找着自己,彼此逃避,彼此拥抱,在这没有实质、没有力气的努力之中,他们不正像他们脚前的这些黝黑的妖魔?
他想必是无意识地大声呻吟起来,因为夫人转过身来:“你怎么了?路德维希,你在想什么?”
可是,他摆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他只是更深地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往日,看这种声音,这种回忆的预示未来的声音,是否会又一次想跟他说话,想用过去来向他揭示现在。
(完)
本文选自

《昨日之旅》
[奥] 斯特凡·茨威格|著
关惠文 等|译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收文8篇,其中包括《旧书商门德尔》《情感的迷惘》《昨日之旅》等名篇。《昨日之旅》是茨威格的遗作,在伦敦一家出版社的档案库里尘封数十年后,终见天日。小说讲述了出身清贫、才气过人的化学博士路德维希与他的老板、枢密顾问G的夫人之间,苦苦相恋却难以如愿的爱情故事。
戳以下标题可跳转至近五期每日读
完整每日读目录请戳文末阅读原文
每日读第52期
《教室里的群体意识》
作者:朱迪斯·哈里斯
每日读第53期
《作恶多端的时代》
作者:伍迪·艾伦
每日读第54期
《罪与罚》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每日读第55期
《试刊号》
作者:翁贝托·埃科
每日读第56期
《驱魔人》
作者:威廉·布拉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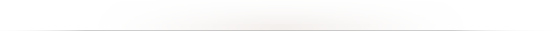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