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月工资才五百块?!”
何佳滢的妈妈猛地提高音量,惹得周围所有路人都好奇地看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戴着眼镜,穿着长裙,看起来是个斯文的读书人,怎么会月薪只有五百呢?何佳滢感到一阵尴尬,拉着妈妈一边快步走远一边补充说:“那不是工资,只是交通补助。”那也不是工作,而是毕业前必须要做的一份法院实习。
这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何佳滢一路手脚并用地解释她的法学专硕需要什么样的毕业条件。只有中专学历的妈妈努力地消化着“盲审”、“查重”、“答辩”,以及最后一句,“妈,我可能毕不了业。”
最近一年,我们几乎是不厌其烦地细数整个教育体系的幼儿园内卷、少年抑郁、高考大战、大学生贬值、考研通胀,却鲜少把目光聚焦在300万正在读研的硕士生身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挤过独木桥,理应是很多人眼中值得羡慕的高端人才。而实际上,把人生押注在一纸文凭上并不等于胜券在握,他们反而加倍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在国内读研很水。”这几乎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
然而奇怪的是,研究生们既承受着吃力不讨好的焦虑和痛苦,又常常面对被各种拒绝和否定
的处境,总之与其高学历的身份极为不相称,可以说是最尴尬的群体之一。
何佳滢苦笑着说:
“读研是渡劫,读博是赌博。”
后悔也没有用,你已经在悬崖上了,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

被嫌弃的硕士生
何佳滢的同学实习很轻松,几乎什么都不用做。但她的运气算是“不太好”,带她实习的法官愿意对一个学生毫无保留,让她去处理疫情堆积如山的案件。虽然只是写判决文书,但是被大量资料淹没的感觉十分窒息,有时单是一个案件就要翻阅满到溢出小推车的文书,包括证据比对、双方陈词、数据报告等等。她有一次甚至要去研究某个知识产权案里打火机的按钮设计。
然后是近乎神经质地反复斟酌措辞,不能有任何带主观色彩的修辞性或评论性词句。这样写出来的判决文书少则两三页,多则二三十页。何佳滢每天下班都感觉自己的大脑被抽空,经常一到家倒头就睡,根本没有精力处理其他任何事情。
疫情让何佳滢本该在研二做完的实习拖延到了研三,这意味着实习、法考、毕业论文、考公全都挤在了九个月之内,完全是地狱模式。

印象中,何佳滢25年的人生一直在考试,一场接着一场。每一场都以为是成功挣脱当前的束缚以获得自由,而实际上,每一场都是以逃避现实为目的的缓兵之计。
她非常直白地说,当初考研是为了逃避就业。
三年之后,就业问题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随时都能压垮何佳滢。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串数字的威胁性,如果具体到一个双选会上,就是一份硕士的简历和一份本科的简历在招聘者眼中的区别,不外乎前者比后者多出500块钱的起薪。更尴尬的是,不少硕士生仍然拿着大三的实习经历当工作经验。真故的人事悄悄告诉我,刚刚过去的金三银四就业季里,她平均每天都会刷掉二十多份硕士学历的简历,其中不乏北大、复旦、港大等等,
理由很简单:没有工作经验。
何佳滢非常清楚自己的简历有多么单薄。所幸她还算是擅长考试的人,所以考公是唯一的选择。某种程度上,这条路更难走。
2
021年浙江省考总报名人数有三十多万人,平均比例是56:1,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有四千多人抢一个名额。
何佳滢和她的父母一起精挑细选了一个只有二十多人报考的岗位,但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前,她需要先把论文搞定。
图|某地省考现场
“你觉得写毕业论文最难的是什么?”
“我跟所有人、所有东西都不熟,导师、专业、文献、同学。”
我们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延毕的问题。一听到“延毕”这两个字,何佳滢就触电似地反应过来,语速很快,还带着颤音。她说有时会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登记表,表格里会有学号,有几个学号是16、17届,在一堆18届的学号里特别打眼。那个时候,她才切实感受到了“延毕”的真实。
“心里当然很慌,”她说,“我有时会看到他们,浑浑噩噩,死活写不出论文,甚至对时间、年龄都失去了感知。还是有点可怕的,我真的不要变成那样。”
去年十月份,法院的实习终于快要结束,何佳滢马不停蹄地扎进文献堆里,昼夜不分地做笔记、写综述。还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她要看完40篇中文文献、30篇英文文献,写出3万字的成稿,每一条参考、每一个脚注都要格式正确。
最紧张的时候,整个星期只睡了不到10个小时,脑神经里除了各种法学术语根本容不下任何其他信息。有一次,她妈妈切了一个梨子放到书桌上,顺便说:“眼睛累了休息一下。”但是她等到妈妈快要关门了才反应过来,回头去问妈妈刚刚讲了什么。
2020年12月31日,还有7天就要提交终稿。何佳滢已经按照导师的意见推翻重写了一遍。凌晨4点27分,她敲下了最后一个句号,一边琢磨着对这份论文的信心至少有七八成一边返回目录仔细检查错别字。就在鼠标移动到第一页的瞬间,整个word文档突然乱码,接着电脑整个死机,她两眼一黑。
 论文是死的,人是活的
论文是死的,人是活的
自杀的念头一闪而过。何佳滢叹了口气,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起身,拉开灰蓝色的窗帘,看着灰青色的天一点点变亮,她感到一股独自受难的苦楚。躺在床上放空了两个小时之后,她心里做好了延毕的打算,并发一条朋友圈来宣告这个毁灭性打击。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说可以试试数据修复。一语惊醒梦中人,何佳滢马上找了一家可以远程操控的淘宝店。客服说,“有80%的可能修复数据。”她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在看着屏幕上的文档开开合合的一个多小时里,这个原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一直在双手合十祈求各路神仙,如果修复成功,她真的愿意吃素一年、去普陀山还愿。
上午11点03分,折磨人的毕业论文终于回来了。她马上把论文发到父母的微信对话框,还有五六个朋友,让他们帮忙备份。做完这些之后,她顿时筋疲力尽,倒头就睡。
读研只有两天是开心的,开学那天和毕业那天。
无论是国内国外,研究生的精神状况都异常堪忧。2018年,Nature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研究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是一般人群的六倍之高。而我国的《2019年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在调查中也发现,60.1%的研究生有焦虑倾向,35.5%的研究生有抑郁倾向。原来读研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就连心理素质也暗中标好了及格线。
在豆瓣小组“学术垃圾”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研究生在自嘲是生产学术垃圾的学术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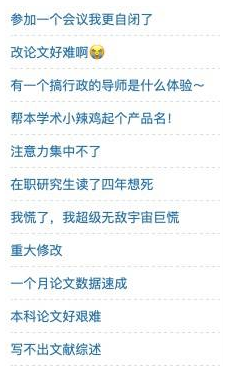
袁源在研一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这种以卵击石的沮丧和痛苦。她是个理科生,语言学带给她的趣味也是理科的。她并不在乎语言学和哲学的交叉反应,而专注于语言的音素,发音看似抽象随意,其实有可量化的客观标准,就像做化学实验,每种元素都有固定的分子组合。
她是被调剂到某双一流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在去学校复试之前,她甚至连学校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她说,研究生本来就不如本科生那样是学校“亲生的”,而她的实验语音学方向,可以说是学校里最边缘化的。“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过客,这很奇怪,是吧?”
只有一个导师勉强符合袁源的研究方向,也只有少量课程符合袁源的学业要求,没得选。无论是用文献检测法来分析《韵书》,还是花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翻译只有三万字但通篇都是术语的《概念转喻》,抑或是给语义学写一篇以“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为题的课程论文,全都跟她的实验语音学大相径庭。研一带给袁源的折磨是看十遍《降临》都恢复不了。
2016年的电影《降临》头一回把语言学摆到公众面前来讨论。袁源记得当时看完很激动,虽然电影很扯,但终于有一个具体的场景来“炫耀”语言学的力量。可惜电影的影响昙花一现,现在她跟别人提到自己学的语言学,别人要么说“学外语的”,要么说“学汉语的”,很尴尬。

图|《降临》剧照,书架第二排的照片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乔姆斯基
大部分时候,袁源都像一个埋在沙子里的鸵鸟那样读文献,自学设计语音实验,成为放羊式科研受害者的一员。
最难熬的是孤独。
何佳滢曾经翻遍通讯录也没找到一个朋友陪她吃生日蛋糕,本科的好朋友都在外省。她看向戴着耳机追剧的研究生室友,犹豫了好一会儿,也没开口。
苏智远常常默默地退出办公室,暂时结束像个智能机器人那样画图的一天,一个人走在凌晨的路上。这条从导师办公室返回寝室的路只有几百米,他已经很熟悉了,熟悉到能闭着眼就指出垃圾桶在哪棵树的旁边。非常疲乏的夜里,他会在银杏树底下的长椅默默坐半个小时缓一缓。他觉得没什么话能告诉父母和朋友的,他们帮不了什么。就算是同病相怜的室友问起来,他也只会随口一说:
“哈哈,好累啊。”
迷宫里的怪物
研究生学院就像一个米诺斯迷宫,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却出不来。困在迷宫里里的怪物正是实验失败的、论文被拒的、熬夜工作的、淹没在文献堆里的、身无分文的研究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