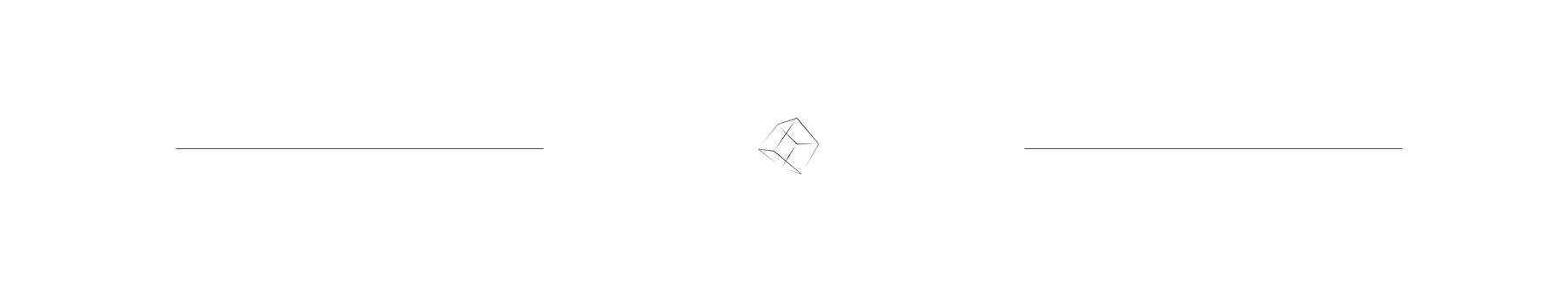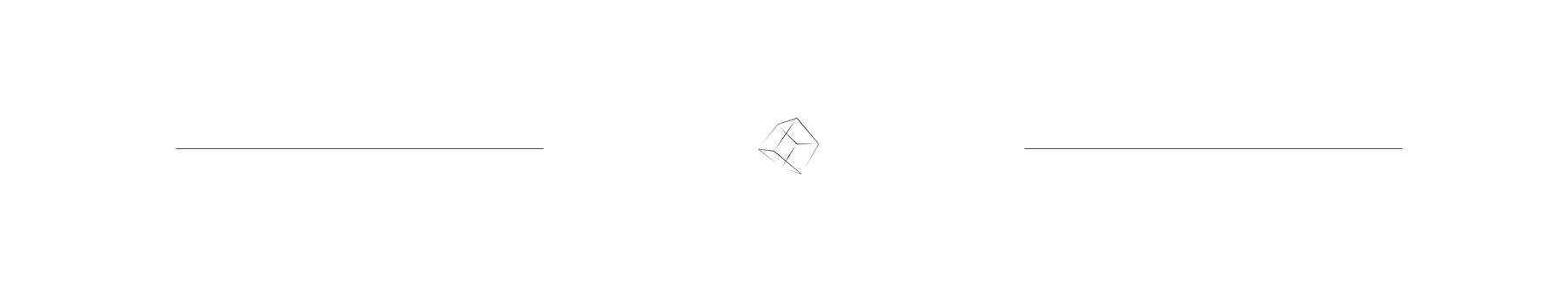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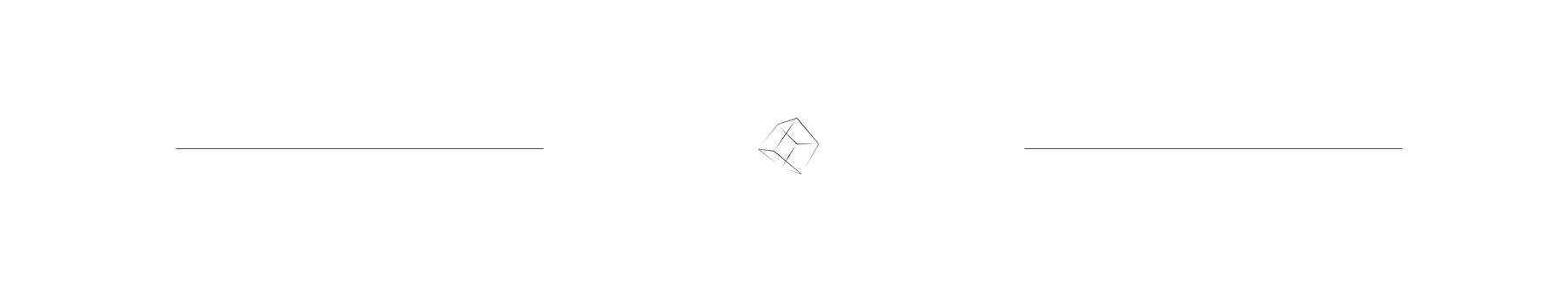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北京丰台区西罗园二区,蔡聪在这里工作了7年。
南三环的景色和我们活跃的东三环存在着直观的视觉差异,低矮破旧的居民楼对年轻人的吸引有限。早上十点钟,蔡聪办公室的楼下,六七个年龄跨度30岁以上的居民在争吵——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沓传单,究竟是从西边
先发还是东边先发,两股势力僵持不下。
前一天,蔡聪的团队——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接受了NHK的采访,以迎接2020年日本残奥会。“不吹牛的说,目前一加一是国内残障人公益做的最专业的,国际上也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他们的网站上罗列着有曾合作的伙伴,从BBC到哈佛法学院到香港乐施会。和媒体打交道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应对那些已经被问了无数遍的问题,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肌肉记忆。“个人层面,我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厌倦,但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受众可能又少了一个了解的机会。”
十多年,他担任着盲人世界的导游。手中的盲杖,像是随时可以被挥舞的小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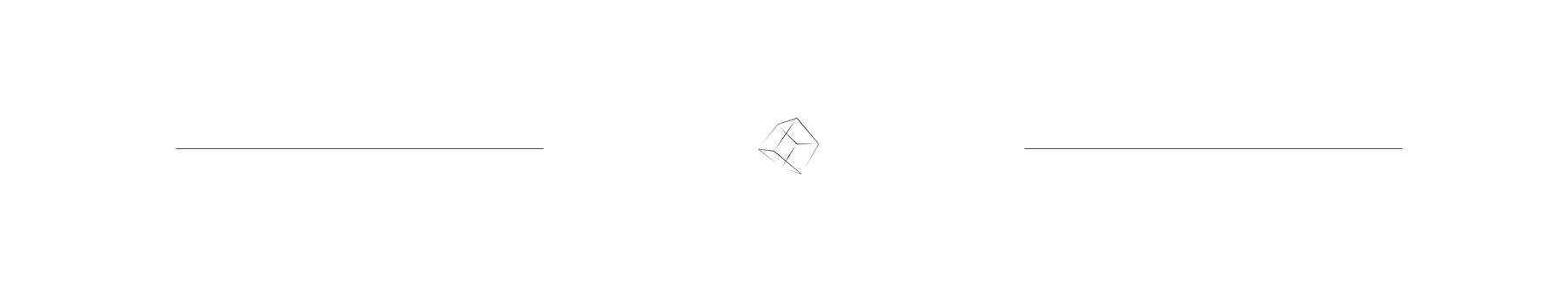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听觉的“超能力”,只是因为“不得不”
好奇心来源于《奇葩说》的后台。我观察到蔡聪一个人站在墙边,低头操作着iPhone,手速极快。
智能手机普遍配备了无障碍功能,iOS系统几乎能将所有的交互信息通过语音的方式传递。这对于“外人”,是科技发展的惊喜;而在蔡聪看来,这是科技发展的必须。
他向我们演示了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快速切换一个APP,输入文字,选择同音字,甚至机器描述图片。他最常用的读书软件是Kindle,理由是Kindle电子书无障碍做得最好。他选取了一段文字后,我们听到一段叽里咕噜的语音——这是用若干倍的速度朗读的文本。他不但能够听懂,甚至能够原本复述每一个字和英文单词。
这并不是一种超能力,这是一种对于盲人同等的求知欲,必须锤炼出来的听觉能力。“速度可以一点一点的加快。”
之所以成为“科技发展的必须”,是因为他经历过与大小企业的抗争。
“谷歌的系统是开源的,很多国内的手机厂商在开发自己的系统时,语音功能就莫名其妙消失了,或者是因为设计上的冲突不能用了。这几年我们和小米沟通了很多,2016年语音功能已经恢复地差不多了。去年华为,我们群情汹涌召集了一千多人签名,敦促改进。据说改进已经进行。”
“但还有个问题,好多第三方的APP是不支持语音的。微博微信,一上市的时候,我们都去沟通很多。Uber本来支持盲人操作,但是和滴滴合并后,体验变得非常不好。”
在和企业沟通时,对方从面子上充满了诚意——“我们理解你,我们也知道你们有这样的需求。”而这些反馈后面往往紧跟着一句“但是”——这个涉及到多部门协作,有各种各样的成本,有更多更重要的计划,等我们把这些做好了,再给你们改。而在国外,无障碍功能对APP来说,是一个基本要件,否则可以理解为bug般的存在。美国的508法案、日本德国的反歧视法案、电信条例,以此为据,外国企业历经无数次被告,最终在实然上,最大程度拥抱了特殊人群。而国内的相关规定简单松散,对蔡聪等人来说,这件法律武器并不趁手。
“只能不断沟通、沟通、沟通。”
当声音成为他们构建世界的全部,对声音的需求就变成了生存需求。
香港、日本、澳大利亚,每一个街头的信号灯,都会发出嘟嘟嘟的提示音。北京也有,可只局限在个别的大路口;杭州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结束后,这些刚刚安装的声音装置就被拆除了——理由是居民投诉声音扰民。
蔡聪提到香港:“香港街头很狭窄,两面都是居民楼。信号灯嘟嘟嘟的声音影响了居民休息,就有人反对。后来,盲人、居民和市政人员坐在一起,沟通出了一个方案——在每个信号灯上安装环境噪音感应设备。噪音大时,提示音就大;晚上噪音小,提示音就小。这是解决思路的问题。”
盲道,即便没被占用,也并不能更好地帮助盲人确定自己的位置——足下的凸起无法告知他们经历了哪些店铺和路口。配合智能手机,使用蓝牙节点增强在各个位置手机定位的精度,提供参照,已经在美国机场得到尝试。
导盲犬,在中国只有一百余条。每只导盲犬的培训费用在20万以上。“四不原则”——不呼叫、不抚摸、不喂食、不拒绝,尚未成为公众对工作中的导盲犬的应对常识。
无障碍设施——电梯、通道,在北京得到了广泛建设。可是它们往往大门紧闭,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人用”。
中国残联2010年公报,给出了8502万残障人数统计,其中视觉障碍1263万人。这意味着全中国1%-7%的人,想要听到信号灯给予他们通行的提示,想要在路口拥有准确参照,想要搭乘无障碍电梯。
中国的大街上少见残障人士,不是他们不想出门,而是在没有嘟嘟声的路口,每次出门,都是场冒险。
有位残障人士问蔡聪:“我出去,还能做什么呢?”
他们已经忘记了上街的感觉,已经将与世界的互动逐渐从生活中抹除,
如同生活在一个彼此不相干的平行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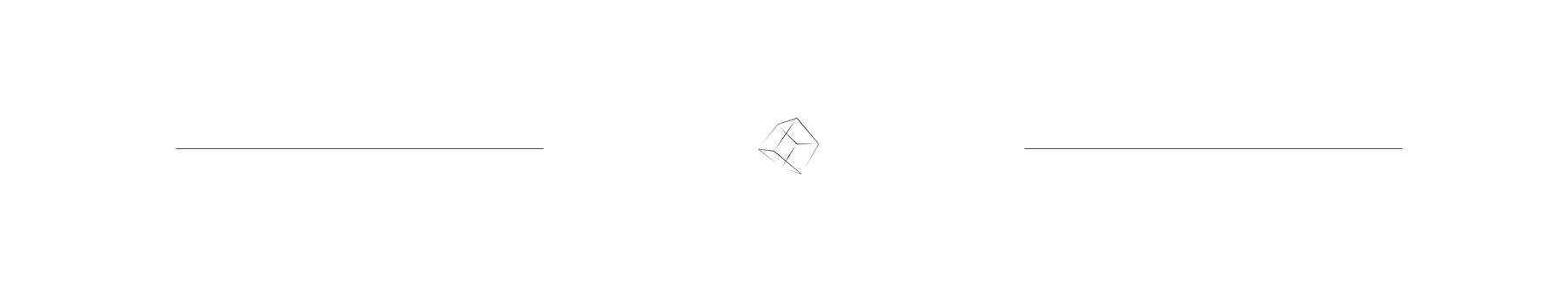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我们没必要证明自己能做一切。”
蔡聪和很多盲人,经历过一段自我抗争。
盲人,分为先天和后天。后天致盲的自我接受显得更为艰难。
“一个人不管多乐观,多坚强,如果遇到否定自己的环境,都会经历挫伤。有的时候我问路,对方说你瞪着俩眼睛怎么看不见呢?我也会很刺痛。有人承受能力差一些,就会为自己的残障有自卑感。”
一加一,给蔡聪一群人,提供了彼此的心灵支持。在外面受的伤,回到这里,被骂两句,被安慰一下,被开开玩笑,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灰暗以外的暖色。
“开始的时候,我们急于证明自己什么都能——这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起初的财务、项目执行、大型培训、物料管理、场地布置都由盲人同事、脑性麻痹的同事亲自来做。在某次活动上,他们亲自挂好了横幅,直到观众说出来,他们才意识到挂反了。后来他们冷静地反思了这种问题——寻求了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开始接受视全人的帮忙。目前,办公室中有相当比例的同事,是视全人士。他们培养出了分工——视障人士负责文字工作、脑力输出;视全人士拥有社工经验,负责执行。
据残联2015年公报,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达到17171个。按摩床仍然是盲人就业的主力战场。
“就业对于所有人都一样,‘我是选择一个不太感兴趣,但是收入不错的工作;还是我感兴趣,但是收入未知的工作’。按摩对于盲人来说,也会是这样的选择。”
蔡聪反复强调,按摩并不苟且。有个盲人朋友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级别,他曾对蔡聪说:“我的工作稳定,你看,收入也比你高很多。万一你们机构哪天黄了,你是不是还得回来按摩,给我打工?”
他说:“有可能。”
但这显然不是他感兴趣的。视力健全与否,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梦想归依。他想要尝试公益工作,也坚持做了下去,一面以社会捐赠维持运转,一面在社会上取得源源不断的声誉——他也想过做不下去的那一天。而那份失败,将一如他人工作的失败,只代表工作的失败。
广播、接电客服、速记、心理咨询师、律师、歌手、写网络小说、开淘宝店卖电子音像产品……蔡聪列举出视障人士就业的无限可能。可是用人单位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这儿不雇按摩的”,甚至他们无法想象盲人可以流畅地操作电脑。即便了解盲人亦能使用电脑,可仍存在诸多顾虑,比如PPT。“开会放PPT,你提前发给我就行啊。我用读屏软件,就能看。”
蔡聪回到办公桌,演示了电脑操作。他正在编写一份残障人士沟通训练营的工作计划,右下角的输入法显示正在使用五笔。
“我们学会接受自己的能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