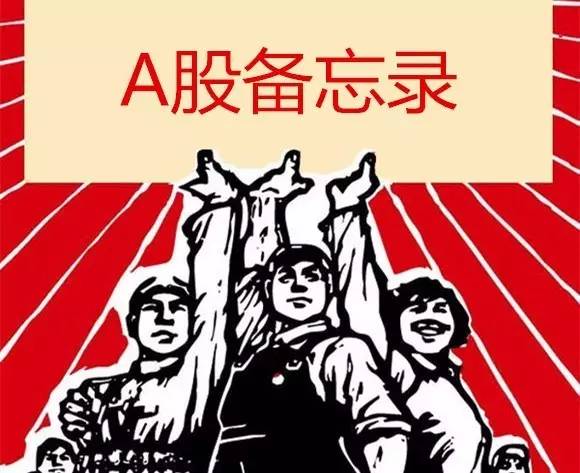齐景公问政,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是劝喻齐景公恪尽职守,做出个君父的样子来。可齐景公没有听懂孔子的话,他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显然他不是从有我之境上思考自己作为君父的责任,而是片面地将臣子对君父的忠孝义务,理解为硬性的名分制度,将道德话语变成了法律话语。但在做此转换时,他却没有将君父对臣子的仁慈义务,理解为硬性的法律话语,也就是说,没有将有我之境相应地转换为无我之境,于是便形成了君父对臣子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子对君父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片面化权利义务关系,这是有我之境的法律所必然呈现的格局,其基本表现便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称。
有学者说:“东方伦理之缺点,在详言卑对尊之道,而不详言尊对卑之道。”笔者以为,东方固有法律确实未详言“尊对卑之道”;但是说儒家伦理思想不详言“尊对卑之道”,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
前引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不包含“尊对卑之道”。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尧曰》篇分别引尧、商汤、周武等古帝王语,均涉及“尊对卑之道”。
尧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下面“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都是在“泛言帝王之道”。
《孟子》里也有不少涉及“尊对卑之道”的论断,譬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儒家经典中还载有不少“君不君”、
“父不父”的反面事例,譬如《左传》中提到晋灵公“不君”和蔡侯“不父”等事。
上述这些儒家话语,是不是可以作为硬性的法律话语来理解呢?国人至今仍在犹疑彷徨;然而在西方,早就实现了这样的话语转换。谭嗣同说:
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于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借口重刑之,则请自君始。
谭氏对于西方法律的描述,容有未确,但大意不错。西方近现代法律对于国事罪限定极严。美国的国事罪是由宪法规定的,只有叛国才可以构成国事罪,且仅限于对美国作战或依附美国的敌人两种行为。据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由宪法规定叛国罪的立法意图,是严防司法或行政当局借国事罪之名,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或侵犯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的待遇也迥然有别,原则上不予引渡。与此同时,法律对于国家元首、政府官员则有严格的约束、监督和弹劾程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裤裆门”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2005年路易斯安娜州的一场风灾,布什政府广遭抨击,不得不引咎自责,这难道不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躬有罪,无以万方”,“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现代西方法律版吗?
贺麟先生说,儒家式的法治即诸葛亮式的法治,其特点是“去偏私”。马谡违背诸葛亮军令,致使街亭失守,诸葛亮上书“请自贬三等”。当时诸葛亮掌握着蜀汉当局的最高权力,但他并未网开一面,宽纵自己,这就叫“去偏私”,用本文的话说就是“无我”。简言之,无我之境的法治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法治,没有可以例外的“我”,最高统治者亦然。
贺麟先生说儒家精神的法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法治相近,确乎不错。现代宪政文明下的法治,莫不臻于无我之境,即便是政事纷扰的台湾地区,近来亦有可称道的跃进。据央视报道,2007年8月28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时事评论家胡忠信诽谤陈水扁之女陈幸妤“前往美国(银行)开户,疑似洗钱”罪名不成立,陈幸妤败诉。贵为“公主”,也不能置身法外,单就此案来看,台湾地区司法体制似已进入了无我之境。同为炎黄子孙,能不为彼岸同胞的进步而高兴吗?
有位西方学者曾形容过中西方法律的根本差别,他说中国古代的法律:“更像一种内部行政指示⋯⋯而不大像法典,甚至连一般的法规都不像。”他解释说:“在研究中国法律时,必须从法官并且最终从皇帝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这与西方人“总是倾向于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去观察法律”截然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他的答案是:“对中国人来说,法律就是靠严刑推行的命令,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潜在地无处不在的,全权的政府的一部分。”易言之,就是“朕即法律”。
这个观点在美国汉学界很有名,以往我总是似懂非懂,如今一下子领悟了,原来无非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有我之境的法律,皇帝就是那个“我”,一旦触及到“我”,或与“我”有关的特定主体,法律便失灵了。因为“皇帝是法律承认的惟一的‘人’。但他是没有义务的,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单方面的,因为他从不服从任何其他人”。西方近现代的法律是无我之境的法律,根本不存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