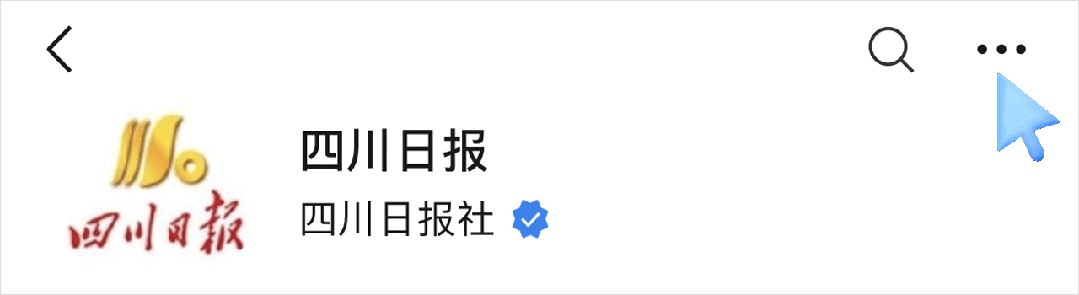
 (点击图片进入报道专题)
(点击图片进入报道专题)
设计一款文创商品,不仅需要巧思,更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文化内涵,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
博物馆的功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应坚持保存文物、开展研究、策划展览、教育公众等核心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馆藏文物来自大陆,它们承载着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就像一条文化脐带,让两岸彼此相连
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同属中华民族,相互合作、相辅相成,这才是最好的
人物简介
冯明珠,
祖籍湖北,1950年生于香港,197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后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清史、藏学、档案学等方面研究。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处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院长,至2016年卸任。其间,不仅积极参与推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文创产业发展及南部院区兴建,还为两岸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现为民间团体宝吉祥文史教育协会理事长、冯明珠文史研究院院长。著(编)有《冯明珠藏学论文集》《故宫南院胜概》《清宫档案丛谈》《故宫近事录》等。
日前,在江西景德镇的一间茶室中,来江西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

川观新闻记者和冯明珠(中)
对话从她编著的《冯明珠藏学论文集》开始。看到记者手中的这本著作,冯明珠眼睛一亮,“很多人认识我都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和文创产业开发开始,但我最早的研究方向其实是清史。”冯明珠告诉记者,清史与藏学,特别是中英关于西藏交涉的那段历史,既是她研究的起点,也是促成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结缘的开始。
香港出生,台湾求学;从受聘参与《清史稿》校注开始频频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接触,到后来入职扎根;从文献研究与保护开始,到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再到开创文创产业、推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设南部院区……冯明珠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她说,回想起来,每一步都是因缘际会,但每一次选择都是遵从于内心的热爱。
1950年,冯明珠出生于香港。她的父亲原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大学机械系,虽然是理工科出身,却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在携家移居香港后,他不愿让子女接受殖民地教育,便将他们送到远在调景岭的一所学校就读。
彼时调景岭一带聚集着不少从内地移居过去的知识分子,当地学校所开的课程、所用的教材等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冯明珠至今仍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国文、历史这些课讲得特别精彩。”不仅如此,父母还常常在家里给他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故事、传授背诵《古文观止》等国学经典,“不上课的时候,父母还会带我们去看《东江之水越山来》《北国风光》等介绍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片。”
家庭氛围的熏陶、教育环境的影响,在冯明珠心中埋下了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她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兴趣尤甚,“上小学后,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讲述历史故事的《东周列国志》。”在中学毕业后,她顶着父母的压力放弃了自己颇有优势的理工科,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学习。
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改变了她的人生。凭着自
幼在国语、文史等方面的积累和对历史专业学习的勤勉热忱,冯明珠在新生中脱颖而出,在当时名家云集的台大历史系受到多位师长的青睐。“大学每个学期,我都有拿许多奖学金,基本上大二后学校的注册费就没再让家里掏过钱。”冯明珠说,历史是自己喜欢的课业,自然也就学得投入。因为学有余力,她还广泛涉猎考古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这也为她后续进入文博行业打下基础。
大学本科毕业后,冯明珠随家人在台湾一所中学任教,但她心中始终无法割舍对历史的热爱。一年后,她又重新考回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出生、成长的特殊际遇,让冯明珠对近代以来外国势力在华殖民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在学校相关专题课程的启发下,她决定将清史作为研究方向。20世纪70年代后,适逢台湾当局逐步开放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总理衙门档、北洋政府时期外交档等资料供外界阅览抄录,冯明珠不断挖掘史料,最终将研究旨趣聚焦到近代以来的西藏。“我的大部分学术研究,其实都与清史、藏学等主题有关。”冯明珠一开始并未想到,在史学园地的精心耕耘,最终成就了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足足38年的缘分。
1978年硕士毕业后,冯明珠在导师推荐下参与了一项重要文史项目——校注成书于1927年的近代史学巨著《清史稿》。该项目在国学大师钱穆倡议下启动,由台湾当局相关文史机构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执行,要用“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法,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海量清代史籍档案为依据,结合应用史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逐条考订《清史稿》原书各类歧误、纰缪并加以注释、载入注中。
校注工作漫长而枯燥,项目成员身份仅为临时聘用,缺乏未来保障……随着时间推移,同事陆续选择离开。家人也多次劝她放弃,毕竟作为台大高材生,当时要另寻高就并非难事,但冯明珠却选择坚守。
“那时候我很年轻,根本没想过退休后没有年资怎么办,只一心一意想完成好工作。”沉醉于浩如烟海的清史档案,她甘之如饴,甚至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只用对史稿、读档案、写注释,就有薪水拿,还能得到那么多学者前辈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她从这份校注工作中感受到了身为历史学者那沉甸甸的责任感,“中国自古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何其多,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修史工作。我躬逢其盛,是一生的荣幸!”
据统计,冯明珠与同事历时6年,累计查考校勘《清史稿》4万余条内容,形成校注成果300余万字,摸清了《清史稿》底细,阐明、诠释了原书大部分问题,最终出版全书达1200余万字的《清史稿校注》,为未来进一步编纂清史奠定重要基础。
项目完结,但冯明珠并未离开。被她的坚守触动,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人员邀她正式入职图书文献处,继续从事文献管理工作,她也舍不得离开自己倾注了数年心血的这些文献档案。此后多年间,从干事到处长,再到副院长、院长,她秉承着前辈“敬业乐群”的人生格言,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伴成长。
把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做到极致,她不断精进在清史、藏学等方面的治学——深度梳理院中所藏丰富的清宫文献档案,将藏学研究时间轴向更早历史时期推进;结合陆续被发掘的史料,不断完善“近代中英关于西藏之交涉”“康藏议界”“川边改土归流”“川茶入藏”等主题学术研究;深入四川、青海、西藏多地开展实地考察,寻古探今……
把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做到极致,她在提高文物保护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献档案,率先推动清宫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为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全面启动文物数位典藏(数字化保护利用)计划打下基础;以引导更多年轻人了解文物、爱护文物为目标,开创性地将文物形象与商品研发结合,推动台北故宫博物院逐步走上文创开发之路……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座文化艺术宝库中,珍藏着包括毛公鼎、《富春山居图》、《祭侄文稿》等诸多稀世珍宝在内的近70万件/册文物,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文化瑰宝、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冯明珠一直思考的课题。

参观者在观赏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博物馆的功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应坚持保存文物、开展研究、策划展览、教育公众等核心价值。”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理念引导下,早在1983年,冯明珠就在兼职运营台北故宫博物院员工福利会时,摸索文物典藏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路径。“那时,国际上还没有流行有关‘文创’的概念,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参考。”冯明珠说,她与其他部门的同事集思广益,从最基础的文物明信片出发,逐渐讨论研发出结合文物形象的丝巾、领带、胸针、布料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体系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
思路打开,创新不断——引入更多合作方,设立艺术发展基金,成立文创行销处,开办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珍贵文物衍生商品设计竞赛……如今,这条文创产业链已经涵盖生活器具、珠宝服饰、数码电子等多个领域,每年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带来不菲收入。
为了进一步拉近公众与珍贵文物的距离,冯明珠还积极推进文物数位典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项目建设。“南部院区2015年12月底启用,第二年8月参观人次就突破百万。”谈及此,冯明珠备感自豪。
更令冯明珠引以为傲的,是她在两岸文博交流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故宫文物就像一条文化脐带,连接着大陆与台湾。”深耕历史文化领域多年,冯明珠知道,文物研究离不开文化背景和脉络渊源,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的根在大陆,要做好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研究,与大陆文博界的交流合作极为重要。
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清“翠玉白菜”。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实现院长互访,北京故宫博物院精心挑选37件雍正相关文物赴台北助阵“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完成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首次正式交流合作。此后两地交流渐频。2012年,冯明珠就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两岸文博界更是迎来交流合作的高峰。
数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大陆多家文博机构在文物保护、图书出版、文创开发、办展办会等方面开展了密切交流合作;冯明珠更是数度前往大陆,为洽借文物赴台、召开学术研讨会、拟定人员交流机制等具体项目积极奔走。在此期间,受益于当时两岸关系改善的大环境,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观光人数、门票业务及文创业绩上的表现也屡创佳绩,为此还专门启动了旨在场地、展品全面升级扩容的“大故宫”计划。
2016年5月,冯明珠卸任退休,离开了服务38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她依然心系两岸文化交流,衷心期盼两岸文博界还能再有水乳交融的美好时光,“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同属中华民族,相互合作、相辅相成,这才是最好的!”
谈文博管理——
坚持“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的理念
记者:
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结缘于文献研究,此后也是您倾力推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古籍的数字化保护利用,能否分享相关经验与成果?
冯明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总数近70万件(册)文物,其中约60万件是图书文献,包括宫中档、军机处档等清代档案40万件,以及历代善本古籍20万册。自校注完《清史稿》正式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我又和图书文献处的同事们开始做清宫档案文献的编辑工作。
随着一份份档案编好出版,大部头出版物几乎压塌了博物院出版物库房的书架,大量书本的管理养护工作也很繁琐。到1997年前后要编军机处奏折录副时,我就建议,不要再出实体本了,做数位档案吧。就这样,我们率先开启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数位典藏作业。
至2002年,在台湾相关计划支持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全面推进馆藏器物、书画、古籍、图档等各类文物的数位典藏。到我担任院长并主持完成第二期计划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建成涵盖器物、书画、善本古籍及先秦铜器纹饰、明清舆图等不同主题的21个数字文物资料库,为博物院更好地开展文物管理、展览规划与设计、教育推广、研究出版、文创开发及观众服务等业务发挥功效。
记者:
在您担任院长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顺利开馆,自筹建到开馆历时15年。这一分院的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冯明珠:
台北故宫博物院地处台北,如何兼顾台湾中南部及偏乡、离岛观众的文化需求,成为历任院长念兹在兹的事。
200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正式提出,项目选址嘉义县,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工程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10年,项目方得以重启;我担任院长后,与周筑昆、何传馨两位副院长领导团队克服种种困难与压力,持续推动项目建设;至2015年12月28日,南部院区终于开馆运营,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献礼。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开馆十大首展,我们相继策划推出“奔流不息——嘉义发展史”,以及日韩瓷器展、南亚服饰展、伊斯兰玉器展、亚洲纺品和茶文化展等。至次年8月,参观人数突破百万,超过法国卢浮宫朗斯分馆开馆首年运营成绩。
回想起来,这个项目建设历经五任博物院院长,终在我卸任退休前顺利开馆运营,总算不辱使命。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与北部院区相互辉映,共同肩负(台湾地区)“南北平衡文化均富”使命职责。
记者:
在您担任院长期间,以“朕知道了”纸胶带等产品为代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曾风靡两岸,请谈谈您所亲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业发展。
冯明珠:
如今,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品牌的文创产业链世界闻名,涵盖生活器具、珠宝服饰、数码电子等多个领域,每年带来不菲收入。这不仅归功于博物院上下近几十年来的全力推动,也要感谢秦孝仪院长当年打下的基础。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发展文创的先行者,其愿景提出远早于英国布莱尔政府的“Creative Industries(创意产业)”计划(1997年)。
从入职一直到退休,我参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发展前后有33年。“朕知道了”纸胶带,源于我2004年策划的“知道了:朱批奏折展”。当时的展览导览手册(图录)由我执笔主编,先后印刷了10多版,一直畅销,其封面即印有康熙帝满汉文朱批“知道了”。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结合文创设计竞赛获奖作品“古纹胶带”,于2013年正式推出这款文创产品,很快爆红并引发抢购潮。
设计一款文创产品,不仅需要巧思,更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文化内涵,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开发文创产品过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始终坚持“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创意必须来自文物”的理念,即使引入第三方进行研发生产,我们也会在设计阶段就参与审核。比如,“朕知道了”纸胶带就衍生自馆藏康熙帝御批奏折中的手迹“朕安”和“知道了”,绝非凭空杜撰。
谈文化愿景——
衷心期盼两岸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携手共进
记者:自2009年开启交流后,两岸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作为亲历者与推动者,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冯明珠:
在两岸文化交流上,我最感动的是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破冰之旅”——是年2月14日,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率团访问北京;同年3月,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回访台北。通过交流互访,大家在人员互访、展览交流、学术研讨、出版品互赠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翻开两岸在文化领域交流合作新的一页,这是来之不易的成果。我当时是副院长,全程参与其中,与有荣焉。
尤其是在合作办展方面,双方可谓不谋而合:当年10月7日,我们携手合作的首个展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拉开帷幕,分藏于两岸的故宫文物时隔一甲子再次聚首。当时展出的246件珍贵文物中,有37件文物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包括雍正皇帝朝服像、雍正行乐图和“为君难”宝印等;我代表台北方面在北京参加了出借文物的装箱启运仪式。
这次展览历时3个月,引发巨大轰动,累计吸引参观者超70万人次,成为两岸故宫博物院深化交流合作的良好开端。此后8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多场重要展览上都有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例如2011年举办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14件文物精品;2013年策划的“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特展”,200件展品中有多达45件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2015年开幕的“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又有8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画作。
此外,我们还先后举办了5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共派人员参加“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等活动,并在文物保护修复、书籍出版、文创开发售卖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合作。
记者:不仅是两岸故宫博物院,在那段时间,大陆与台湾的文博机构也往来频繁,交流合作空前活跃。在与大陆博物馆(院)的合作中,您认为有哪些成果亮点?
冯明珠:
2008年至2016年间,除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密切联系,我们还积极与大陆其他重要博物馆(院)和文化机构开展交流互访,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最早的雍正文物大展,除了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还有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珍贵馆藏。又如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浙江省博物馆借出“剩山图”,与我们的“无用师卷”一道并列展出,让受焚损分离360余年的传世名画历史性合璧;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等大陆博物馆(院)也纷纷借出馆藏黄公望书画珍迹共襄盛举。此外,还有2010年的西藏文物展、2012年的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和西周文化特展、2015年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展……都得到大陆方面的鼎力相助。
我担任院长后,于2013年1月首度正式率团访问大陆,先后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博物馆(院)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更多共识。同年4月,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又率团回访台北,赠送我们一幅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复制品),我们也回赠了一幅郎世宁的《聚瑞图》(复制品),寓意双方交流合作“平安聚瑞”。
总之,得益于当时两岸关系的改善,我们与大陆在文化领域展开多项务实交流合作。尤其大陆方面释放了极大诚意与善意,慷慨出借珍贵馆藏文物,并在各方面给予理解与便利,才让许多重要展览和活动得以举办。其间,大陆观光客的到来,也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与门票收入屡破纪录。2008年至2014年,我们的观光接待量从224万人次增长至历史性的540万人次。
记者:
多年来,您始终心系两岸文化交流,结合长期在文博界的耕耘,您对两岸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有何建言?
冯明珠:
2025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据我所知,两岸都要举行多项活动庆祝百岁华诞。记得2015年,我们双方共同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积极策划、联合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如郎世宁画作特展、故宫及文物历史影像展,携手出版“三希帖”等,收获了巨大的反响。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我始终坚信,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馆藏文物来自大陆,它们承载着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就像一条文化脐带,让两岸彼此相连。
在这种文化连接上,情感连接同样密切。在我入职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仍有不少1949年赴台的“老故宫人”尚在院内工作,他们中有的人自1930年代便守护国宝文物一路播迁,最后因种种原因,终其一生未能再返回故乡,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让2009年的“破冰”更显珍贵。
“破冰”后的数年里,两岸文博业者尤其是两岸“故宫人”间交流频繁密切,许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大陆各大博物馆(院)的馆藏精品多次借展台湾,也让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领略更多国宝的魅力。至今,两岸文博业者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等方面依然保持交流。可惜由于一些因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一直未能顺利赴大陆展出,希望未来能有如愿的一天。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未来两岸文博业者能进一步加深合作、相辅相成,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携手共进,是我的衷心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