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不懂艺术都能看懂的
象外

图为阿改主编发在朋友圈的摄影作品
感谢大家,忍受了笔者又臭又长、绵延了五期的长文。因为想说的事儿又多又杂,借着“学院派”、这个可以高度泛化、指涉到当下方方面面的题,笔者发了一通文章结构脉络不是很明朗的牢骚。
上一期中,间接画法的素描/色彩观,和直接画法的二观间的其中一部分差别,是在某些客观共识的基础上,经LH的二手
(有“照着讲”也有“接着讲”)
,到笔者这里的三手
(三创)
;因为可能涉及争议性,所以不暴露ta名字,但想想又不能专美;只能补充一句,过于激化部分的锅都是我的。
这期最有趣的,是笔者下文中所谓的“私货”:笔者把“自辩”直接写成了“自黑”。说到底还是体系癖问题。当然,惰性的艺术体系一般来说是不太好的体系,但自觉自发的创作体系化……则分很多种情况,全文五期反复在聊的根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两句话概括。
咱真的会“say sorry”啊。
(引子)在当下艺术语境中,面对“学院派”问题的众生像
(三)以检讨“素描”和“色彩”两个概念,在当下美院语境中的概念生成和实践方式为例,看一看作为“保守”美德的“学院派”精神,是如何可能因“保守”而更“进步”的
(前半章的史料部分,主要参照佩夫斯纳《美术学院的历史》,克里斯特勒《艺术体系》等二手资料;史观部分来源复杂,但以梳理总结为主,适当部分“接着讲”了一点,若说拍脑门纯原创的观点成分,肯定没那么高)
现代性的进程,将美术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赋予了自律、闭环的系统话语意识。这也促成了,一系列,我们误以为是艺术中所包含的人文“本质”、接近于人心普遍深层秩序的东西,其实掺杂了大量工具理性、技术手法,这些东西,和我们对艺术终极目的的信念,混淆在一起。我们以为超然的、高贵的、代表个性解放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掺了非人性的、系统程序性的成份——也就是负面意义上的“学院派”的。
学院派意识先于实体的美术学院这一点,也可以由历史书写的前史追溯中,构筑的
传说中非实体的莱奥纳多
(即达芬奇)
学院,来侧面印证。并且,会还对标文艺复兴时的“学园派”,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复兴的伟大光。
实体的美院,自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始,据说,其创立,是基于在美术行会/工坊的对抗意识。
对立于套式修正/工匠教条,新的“学院派”绘画/雕塑,讲求“科学”探究的精神
(当然,文艺复兴时的“科学”观,和后世支配理科、并向文科渗透的实证主义“科学”,有所不同)
,用我们如今的归类法参照,也许可以称为,“研究型”造型艺术——
这样一种符合旧“科学”精神的美术,有着文艺复兴哲学,也就是新伯拉图主义世界观的底色;这套世界观,部分延续了中世纪的世界图景:存在巨链;
在实证科学、学科细分的萌芽之初,整合所有知识的文科通识,还是一个有效的信念;
神圣-自然-人,仍然共享于同一套可无限类比、没有差异褶皱的秩序。顺便说一句,据说,最早的美院,主要是维护协会会员/研究员权益的机构,其次才是教育机构。
作为被追认的“学院派”之祖,达芬奇在其《笔记》中,将线性透视、空气透视、色彩透视,当作三套相对独立的表现空间手法来记述,而非强调,一个画面、必须同时符合三种教条。分别是一种“观”,理论上,可以单独使用。
简单讲,最经典的线性透视,也就是透视缩短/变形的表现法则,在潘诺夫斯基以后,普遍被视为,和
笛卡尔理性主体的视角主义,属于视觉与认识论间的同构。而空气透视,就是把氤氲神秘的雾气,和我们说的远近虚实混杂在一起。
色彩透视,相当于对自然风景中“冷暖”的认知——虽然没后世的印象派那么细,但认知上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同样的现象,在画布上的表现方式,则是迥异甚乃对立的见解。究其原因,是对再现媒介/认识工具,之于主体视角的关系位置,见解/立场有所不同——也就是“representation
(常译作再现或表象)
”观的不同。
达芬奇绘制的大脑和头骨素描 约1510 图片为网络公版
达芬奇
洪水 素描 1517-1518
图片为网络公版
达芬奇
受灵领报 98x217cm 木板油画 1472
图片为网络公版
因为笔者才疏学浅,所以大体上,对于“再现”观史,仍然延用福柯的知识型分期法。一阶,
一个最低限度的肖似性符号,可以延伸出具有普遍共识的半中世纪头脑中,不断类比的链条,看到几点“表象”、便轻易地脑补齐背后的整个世界;二阶,对肖似/“像”的要求度变高,因为要为
不断扩张的无限“宇宙/世界”
,纳入有限秩序规则之下的秩序感心态,提供心理支柱;三阶,
知识系统取代外部对象,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符号的意义已然在于代表性、规定性,表象相似性变得无足轻重。这套大概的分期法,让人脑中立马冒出一部和现有“常识”不太一样的美术观念史,各处都可以对应上;以及,这套知识型史,虽然漏洞、瑕疵不少,但和其他的“现代性”史写作,也可以对应得上
(极左的福柯的“再现”观史,连和极右的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确”观史,居然是能串得上的;笔者或许以后会抓着各种“现代性”观的串联性,写一部自发胸膺的野路子西方美术观念史)
。
笔者想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观念对应的象征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语境中的“再现”“自然”
(毕竟“再现”是认识,“自然”是“理念”)
?我们以我们的语境,搞研究型绘画,表现我们时代局部共识中的某种“现实”感,会是表现什么东西?是不是该搞,
探究价值多元/相对主义在本土土壤的利弊伦理
(这可能确实像是特别适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土壤)
,以及合伦理地“再现”某种对应的观看/视觉表象形式?是不是要把古今之争的价值观裂痕、和缝合方式,变成某种相应的视觉形式,或者,发掘古代认知世界的习性和现代间,更深层的观念差异,并以现代的表现习性、转译出更“真实”的古代视角?
扯远了。回到历史上的“学院派”美术。希罗也好,文复也好,其实都只是被追认和“学院派”有关,并非无可争议的“
学院派
”。一般说来
(在笔者粗浅的认知里)
,最无可争议,总是被称为“学院派”美术的,是法国“新古典主义”。那是对“学院派”的标准,最友好的时光,也是人类历史上,美术学院在美术领域具有相对较合理权威性的时光。
法国“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连续性,体现了某种观念上的同时代性。在法国,古典主义是将“浪漫”的“古代”进行集体的礼仪化/仪轨化而得,“现实主义”,则是“浪漫”具身入小人物命运后的变种。
实际上,“新古典”复合了很多东西,波旁王朝前后的宫廷文化风气,让奢侈和“伟大”挂上钩,矫饰和庄严挂上钩,身体欲望和优雅挂上钩,进而辗转隐迹地塑造了法国大革命文化趣味的某个部分,法国的特殊、混合成为普遍的代表,而这种“普遍”,显得是一种错觉。
作为
绝对主体的
文化民族-共同体意志,是那时的“常识”;
现代国家的“总体”意志和绝对个体/私人的权利
(后神权的人性)
互为想象化的呼应;国王代表个体,象征了人作为主体的绝对意志;拉辛、高乃依,和大卫、安格尔,具有同时代性。斯坦纳对法国新古典戏剧特殊性的理解,可以同本雅明将德国悲悼剧与希腊悲剧的比较,进行参照,而更进一步,给出某种“新古典主义”绘画之形式特征的理由。
一顶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假发,用马尾制成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那也是小报漫画,作为启蒙时代产物,“流行”一时的时代。
文化工业,还和传播、讨论先进思想的阵地连在一起,
“流行”也还不是个贬义词
(在后世,“文化工业”代表着同质化且低智化的文化传播学逻辑,在迎合受众的同时、也将受众改造成麻木的、没有审美鉴赏力的人)
。
恰恰是公众与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艺术舆论场还没有撕裂的时候,便是“画得好”的规范最稳定、并得官方认可的时候。
但这种背景语境,毕竟是一时的、有其历史特殊的。一旦以“浪漫派”
(应区别,以德国理念论为底的“浪漫派”思潮,和文艺类型学、风格学所用的所谓“浪漫主义”,两者不是一回事。浪漫派不仅是文艺思想中、“现代主义”的源头之一,也是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特性的隐匿发韧处)
为代表的新时代、新思潮来临,对“天才”、“原创”等新信条的崇拜,就
瓦解了“学院派”艺术的话语势头。
如果说,德拉克洛瓦、席里柯的时代,美术史主线叙事仍在沙龙的体系内,那么到了印象派崛起的时候,“学院派”就真成了挨骂的靶子:那可是脱离现实、教条化审美、布尔乔亚阶级审美鸦片的代名词啊!
为什么布格罗,会被跟甜俗造作过气的堕落流行趣味,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比安格尔晚生了几年?还真是。一些东西变得不合时宜了,毕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接近永恒,“历史代表性”是会更易的。但说句公道话,所有过往的时光,真的都比现在要强,毕竟,古时候的郑声淫、靡靡《后庭花》之音,咱可以拿来读一读、听一听——搁现在人的耳朵里,何止听不出有多放逸,简直就是端着的、修养身心的“雅”乐了!
(当然,若真把古时的“雅”乐对比着听,倒是可以明白,比较下,那还真得算淫靡之声)

布格罗
柏彼丽丝 布面油画 48x79cm 1884
图片为网络公版
但如笔者在前面章节所述,作为知识系统主义的权能的一体两面,“原创”精神的自我作古、最终趋于内部编织的个性,和规训、教条化的“学院派”,未必没有内在同构性。就如
福柯所说,
马拉美式的、神秘、自制体系的纯诗,和被实证方法支配的文科,里面贯穿了同时代、有关联的知识型。
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很快就从反思形式语言的再现能力,变成了反思材料性本身。在抽象艺术崛起的时代,所谓的“形式”本身,变成了和材料性质紧密相连,绘画反思平面、反思基架,雕塑反思基座和空间关系,艺术的“本体”,仍打着理念的旗号,则以“系统”为中介话术,走向了由物质性想象奠定的艺术“本体”。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有意义的形式”,本义并不像字面那么开阔,而实际是一种狭窄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提倡,要优先重视,“材料因”“内在自具的形式”。“内在自具的形式”,这种文艺观,原本被视为文艺思想中,摹仿论/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源点,现在,头尾颠倒,成了纯抽象艺术的话术。但,其实,这不足为奇。从根上讲,咱眼里的所谓纯抽,和咱眼里的所谓写实,共享一套形而上学嘛。
而格林伯格的绘画本体论
(基于材料特征的纯粹“形式”)
,紧接着当然是丹托所说的风格矩阵——毕竟,“系统”的要求,一方面要创新,但另一方面,“创新”这一教条,也必须在算法可控的规训之内。
最后,既然在聊历史了,我们不妨再次大概聊一聊
(其实前文已经聊过了)
,“当代艺术”,和“学院派”思维的关系
(但因为和早前史不同,“当代”的主线不太好短小篇幅内处理,所以笔者史观大于史料的毛病,就更放大了;反正我们还是在艺术批评的范畴,不是在学术论文的范畴)
;在两个层面上都有纠缠。其一,一方面以反系统为教条,所以在呈现的方式语言上,系统算法的固化惯性所推演出的有脉络可循的“创新”,就更令人难堪/发指;讲求
学科分化之后的“跨学科”意识
——从笔者用以概括的词组,就可以看出尴尬所在
。其二,
“当代艺术”
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紧密关联,建制化的价值相对主义;举例来说,以美式的、学院性建构的学科高度细分化、通过实证化而趋向知识泛平等化
(向下的)
的偏爱
(源于德国,放大变味于美国)
,吸取只要激进真理、不要社会体系建构上的合用性
(文化安那其主义)
的法国思想;进一步,献给全世界
(笔者这话让人想到《十月》派对不对?)
……嗯,懂的。至于国情特色,前面几期聊多了。
〇
5.1“反学院派”=另一种“学院派”?
如前文所述,当一个艺术家,点对点,概念性地反转“学院派”教条,以此为方法,形成自己的新方法论体系的时候,那么,在本质上,ta多半可能仍是一个“学院派”,一个变了形的、激进的新“学院派”。
左 谭坦 Floating in Music 布面油画 60x80cm 2016;
右 谭坦 一把椅子 布面油画 120cmx90cm 2024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右图亦无法反映原画长啥样
谭坦的焦虑在于,按照学院派的其中一种色彩标准,她驾驭丰富和明亮的色彩关系的能力,得到广泛认同;但这种画法在一段时间之后,影响到了她的情绪表达。于是她选择
最低限度的颜色,来为
形状和构图作陪衬;但实际上,越到色简,从颜料层透出、漏出的颜色,在表面颜色的关系意味,就越复杂。而当物像放大、以类似特写镜头的视角逼视局部后,平面构图就变成了实际是心境的空间化呈现的功能(这一项可能是艺术家的主要追求)。画面里的每一功能组件,都在复合的层面上、发挥了多重功能。
艺术家的“减法”,本意是追求“纯粹”,但是,除了乍一眼视觉上的“纯粹”,实际上,功能意味变得复杂。这就是典型的,在“学院派”意识底下,做出的反学院派(具体到她,为“反色彩”)主张。
点击:
一篇关于谭坦,“转机请向右”的评论
许多人,对这种矛盾,是自觉的,并相信,这种状态是自己的真实,是“保守”和“系统癖”的双重本能在发挥作用,但因为现有的固化旧体系实在有所欠缺,所以看上去,得自我作古。
由这一类型更进一步,还有一些人,相信过激/破格欲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就像样式主义对古典主义所做的,晚期风格对成熟风格所做的,这种形式意志,是内在于人性的。尽管反对者会觉得,这样做太概念先行了。
(参:德勒兹论培根,“图表”可以辅助加强心灵动势的强度,而非两者对立。笔者觉得,可以引此作为辩护。坦白说,如果作为哲学看,笔者觉得,德勒兹的写作、无甚新洞见,只是在立场宣言式的姿势加持下,给一些常识般的当下史现象,发明了一些“新名词”。但要搞当前艺术的评论文章的时候,不得不说,他那一套套的真好使)
反对者的观点,则认为“概念化”的反学院派,是理论指导心灵,和绘画性讲求的身体感受性、直觉的逻辑、围绕“形”本身展开的思维,是矛盾的。用头脑做“制图术”是合理的,但搞绘画性,就抵牾了。
反学院派本是为了踢掉刻板、以
解放绘画性
(=手感)
和心灵的对应关系为初衷,既然如此,不从生活体验出发,概念化地硬上,就南辕北辙了。
其实笔者的实践经验,让笔者倾向于后者的说话,更合乎人性的自洽,但笔者的追求意志,让笔者可能更倾向于站前者
(笔者确实有点认同于“异化”,简直是在反“人类”的赤子心了)
。在这里,为了让这个问题清晰化
(也为了呈现对问题重点的不同视角)
,笔者重提一下,系列全文第一章,提出的一组区分:作为存在类比的形式主义,和作为系统癖的形式主义;两者在实操中,往往互相渗透,但概念上,是对立/对称的。
吕岩 绘画 综合材料 200cmx250cm 2019~2020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
之所以在这里谈及吕岩,却主要不是因为艺术家本身(笔者觉得他画得好),而是因为郝强写吕岩的一篇评论,刚好看在郝强和笔者的一次对话之后(聊的是笔者个人创作上的一些问题)。郝强称吕岩的画,是反学院派的,并且是这样一种反学院派:克服了学院学习经历影响,画出了生活体验的绘画。作为对比,郝强批判了一种“概念化”的“反学院派”精神。
前文中的“反对者”观点,自郝强和笔者交流时的说话进一步推衍开去,但并非完全等同于他的观点。
点击:
郝强论吕岩的评论文章
5.2“中间状态”
“中间状态”,既是指“概念化”的“反学院派”,和感性肉身真实的“脱学院派”之间;也是指属类比的“形式”,和属系统的“形式”之间。听上去,
“中间状态”
像一种折衷
(事实上也是)
;但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偏风骤雨、狂飙突进且败北之后,达到的残心状态。
刘川 伐木工人 布面油画 145x95cm 2023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
刘川的画作,在叙事性和反叙事性之间,有明确意图的笔法(形式)和去意图性的笔法之间。
像贾科梅蒂那样,不打稿、直接起形,事后觉得起错的形体勾勒、也不抹掉,保留作一种痕迹(变成多个复数的形象),而这种痕迹是否是一种过程心迹,而这种心迹又是否因为绘画过程中情绪饱满稳定、于是合乎画面呈现的感受整体性——诸如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自觉的,但又没有形成过于理智的反思、从而跳脱出去,变成“概念”的。
关于刘川的一 篇评论
:
俗话说得好——抒情很具体,叙事很抽象
实际上,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种“中间状态”,不论是褒义上的、或贬义上的。
当你画上一笔的时候,你的习性,未必不是学来的,只是在过程中,染上了你的颜色;当你自发地画上一笔的时候,原本是你情绪饱满时自得的笔法,但时过镜迁,成了你自己的套路,然后你会看到,你自创度较高的套路,失去情感内核后,很快就变得,和别人从哪里学来的套路,也并无不同。而你为了破解自我惯性而破之的结果,有多少是渗透了破格情绪的“晚期风格”,多少是原来还有你所学围囿中的算法内部自破性?
直到最后,一个艺术家,究竟是激进的,还是中庸修持的,或者以不断中和化作为自己激进的方式
的,也许并不绝对地决定了作品的样貌;艺品和才性一样,做不得定下最终呈现之作好坏的充分终审标准。还得有第三项:机运——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词。“真诚”真的不是全部。
请允许笔者,借着描述他人的艺术形式论理念,掺杂带出自己私货的生发谱系。
如前
(延后发布的第三大章中)
所述,在学院中,一些和架上绘画有一些距离的院系,对和架上绘画有关的教学传统中,出现了一些,来自学院内部的,以画“错”/“坏”、做“错”/“坏”,发展成绘画形式语言的新传统。这些“坏”,显然又是最典型的“反学院派”的。我们举在版画专业出现的一些倾向为例。
和经典的“坏画”对于“坏”的范式叙述不同,版画专业出身的“坏”,恐怕和工序步骤/分层的繁琐,而造成的容错性有关。很大程度上,这种“坏”,可能只是一种更易于构筑画面张力/强度的自由。对油画专业思维出身的而言,“拗”与“拗救”,是横向的、直观的,更因难见巧的;而对版画专业思维转型之后的架上绘画
(以及其他)
而言,困难的横向关系可以被容易的纵向关系,轻易补足,“坏”其实可以没那么难:结果就是反过来,“坏”可以“坏”得更凶、更刁钻困难了。
最直观的宣言,是王华祥的“将错就错”;但笔者对之了解不深,只大概知其版画语境中的“错”为何,不知其将之转移到架上绘画时,是如何实施的。笔者相对比较了解,并一时能想起的有:李昶的论文,将
英美文学
形式主义
新批评中的“非诗因素入诗”法,借鉴进与画的形式论对观
中
(和笔者写过的“江西派诗法入绘画论”颇似,并比笔者早,但笔者写那的时候,不了解她这)
;能尖日以学院式的研究方法,归纳总结,并用到自己作品中的“素人艺术”研究;许宏翔的以版画制造中常见失误,挪用到绘画上作为作画手法的“错图”;劳大伦从“LOD美学”中归出来的、建模低线数造成的“锯齿”风格的纸上画……说那么多,无非是想最后借机端上笔者的私货
(看!笔者个人创作“走火入魔”的“错”法,不是孤立的,可以拉出一条“疯狂”的谱系的!)
:笔者受过的指导是
(不是笔者导师,是蹭谭平老师的课)
,
“保留画面中不合理的东西,并找出一种方法/中介装置,使之合理化/立得住”。笔者古怪的绘画理念,并非拍脑门、从私人感觉和书本理论出发而纯自发,有一定学习根据,尽管受个人性格等影响,将之极度激化。
事实上,这也昭示了,笔者在艺术理论和艺术评论上的“叛逆”倾向,还是有一个个人实践背景的影响的,
也就是脑袋还是受屁股影响,
在理论上是不纯粹的,以及,居然有“好学生”的错误倾向的
(明明本身
特叛逆,都
是半个野路子了;没有办法,爱极端的人,学习了“保守”派精神后,会把“迂腐”当作一种激进的方式)
。
形式语言中,物质施行过程中的局限,也就是短板,会构成一种形式语言/风格的边界、阈限;不是围绕着一种材料性的长板,而是围绕短板,进而形成一套,由少量表达式的组合叠加,转译大量语义指涉的表达体系。“局限性演为形式语言”,风格的形成,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从结构主义理论,和真实的美术史上,都有一些依据,之后有机会聊起,这里不赘述。
但把局限性放大,彰显其作为“错误”的一面,甚至不会犯错却硬要模仿别人犯错时的面貌,再以刁钻、因难见巧的中介装置,让“错误”在画面整体关系中体现为非“错”——其实还很少出现在美术的形式论中,但在文学的形式论、甚乃音乐的形式论中,都很平常;但在“坏画”的实践中,出现的,脱离“坏”的原初理念,以“坏”建构新的“合理性”的实践中,却很常见——且不论这样的“坏”法,是否违背“坏画”的初衷。
以“错/破”为系统建构的语言,以随时“反体系化”的手法搞“体系化”,随搭随拆,如果是自洽的,只能说,是和心迹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有着对应表征关系。语言之“错”,和心境之“错”,与其说,是靠是想象力的主观能动性的移情能力,以得以两者相融,不如说,是人身在各式社会系统间,产生的
错位感,和形式语言系统的错位感,天然地、无须自主地、发生着对应的移情。和系统的不断对抗的命运,成为时代的表征,其前提是,人将自己和系统的关系,予以了某种不情愿的“认同”。因此,系统癖的痼疾,支持了一种古怪的“反系统”/“反学院派”的作法。
许宏翔 众神的植物NO.2 180×250cm 布面丙烯、油彩 2022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
许宏翔的“错”画,是将版画中的“错”(失误所造成的视觉),挪作布面作品上的形式风格,其实无所谓“错”。但,在他的主体而言,是一种克制在限度以内的,自我主张的自由。这和他,为了能一次性短时间即时完成某个局部,以不惜做大量铺垫/补救工作的创作方式,相对应。“困难的自由”、“局部的自由”,是一种自我选择。
一篇关于许宏翔的评论:
“错图”,对画;或许可以更“错”?
能尖日 photograph龟纸本水彩 聚苯乙烯,毛绒,树脂 127 x 59cm 2018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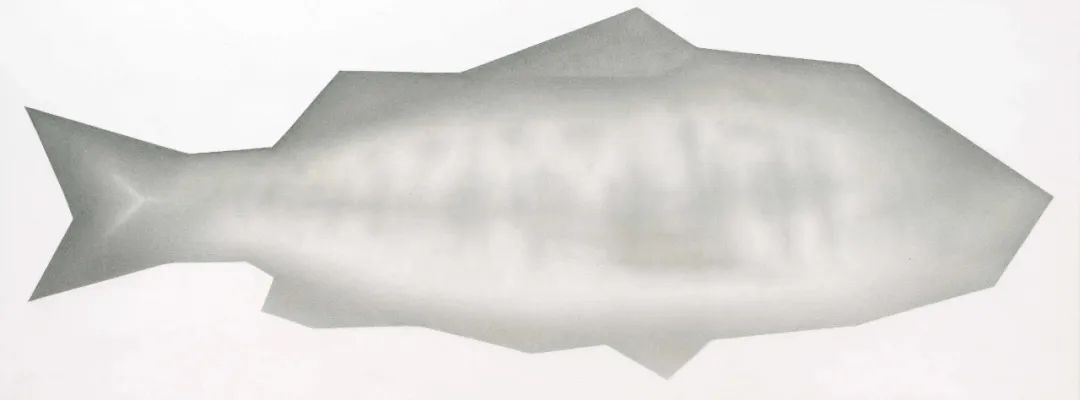
劳大伦 鲈鱼 8.5x22.5cm 纸本石墨 2016
图片未经用于本文的授权
3D建模的视觉,是一种特别当下、所以也被认为属于当代/后现代的视觉,但劳大伦“媒介考古”后
(林梓、雷鸣用语)
的视觉迷恋,进而挪作同构性的绘画形式语言的“诞生
(从底层进行体系建构)
”,却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趋向。他的“锯齿”、“简陋”、“错”,有着双重发生动机。在指涉“现实(屏幕时代视觉体验)”和形式语言系统建构之间。
一篇关于劳大伦的评论:
“劳大伦的LOD美学”是一种完全的新世代美学吗?
总结:
毫无疑问,笔者的全文关系有点乱糟糟的,因为围绕一个名词展开的,是周边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意识。而且在必要的尖锐和必要的温和之间反复横跳,虽然不失立场一贯性
(一贯的心态暧昧,非左非右)
,但在修辞间充满了疲惫。
最后,还是说几句冠冕堂皇,正能量的鸡血话结尾吧。
在一个充满价值断裂、争议,现实矛盾的历史语境里,撕裂虚假“共识”的艺术,才是最真诚的艺术。
“学院派”之所以没有沦为一个纯贬义词,是因为从“学院”意识而来的许多人,保持了正面意义上的学院/系统化/形式思维,和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法、极度过不去,又在“保守”所学传统的愿景基础上,追溯“传统”的脉络由来,开发“旧”基础里的“新”可能——作为一个温和的、在做“好人”和做“正直的人”之间摇摆挣扎的人,脑袋决定屁股——哪怕知道,这是一个非原装的、半被驯化的脑袋。
也许,有时候艺术家的品味和手法是同一的,但在讲求“进步/创新”的语境里是有害的;
有时候,艺术家
本身,是复合多样地被塑造的,和艺术良心最舒适的表达状态,是对立的,无法主动地体现人格的,但却亦体现某些价值的;对固化系统的反对方式,一半来自系统本身的变形状态,一半是急切的情感表达意图,而最终,真情亦被自我驯化了;这创作动机的复合意识,并且是自觉的复合意识,最有可能,是学院的痕迹、曲折迂回造成的,尽管在字面上、常识的话语里,这种反而一般不会被称为“学院派”。
一封“远方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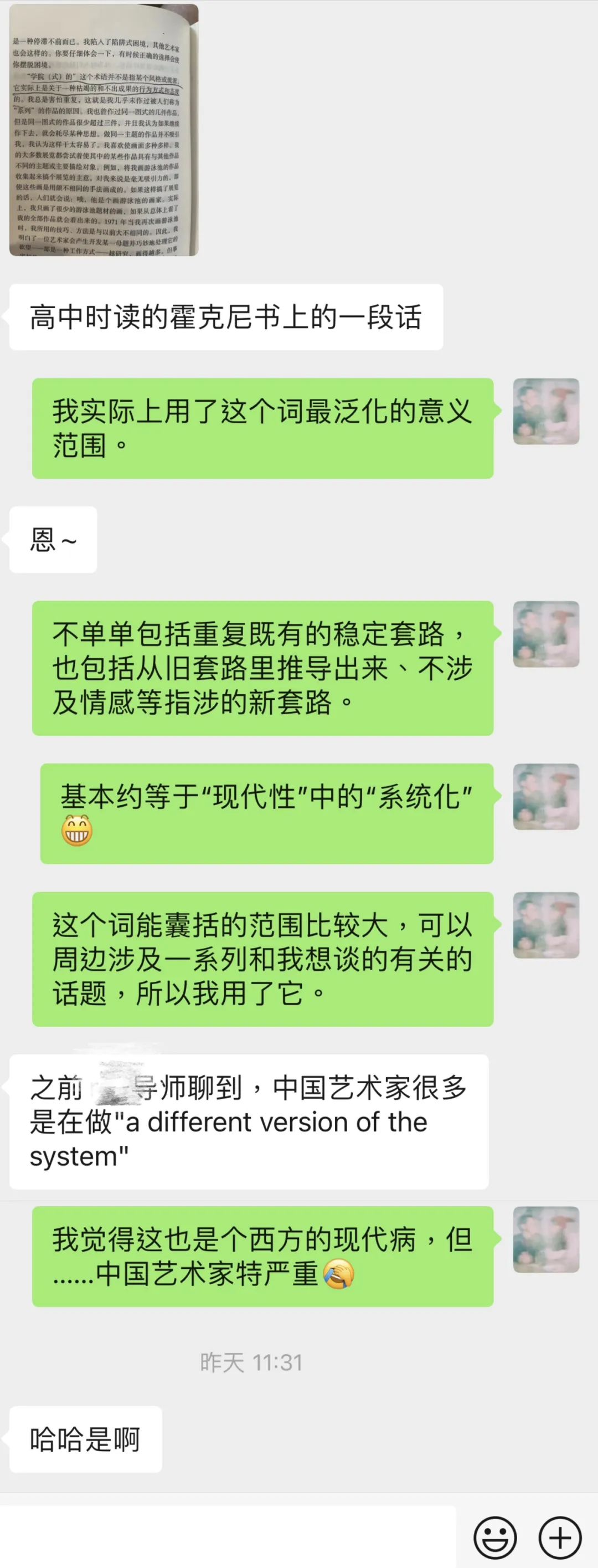
一位朋友看到了前几期推送,专程
发信息来
和笔者交流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