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1 年至 2014 年,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四部情节相连的小说,被合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故事描述了两个出生在那不勒斯一个贫穷社区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和战争,并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笔触深入而彻底地展露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今年,前两部小说《我的天才女友》和《新名字的故事》中译本问世。
在今天推介的文章中,单读主编吴琦解读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形式与结构之美,第二部书中故事的新发展,作者突破性别命题困境与当代阅读习惯的精妙尝试,以及最重要的,那种追求改变浪漫本质。
以下文章转载自《北青艺评》

变化本质上都是浪漫的
吴琦
当电影、连续剧成为主要的故事来源,长篇小说已经越来越珍稀了。尽管创作者仍然挤在这条攀爬文学高峰的路上,观众的座位悄然发生了位移。正因如此,《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的流行,本身成了一个浪漫故事。连载、四卷本、匿名写作,一段古典爱情的样本,像看多了欲望速朽的情节之后,又遇到几个顽固的跑马拉松的人。这个时候,我宁愿相信,谈不上进步或者残忍,变化就只是变化而已。
真正的变化从来不在于形式,任何进化成功的形式,本质上都修改了内容。连载小说的创作与阅读在今天之所以显得特别,不仅因为时间上的长度和跨度,更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具有现代生活通常所匮乏的气质——那种不断拓展的认知纵深,流动的阅读体验。这种阅读的“流动性”是在所谓“流动的现代性”中日渐丧失的,当生活被加速、被切碎、被填充、被替换,人并不必然变得开放,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加依赖定见,或者用流行一点的说法——依赖执念,再政治一点——依赖刻板印象,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

在《四部曲》这个案例中,拉开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成为打破这些东西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连载也因此不仅作为形式,也成为它的内容——不断修正和自我修正,新的一部总与前一部有所不同。而它的逻辑显然又不同于那些根据观众反响、演员档期而随时调整的电视剧。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中文版的问世,让中文读者真正得以参与这个过程,我们几乎与其他语种的读者同时看到,在第一部中展露的两位女性及其所在街区的故事,如何升级、变幻,和其他复杂问题缠绕在一起。
小说多是后见之明,《四部曲》一开始就主动暴露了这一点。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在于叙事者埃莱娜进入老年,她同时意外得到了好友莉拉用来记录自我的笔记本,从而掌握了叙事的权力和能力。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故事将不复存在,顶多成为一个人的意识之流,或片面之词。这是整部小说最大的魅力,随着情节的推进,两位女主人公的情绪与智慧,彼此矛盾、补充、印证,推波助澜,构成一种文学上的校准,不断调试语言的刻度,迫近属于、也只属于她们的心理时间。
这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光辉时刻,以这样完整、细密、自觉的程度,展现一个性别的困境与可能,尤其在现代,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奢侈。但它同时可能造成障碍,对男性读者而言,一种可以想见的逆反或者漠然,也就是难以撼动的定见之一——你们可想得真多,我为什么要像你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你?更有趣的是,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如何调整自己的观看位置,变得更加暧昧不清。这可能构成一个困境,迅速为《我的天才女友》确立女性故事、女性气质这个基调,很容易和其他性别讨论一样,以同样的速度遭遇接收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第二部带来了更多路径、新的消息。第一部提及的“庶民的世界”,被更广泛地展开,作者引导、至少暗示了读者,可以不时从单一命题中抽离,让这个庞大的故事在其他维度上得以呼吸。

应该注意到,小说中对于女性角色饱满的同情心和惊人的坦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物,其他的男性或女性或多或少都被客体化了,成为这两位闪光的女性人物的衬托、环境和画外音。这不是批评,而是叙事技术中必然的平衡。主人公自己也说,“我对男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也不懂”,即便是给二人命运带来关键转折的、目前对她们最具吸引力的男性角色尼诺,也“只是一个工具”。尽管如此,所有的女性都在寻求与男性关系的调整与安置。而尼诺、加利亚尼老师的儿子、以及埃莱娜后来两任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友,在第二部中轮番出场,帕斯卡莱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们用非常明确的雄性语言,发表对于如何改变世界的看法,并且走向职业和社会行动的转变,甚至在结尾处,埃莱娜在新书发布会上被发表意见的男性包围,尼诺再次出现……革命应该通过计划还是暴力?殖民主义、饥饿和战争可能被战胜吗?男性角色不断抛出类似的问题,但不能妥善地回答,让这部分叙事也更像是一种技术,同时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社会情势、历史潮流的敏锐,在结构上与女性的呼喊形成对应。
也是在第二部中,两位女性童年的贫穷——物质、精神以及超越这两者的文学上的贫穷,越来越浮出地表,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成功出版第一本书的埃莱娜反而迷失在语言的沼泽里,在那不勒斯方言和比萨口音中无所适从,对自己的文章和莉拉的笔记本都产生了怀疑,在更明确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前丧失自信。她开始质疑语言的可靠程度,认为那不过是“对逝去时光的艰难衡量”。这种指控构成了对这本小说的自指和自反,进入了对小说元命题的探讨,同时也是对这条二人曾经共同追求的道路的否定,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既是女性的命运、也是底层的命运)的努力,在不同的人生试验和突围中,均宣告失败。最终,任性的莉拉逃出家庭,进入工厂,被现实摧毁,性别与阶级彻底同构,小说的触角抵达深处。

故事被推向又一个西西弗斯的困境。跨越性别的理解,标示出我们与他者沟通的能力,挑战既定的性别秩序,也代表着文明更新的难度,更致命的是,当两者相遇,并不能互相抵消,也难以互相借力,让人想起历史上女性和阶级运动坎坷的合作记录。女性的渴望(以及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温柔世界)和男性的决心(在男权社会权力关系主导下对乌托邦的设想),同样是难以实现的。这和许多使用全知视角的古典文学作品,再次达成共识,而《四部曲》并不是通过全知视角来实现这一目的——形式上的更新,并未阻断思想上的共鸣。
第二部带来的这一点观察,在随后的阅读中仍可能被推翻,那将是追随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最大的乐趣。因为就如同埃莱娜和莉拉对于一个女性应该怎样体面生存的设想,如同主要由男性起草的诸多社会宣言对平等、正义的主张,如同一切人类追求完美原型的冲动——冒险、出走、疯癫、革命……变化本质上都是浪漫,尽管它可能不解决任何问题。而在这层层束缚的情势下,仍然谋求改变,是这部小说目前展现出的,最大的雄心。

编辑 | 关关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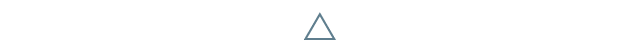

识别图中二维码,预购正在印刷中的《单读 14 ·世界的水手》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抢先预订正在印刷中的最新一期《单读》,成为与我们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