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很多女权主义者按照性别将自原始时代末期以来的社会称为男权社会,认为社会中存在也仅仅存在着男性对于女性的单方面压迫,进而将压迫的问题简单地以性别两分,并将“父权”与“男权”完全等同。这种简单的性别二分法,让人们认为女性所遭受的所有压迫,完全是作为男性整体乃至于所有男性所施加的,男性之间似乎并没有相互之间的压迫。但事实却并非是如此。
历史来看,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是生产力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财产观念与权力观念也就此产生,并与父子之间的血缘继承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父权社会。此过程中,父亲对于妻子、儿女的人身都具有相当的占有权力。
而对于男权制的定义,李银河认为:“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看,父权制与男权制完全重叠,应当可以通假,视为同义词”,“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男性中心的,这个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压迫女性”。

观之而言,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问:一、是否身为男性,就已经天然地享有对于女性的统治权力;二、是否身为女性,在此系统下就天然地受到压迫;三、男性之间是否不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现象。
事实上,这种对于男权的定义和对父权与男权的混淆出现了极大的错误。
刘思谦在《关于母系制与父权制》中曾经指出上述言论的两大破绽:
其一是把男性和女性都看做是无差别的统一的“族群”,
遮蔽了男性和女性这一性别身份中包含着不同的阶级、种族、社团等身份;遮蔽了这中间错综复杂的变化和张力。二是与此相联系的将“父权”等同于“男权”,等同于男性之无差别的“男权统治”,遮蔽了男性与男性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遮蔽了父权制的统治既包括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也包括男人对男人的统治或少数男人对多数男人的统治。
实际上,压迫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群体而言,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都面临着一定的压迫与统治。简单地将父权与男权等同来简化问题,对于解决问题并无任何用处。父权是自私有制产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建构,它不仅仅包含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别压迫,也包含了以阶级、等级秩序为逻辑的非性别压迫。如《十二铜表法》规定,“家父”对于“家子”有抛弃、审判、出让的权力,而“家子”对于“家父”则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在父系氏族形成的过程中,族长与家长掌握着财产与统治权力,形成氏族共财制,族长或家长掌握着大部分成员的生产资料,并压迫着氏族其余成员。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宗法制度进一步包含着阶级压迫的性质,进而成为奴隶制国家用以统治人民、维护阶级秩序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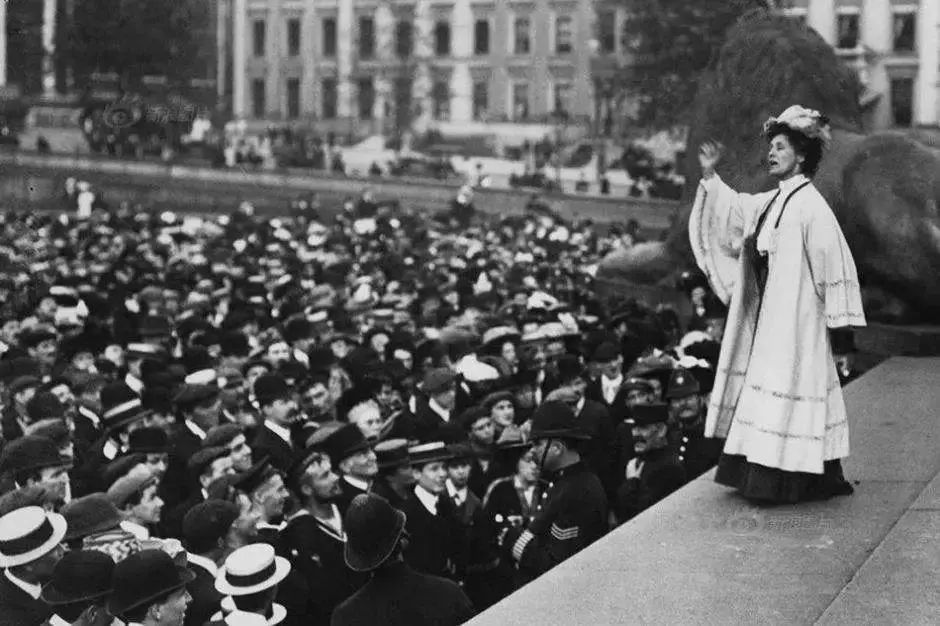
当然,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由于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是为数众多而又分散的家庭,交易对象过多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难以对其进行管理,因此将一部分权力下放至氏族、家庭,甚至以法律的形式协助其建构宗法秩序,试图以较低的制度成本完成对于基层的管理。
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宗法制度开始过渡到以个体家长制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这种封建宗法制度,同时强调着家长权的强制性与剥削性。家长对于血缘亲属及存在人身依附的非血缘者,拥有着极强的人身权力,并凭借这种权力迫使其服从。
宇培峰在分析中国家长制时曾指出:“进入封建社会后,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使得宗法制度的直接政治作用大为削弱。但是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如君权与族权的结合、家长、族长的法定特权,嫡长子继承制,尊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完全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统治者从长期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父权、族权的特殊作用,因而力图把巩固封建国家的任务,落实到社会的细胞组织——家庭。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家长权与族权,积极构建伦理法的体系,丰富伦理法的内容。中国封建法律确认和维护父权和族权,又使得家长权、族权法律化。中国封建家长制家庭的长期延续,法律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法律的规定,伦理和政治进一步结合,家和国
进一步沟通,家长制家庭俨然成为一个主权单位,父权和族权是专制王权的缩影,而家长既是家族内的立法者又是裁判者,他们拥有统治家内成员的广泛权利,同时也对国家承担着应尽的义务。”

封建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以法律及思想确立了宗法制的统治地位:若将基层管理的责任与义务交予氏族或家庭的族长、家长,无疑可以大大减少交易对象、交易费用与制度成本。
宗法制度与封建制度的结合,将封建宗法秩序从单纯的氏族扩张到氏族之外,家长或族长对于佃农、学徒、门生都有了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上的权力。封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节约制度成本的指导思想之下的一种基层管理制度。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并进一步促进上层建筑的转变。信息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成本缩小,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推进基层管理的制度收益增加,也同样是关键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这种转变,最开始体现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之转变上。由于封建宗法秩序往往建立在人身依附之上,而资本主义雇佣制打破了生产关系中的人身依附,使得原本生产关系中凭借着人身依附对于佃农、学徒等的剥削,开始转化为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女性社会生产参与率的提高,又使得家庭中妻子对于丈夫的人身依附关系,伴随着女性大规模参与社会生产并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而转变为相对平等的关系。
由于生产的大规模机械化,男性与女性所提供的劳动至少在低端制造业中大体是同质的,但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并不如男性一般,能够为资本家提供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资本的逐利性与生产力的局限性,并未能克服这种生理原因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剥削女性劳动者远不如剥削男性劳动者来得好。
综上而言,资产阶级在夫妻关系上,也依然对封建宗法制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妻子不再是丈夫单纯的“私有品”,西方所宣言的“自由与平等”终于在经济基础去人身依附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尽管如此,子女对父母依然存在着依附性。对于子女而言,这种依附关系开始普遍地从单纯的男性家长扩张为男性及女性家长,并使得子女依然如同父母的所有物一般受到压迫。
由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及法律上层建筑中,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往往是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也操持于家长手中,故而衍生出了中世纪以来所谓的“家长私有制”,并固化于上层建筑之中。在封建宗法制下,甚至于父母的同辈兄弟姐妹,在保持家长权威的指导思想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迫使晚辈服从的权力。
这种代际的不平等,正如以往妻子遭受丈夫压迫时一般,源于经济地位的不独立所形成的对于父母的人身依附,甚至在封建宗法制度指导下延续至子女成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