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米兰达共和国大使法拉尔·科斯塔先生,被布努埃尔看成了典型的“布尔乔亚”。他的手从长条餐桌底下伸出来,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胡乱摸着,他想尝一尝女主人精心烹制的烤小羊腿。
但在慌乱中,他只抓住了一片火腿,结果被恐怖分子发现。他们掀开了桌子,看见了龟缩在餐桌下狼狈不堪的共和国大使科斯塔,他大难临头,却不顾一切地吃起火腿来。
这个梦是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 1972)的最后一个梦,这个梦让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幽默感、创造力和讽刺达到了巅峰,并给这场布尔乔亚“不可能完成的宴会”画上了句号:法拉尔·科斯塔先生被噩梦惊醒,他穿上了睡衣,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片火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
1
这部杰作通常被译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原名中的“bourgeoisie”翻译为“资产阶级”不是非常妥当,其直译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准确地讲不是中文所说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e),也不是“中产阶级”(classe moyenne),似乎保留“布尔乔亚”这个音译更准确、更有时代感、也更幽默。
比起“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布尔乔亚”在欧洲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就算在今天,在中国说“布尔乔亚”和在法国说“bourgeoisie”仍是两个意思。

中世纪时欧洲出现了最早的“布尔乔亚”,指那些生活在欧洲小镇里的居民。欧洲大陆最早的城镇叫“bourg”,来自古拉丁语“burgus”,其居民就叫“布尔乔亚”(bourgeois)。
从十三世纪起,小镇居民中的一些人用钱物向封建领主购买一定的特权,并让小镇独立。独立的城镇开始颁布一些“宪章”,并在宪章里规定,部分居民在政治和税收上享有特权,比如图卢兹最早的“市政代表”(élus)或波尔多的“执政官”(consuls)等,这些人对城镇具有真正的主宰权,比如有组建和动用武力的权利(经常是由法兰克弓箭手组成的城镇自卫队)。
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乔亚”成为与普通城镇居民有区别的特定人群。也就是说,从词源角度看,“布尔乔亚”的特别之处来自于城市化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运动给“布尔乔亚”附加了非常光彩的含义。“布尔乔亚”开始包括那些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是“布尔乔亚”们带来了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狄德罗、伏尔泰等都是光荣的“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有了新式知识分子的含义。
慢慢地,欧洲开始出现除了教会、王室贵族阶层之外的新特权阶层——工厂主和新贵族,很多新贵族的贵族身份是用钱买到的,这些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被列为三个阶层中的“中间阶层”(la classemoyenne),就是我们今天大谈特谈的“中产阶级”。

它的出现意味着在封建社会权力的两极(教会与皇室、老百姓)之间产了一个阶层,“中间阶层”加入到“布尔乔亚”中,刷新了这个词的含义,于是“布尔乔亚”们脱下新贵族的长袍,又穿上了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外套。“中间阶层”直接领导了法国大革命,尽管一些特权随着革命被剥夺了,但布尔乔亚们又有了“新特权”:对工厂和机器的占有。
“资本”(capital)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真正被人们广泛使用是在十八世纪,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资本家”(capitaliste)这个称呼似乎成为对人格、道德都含有贬义的险恶词眼。
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几乎没人愿意自称“capitaliste”。作为一种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现实,“资产阶级”一直在扩张,但在扩张中,“资产阶级”的命名却在逐渐消失。

就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在从现实到表面的过渡中、从经济到心理过渡中,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不要被命名的社会阶级”,于是“布尔乔亚”顺理成章地成为“资产阶级”的“替代品”。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情感含义定型之后,“布尔乔亚”开始变得“暧昧”。在今天,它同时拥有城市、特权、先进思想、革命性和财富等复杂含义,“布尔乔亚”变得越来越迷人。
复述“布尔乔亚”的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欧洲电影中的“布尔乔亚喜剧”,这种喜剧让“笑”和“讽刺”有了明确的“阶层意识”。如果追溯到中世纪的民间小说,那“布尔乔亚喜剧”几乎可以成为一个不可抹灭的喜剧类型。

在1960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中,“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索邦大学正门左侧贴的是萨特像,右侧就是毛泽东。这样的时代气氛下,1970年代的欧洲喜剧毫不留情地拿“布尔乔亚”开刀。
我没做细致的统计,但直接以“布尔乔亚”命名的讽刺喜剧片以及同类主题的讽刺电影多集中在这个时期,“布尔乔亚”这个词的情感含义再次跌到历史低谷,在这场“反布尔乔亚运动”中,标志性电影就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2
路易斯·布努埃尔在1929年以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Un chien andalou)闻名。有人主动替他解释:《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完美地把超现实主义运用到讽刺题材中,他用了梦,用了弗洛伊德,而事实是与他的其他电影相比,《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被绝大多数观众接受了,人们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惊人地一致,成为布努埃尔影片中最上座的一部。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入围了当年的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布努埃尔在接受墨西哥记者采访时,自信地说:“《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一定获奖!”消息见报后好莱坞一片哗然,这么重要的奖项怎么可能内定?其实布努埃尔这么说,只是一种对好莱坞的嘲讽,他认为影片根本没有获得最佳外语片的可能。
该片的制片人是塞尔日·西尔伯曼(Serge Silberman),这位传奇制片人是布努埃尔晚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看完报纸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打电话质问布努埃尔:为什么要这么说?布努埃尔说:“你放心,美国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一定信守承诺。”1973年3月,奥斯卡小金人真的给了《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美国人果然兑现了布努埃尔所说的“诺言”,这个“诺言”到底是什么?

影片的海报用了格外时尚的拼贴画风格,表达了布努埃尔在电影中尝试的一种努力,海报有点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利特的风格——上面是一个礼帽,中间是两片肥大红润的嘴唇,下面是女人的腿。
在电影中,类似于拼贴的强制手法给布努埃尔提供了非常大胆的自由,他用一些杂乱的、无序的事件给法拉尔们修建了一座“意象城堡”。在一场又一场失败的宴会之间,强制介入了宗教世俗化、独裁政治、虚假外交、以权贩毒、革命幼稚病、恐怖主义和警察等故事,构筑了细节丰富、立体的“布尔乔亚城堡”,这比单纯表达一种阶级幽默感更刺激。
好比吸血鬼德拉古拉的城堡,它源自中世纪罗马尼亚的哥特式建筑,但却只能存在于那些作家和导演的脑海中,如果他们要刻画德拉古拉伯爵,就一定要描绘他神秘的壮观的城堡,让每个角度——无论多么阴暗、潮湿、腐朽和颓废,都映衬着德拉古拉的邪恶光辉。

布努埃尔在电影中的创作自由是无法比拟的。当他需要性的时候,就突然有了偷情;当他需要政治,就出现了女游击队员;当他需要梦,一个炮兵上尉就跑出来给布尔乔亚们讲梦。既然是梦,就弗洛伊德一点,干脆就讲“弑父”;当他不想布道的时候,女游击队员引用的毛泽东名言就被噪音淹没了。
就像法拉尔在剧中的一句台词:“毛泽东没读过弗洛伊德”,布努埃尔不断插入的题目,彼此之间就好比“毛泽东与弗洛伊德”那样相互屏蔽。一些左派影评人曾对布努埃尔在这部影片中对待革命的态度感到遗憾,这种带有时代色彩的一厢情愿歪曲了布努埃尔的良苦用心。

他把围绕在主人公周围发生的任何有关宗教、本能、精神分析、革命理论都取消了意义,他们的意义就在于构建布尔乔亚的城堡,而这个空间是无序的、不均匀的,呈现出可笑而荒诞的面貌,这种愿望超过了一切。
3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故事挺简单,六个中产阶级和一个主教一次又一次地聚在一起,想好好地吃顿饭,但宴会始终无法顺利进行,一直维持在“开胃酒”的环节,不断被各种事情打断,“正餐”从未开始。宴会不成功,他们又做起噩梦,梦里的宴会情况更糟,不仅宴会被打断,还经常发生恐怖事件。最后,大使法拉尔做了个梦,在梦中他终于“吃”到了火腿。

一直困扰法拉尔们的难题不是“吃”,而是“没吃好”,“欲吃而不达”。“吃”这个动作太原始了,人生下来就会吃,动机是那么简单而明确:让饥饿感获得满足。好比影片中的一段对话,女主人艾利斯问她的宾客:我们是先喝开胃酒,还是直接上桌吃饭?那个矮个子布尔乔亚说:还是直接吃饭吧,我太饿了。
“吃”不但是本能行为,也构成了这个布尔乔亚故事的物质惯性。在饥饿状态中,吃的形式和内容完全可以忽略,关键是女主人的提问方式,这表现出典型的布尔乔亚式谨慎:吃需要程序、礼节和仪式,吃于是变成了宴会。

装甲部队军官请几位布尔乔亚到他家里赴宴,他对法拉尔的国家进行了痛快的批评。在他心中,批评这个大使的愿望要比吃饭更强烈。这时,“吃”变得次要了,“宴会”变成一种形式,宴会者的社会地位和态度变得比吃更重要。
因而在这场戏中,布努埃尔不仅想表达对极权国家的嘲讽,更想表达这种嘲讽本身的布尔乔亚化,后者同样被布努埃尔所嘲讽。
法拉尔、亨利等人的世界观永远是不均衡的,他们很难在食物之外找到更投机的共同话题,所以他们的谈话总是装腔作势,莫衷一是,在反反复复的聚宴过程中,健忘、性冲动、食欲、梦和自我保护经常扮演搅局的角色。“布尔乔亚的宴会”看上去是围绕着“吃”,实际上是围绕着那些悬浮在宴会周围的一些必须进行、又无法真正展开的无关交谈。

影片的布局也是如此,看上去要讲关于布尔乔亚的宴会,实际上讲述的事悬浮在周围的无关事件,布尔乔亚阶层所积累的特权、先进性和财富特征都在这种不均衡中消失了,布努埃尔用完美的形式给事件提供了本质:逻辑上缺乏平衡的、彼此毫无联系的故事与布尔乔亚宴会上虚伪的和谐。
我们看到了布尔乔亚在风波中的不安,这令人发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新的中产阶级最容易暴露出现代人对自己的陌生感,他们在秩序和仪式中寻找被物质世界占有后的平衡。

所以,与其说剧中那几个画面是布尔乔亚在旷野上行走,不如说是在寻找平衡。这种“失衡”也是布努埃尔在电影中设下的咒语:我们只有认定自己不是布尔乔亚,才会觉得影片好笑;可我们也像剧中的布尔乔亚一样不能如愿,随时面临着突然插入的情节。
看这部电影于是也像赴布努埃尔摆下的“宴会”,我们成了座上宾,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中断而渐渐失去平衡,不断实现这个“咒语”,兑现布努埃尔所说的那个“诺言”。布努埃尔的绝妙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电影也像我们与世界之间没有完成的约会。
4
布努埃尔在回忆录里否认《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表达了某种阶级性,“写这个剧本时,从未想过要用‘布尔乔亚’这个词”。他在1970年代的最后三部电影没有把枪口对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而是那些单纯的有钱人和有权人。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用“梦中梦”的形式描写“吃不好的饭局”,到了《自由的幻影》(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 1974),则成为“戏连戏”的布尔乔亚小道新闻,嘲讽的对象仍然是上层社会、教士、官僚、警察局长、大学教授和商人。在《欲望的隐晦目的》(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 1977)中,他又把焦点放在一个中产阶级对一个性感女孩无法实现的的占有欲上。
也许,正像布努埃尔自己说的那样,“布尔乔亚”这个词的出现改变了他只想描述荒诞场景的初衷,同时这个词也让他为这种荒诞找到了最恰当的“身体”。
提到“资产阶级”,立即让人联想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对机器、工厂和劳动力的占有。而当我们提到“布尔乔亚”,则使人想到这个阶层的风俗和情调。“布尔乔亚”是个令人尴尬、恶心但让人荣耀的身份,一种自由选择消费活动所能带来的各种情调的生活趣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布努埃尔瞄准的是作为“阶级”的“布尔乔亚”,还不如说是作为“情调”的“布尔乔亚”。所以没有工厂,没有生产活动,没有社会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布努埃尔的镜头里只有布尔乔亚们“欲求而不达”的荒诞。这些人不断做梦,不断回忆,形式不停地转换,讲述那些有头没尾、没头没尾的故事,其效果是让事物的不均衡、时间的不连续和感觉的不确切浮出水面。
布尔乔亚们慌了,我们也慌了。布努埃尔对偶然性与内在不安的这个发现非常精彩,它割开了现代社会的表皮,暴露人们极不均衡的虚假本质。当布努埃尔想给这个本质找一个“身体”并显现出其荒诞可笑时,“布尔乔亚”是不容置疑且独一无二的选择。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出现了许多奇怪而不可完成的宴会,在《自由的幻影》中也有一场精彩的“宴会”:教授带着夫人到一位朋友家做客,温文尔雅的女主人把他们引入餐厅,按照传统礼仪安排宾主落座。
那是一个宽敞、光线充足的饭厅,一张豪华而体面的长方形餐桌摆在正中,但大家落座时,女士们却撩起了裙子,先生们脱下了裤子,彬彬有礼地坐在桌子周围的马桶上,并礼貌地攀谈起来。
布努埃尔调换了厕所和餐厅的风俗,马桶作为厕所的本质被套上了餐厅的形式,大家像宴会一样坐在桌子周围如厕,攀谈,讨论着全世界每年制造的小便多得惊人,形成了无与伦比的讽刺。之后,教授冲掉马桶,起身去餐厅吃饭。

而所谓餐厅则变成了封闭的、每次只能进一个人且需要反锁的小单间,就像厕所。影片这段戏讽刺了片中教授所说的“风俗理论”,堪称电影史上最经典的讽刺,令人啼笑皆非,也揭示了人们处在风俗场景下产生的“无意识”竟如此荒谬。
在历史上,布尔乔亚们曾创造了现代社会,他们是城市化、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先锋。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创造了自己的风俗和情调,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话说,恰恰是这种风俗和情调遮蔽了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内在分裂控制的危险形式”。

布努埃尔的讽刺中最好玩、最好笑的,就是这种风俗和情调的毁灭,也摧毁了我们对风俗和情调的好奇与崇拜。在这个基础之上,影片中的任何表达形式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花样:梦、回忆、幻觉和错觉……
梦与回忆是不可还原的,加上心理失衡的叙事方法,让主人公与观众都进入到时间迷失的紊乱状态,电影的形式与内容达成了惊人的和谐,布努埃尔耐心地一块一块地撕开故事表层的豪华壁纸,暴露出斑驳、腐朽、丑陋的墙壁。
5
同样是阶级讽刺剧,同样是荒诞不经的布尔乔亚的宴会题材,马可·费雷里(Marco Ferreri)的《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 1973)则显得格外沉重,他给布尔乔亚这个“阶层神话”的主人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沉重的肉身”,死亡让这场闹剧变得令人愤怒,也充满惆怅。
影片中四个中年男人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作、身份以及财产都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他们是最没理由自杀的人,但他们却在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生活中受到死亡的召唤。

死亡具有真正的平等意义,具有解构布尔乔亚神话的终极意义。人总有一死,一切财富、地位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论人在现实中属于哪个阶层、拥有多少财富和女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肉身的毁灭。因而,死亡是对权势者和资产阶级构成的最大威协与讽刺。在一个平静的周末,四个男人聚在一起,打算享尽人间美食后饕餮而死。
这是一场奢华但丑陋的死亡仪式:一车车美食,一个个身形肥大的女人,他们打算通过充分满足食欲的方式结束生命,把生的本能(吃、性)变成死的仪式,用欲望不断获得满足的生理性高潮,替代死亡瞬间的恐惧与痛苦。这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的死亡迷梦,是依靠财富和权力才能获得的死亡仪式,宛如古代君王奢华的祭祀。

以消化道内爆的方式保全身体外形的完整,也是四个人选择死亡的梦想。我们看到布尔乔亚神话的物质崇拜被还原为身体崇拜,这才是布尔乔亚的秘密:飞机师马切洛对自己性能力的迷恋,菲利普对奶妈身体的依赖,雨果对美食技术的崇拜。
如果说布努埃尔在《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和《自由的幻影》中剖析了布尔乔亚的风俗、情调和社交仪式,那《极乐大餐》则让他们脱掉了这些外衣,还原为身体和本能。他们面对着欲望与死亡,不再有任何阶级的含义,享乐就是单纯的享乐,死亡就是纯粹的死亡。

米歇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向阳台,说着说着便扑倒在栏杆上,放了一个长长的屁之后挣扎断气,“饱食而死”似乎是最美丽的自杀,却散发出刺鼻的腐臭,让我想起《自由的幻影》中那种奇怪的因口吐粪便而死的怪病,那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病,或者说是无法诊断的现代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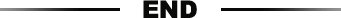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这部电影是九月院线最大的惊喜!只刷两遍恐怕还不够
《权力的游戏》还是代表美剧最高水准的神作?我开始恐惧第八季
深入地谈一谈福特和莱昂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