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花木,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湖风光和翠湖的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痛促进了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力量,因而形成了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文学社团的另一功能是培养人才。学生社团的育才功能尤其突出,新潮社出了杨振声、傅斯年、顾颉刚等而有地位,湖畔诗社因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等而著名,西南联大的学生文学社团亦走出了一批批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成为我们今天仍要关注的对象。
说穆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诗人,不会有异议,说穆旦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培养出来的诗人,恐怕就有人说“不”了。的确,人才的养成需要各方面的条件,教育居其首位,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环境养育了穆旦的诗人素质,再加穆旦的努力追求,才有穆旦的诗名。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西南联大文学环境里的社团成分,再考察穆旦在文学社团里的活动情况,就不会说“不”了。其他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出来的作家亦当作如是观。

穆旦
穆旦是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社的“五朝元老”。他参与发起了这五个社团,并在社团中积极工作,出谋划策、参加活动、努力创作,既得到社团的养育,又丰富了社团的成就,可以毫无悬念地说,穆旦在哪个社团,就是哪个社团的创作旗手和代表诗人。我们可以通过社团梳理出穆旦的诗歌道路。在南湖诗社,他带着“湘黔滇旅行”的豪气,感受到南国天地的空阔宏大,胸中充满豪迈刚劲的情愫,表现在诗歌里,就是一种宽广雄阔的浪漫气息。这时,他的诗友林蒲已经开始用现代主义方法处理题材与情感了,他还沉醉在对春的歌咏、美景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之中。离开蒙自进入高原社,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在他的诗作中,但浪漫主义仍然是他的主调。南荒、冬青社时,现代主义占据主位,把他那种复杂、矛盾、紧张、焦灼、痛楚的内心表达出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诗歌成就,成为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因此,穆旦是在文学社团里探索、发展、成熟的,社团给予他的甚多,创新的氛围、师友的鼓励、发表的园地等都是催生诗人的条件,到文聚社,他已走出了自己的诗歌道路,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之后他没再参加别的社团了。几经风雨灾难,“文革”后他复出,又把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诗风带给诗坛,引起诗坛的震动。
论成才与文学社团的关系,汪曾祺比穆旦更为典型。他是冬青社的首批成员,在社友的鼓励下,一篇篇作品刊登出来,创作动力大增。他初期的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随着课堂所获的增多,他探索各种写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方法并举,无论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呈现多种风格,成为冬青社的优秀作家。汪曾祺参与发起文聚社前后,创作成绩突飞猛进。由于两社并存,这时的作品分不出哪篇属于冬青社,哪篇属于文聚社。由于他很少参加后期冬青社在校园的活动,可以把他离开西南联大前后的作品归为文聚社。这就出现了这样的轨迹:通过冬青社的培育,到文聚社他已经显示出成熟的气象。他的成熟并非《邂逅》时期突然的飞跃,而是在文聚社时期就实现了的。笔者访问西南联大校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著名作家。1946年他返归故里路过香港时,报纸刊登“年青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所以,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培养出来的作家。上世纪70年代末,他把40年代的创作链接起来,捧出《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赢得文学界一片赞誉。
作为冬青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杜运燮付出甚多,收获也很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结识了穆旦及王佐良、杨周翰等一帮现代主义诗人。他没有听过燕卜荪的课,难以走近艾略特,却随诗友靠近了奥登,最终成为西南联大诗人中奥登的第一传人。他当然注重现实内容,但在处理题材时,往往采用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增添了冬青社作品的现代主义成分。他的成名作同时又是代表作是提供文聚社的第一首诗歌《滇缅公路》。这时他已从军而暂时离开西南联大,虽然是文聚社的发起人之一但无法参与文聚社的工作。他带着冬青社的诗歌技艺在“飞虎队”和印缅战场创作了现代文学中特有的作品,其中一些刊登在《文聚》上,履行一个社员的职责。当他毕业离开昆明时,已经是一个著名诗人了。纵观他的创作,他的代表作都是在冬青·文聚社时写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他以朦胧诗重出诗坛,刮起一股现代派诗歌的旋风,开拓了新时期诗歌的发展道路。究其实质,这是他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里的素养之释放。

杜运燮
新诗社的组织与领导者何达,原先是文艺社的诗歌骨干,他拜闻一多为师,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探索朗诵诗的创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新诗社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新诗社的发展就是他的发展。在新诗社之初,他的诗虽然可以朗诵,但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不能贴近大众。新诗社逐步走向朗诵诗创作后,他尽量采用大众语言,自觉创作平易通俗、入耳即懂的诗,在每次诗歌朗诵会上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二·一”运动爆发,他用诗歌发出高亢的呐喊,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使反动派胆颤,还把那段历史“镌刻”在诗歌史上,是今天了解西南联大反内战民主运动的史料。他还把新诗社的诗风带到北平,推动了上世纪4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朗诵诗运动。他是新诗社的创作旗帜,他的诗是新诗社的招牌。他的诗集《我们开会》代表着上世纪40年代朗诵诗的最高成就,是闻一多朗诵诗观念的最佳体现、朱自清朗诵诗理论的有力证据。何达与新诗社紧密相联:假若没有新诗社,就没有何达的朗诵诗成就,而没有何达朗诵诗的成就,就不能说明西南联大朗诵诗运动的巨大功绩,新诗社的文学地位也会降低许多。新中国成立后,何达定居香港,1979年应邀回大陆参加中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以上几位都是成就一种文体,开一代文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方面或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西南联大作家,他们一生的事业都跟文学联系在一起,尽管历史与个人的原因使其创作有过中断,但他们始终从事文学创作,且在不同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文学史不能不写入的作家。
像他们一样或断或续,后来或晚年仍在创作且成绩不菲的作家还有刘北汜、秦泥、于产、巫宁坤、赵瑞蕻、林蒲、叶华、闻山等,他们的主业也许并不是文学,但他们仍坚持业余创作。刘北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人的道路》《山谷》《荒原雨》等作品。秦泥,中国作协会员,发表中篇小说《两对旅伴》、出版诗集《晨歌与晚唱》等。于产,中国作协会员,短篇小说《芙瑞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周公馆》(合作)获第一届蓝盾文学奖。巫宁坤退休后移居美国,创作了许多英文的散文和小说,自传体小说《一滴泪》享誉西方,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著作。赵瑞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译有《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等,出版诗集《梅雨潭的新绿》、散文集《离乱弦歌忆旧游》、著作《诗歌与浪漫主义》等。林蒲是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出版《暗草集》《埋沙集》等,被称为“一位默默地耕耘在诗坛上的爱国诗人”于建一:《我所知道的诗人艾山》,《人物》,1996年第3期。叶华旅居国外,笔耕不辍,有《叶华诗集》出版。闻山,中国作协会员,诗书画俱佳,散文创作颇丰,有《闻山全集》行世。
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有: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中山大学教授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凤仪,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康伣,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袁可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德,河南大学教授李敬亭,美国南方大学教授陈三苏,广西大学教授贺祥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佐良,北京大学教授杨周翰,西南大学教授刘兆吉,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向长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治中,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家程应镠,云南师范大学蒙元史专家方龄贵,扬州师范学院地方史、西南联大史专家张源潜等。
从事与新闻出版相关工作的专家有:商务印书馆郭良夫、文艺研究杂志社林元、羊城晚报社萧荻、收获杂志社萧珊、中国语言杂志社周定一、香港画家李典、新华社刘晶雯、人民中国杂志社秦泥。
还有从事政治工作的王汉斌、彭佩云、马杏垣、田堃、何扬、程法伋、彭国涛、马如瑛、陈盛年、黄平、刘波,甚至还有化学家邹承鲁等。
以上所列仅为一鳞半爪,并非统计结果,而且一个人的工作与单位是变化的,可能有多个,将其固化为某个单位、从事某项工作并不科学。前举各例,是为了说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推出了一大批人才,他们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节选自《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李光荣著,中华书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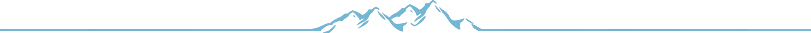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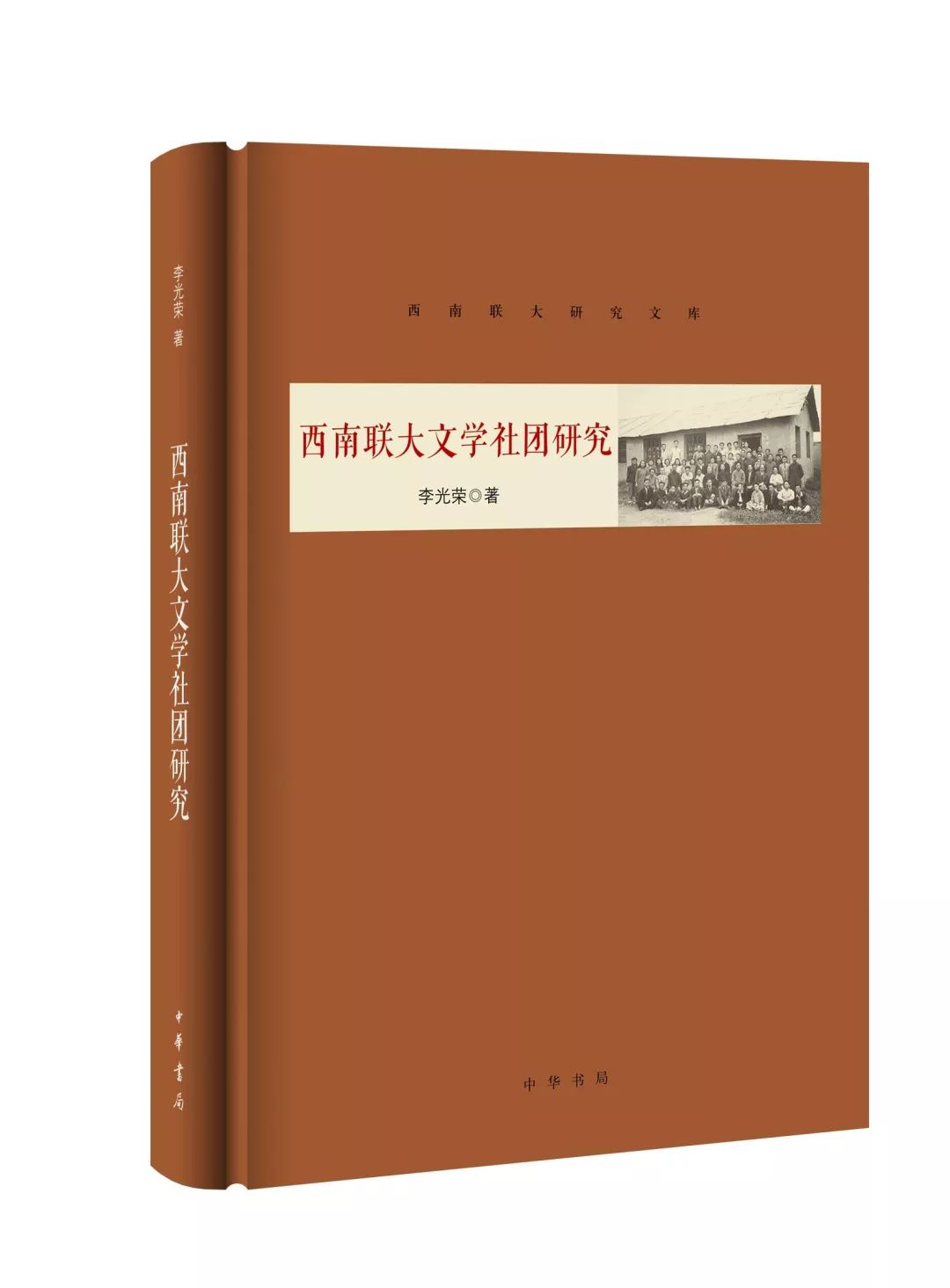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李光荣 著
装帧:16开 精装
书号:9787101134452
定价:128.00元
本书是中华书局2011年版《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一书的增订本,共约40万字,对现代文学史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对西南联大具有代表性的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等重要社团的产生、发展、创作实绩、影响地位等进行史料钩稽和深入探讨,是体现现代文学史、大学教育等领域前沿学术水平的研究专著,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李光荣,云南永胜人。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樊骏先生访学一年。先后任教于红河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次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编著有《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西南联大名师书系·语言文学大师风采》《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等。
作者在本书跋语里提到,在确定选题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作者曾作过文学所的访问学者,樊骏先生是他的导师,按说樊骏先生应该是最恰当的序作者,但樊先生身体不好,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作者也提到我对他的研究的关注,这也是事实:我和李光荣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了。那么,我就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来谈谈读了书稿以后的观感吧。
我拿着这本厚实的书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在默默地研究,而且是在遥远的山城。”这是我十年前为贵州一位年轻学者的鲁迅研究著作而写的序言里说过的一句话。在文中我还很动感情地谈到,二三十年前,自己也在贵州做过研究,“为寻找一条资料,解决一个难题,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这其中的艰辛,非亲历者绝难体会”。我因此说,自己“对边远地区的研究者,总是怀有特殊的敬意。而且我深知,在如此艰难的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坚持研究,并作出成绩,是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的支撑的”(《袁荻涌〈鲁迅与世界文学〉序》)。这大概也是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关注李光荣的研究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光荣的云南老乡、老师,我的老学长蒙树宏先生。王瑶先生在为他的专著《鲁迅年谱稿》所写的序言里,也说到蒙先生“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鲁迅生平史实研究的新收获》,文收《王瑶全集》第8卷)。这说明,在云南、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默默研究者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地图”时,是不能忽略这一方土地的。而且这种研究也是自有传统的:本书中多处引述蒙树宏先生的论著,显然受到教益和启发,而且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更有着学术精神、方法的影响。
那么,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传统呢?我想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首先是“老实人”。应该说,在边远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的困难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之外,也还有边远地区特有的相对懒散、闲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的惰性,繁琐而又温煦的人事交往对人生命意志的销蚀,视野的局限,由此造成的既自大又自卑的心理等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很难很难的,它需要特殊的素质。第一要有对学习、学术的特殊爱好,以至痴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这样才能以读书与研究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作为精神的支撑,才能如本书作者在《跋》里所说,对学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投入”,使读书、研究、写作成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也才会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即所谓“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此外,还必须甘于寂寞,拒绝诱惑,淡泊名利,特别的勤奋,超人的努力,有鲁迅所提倡的踏踏实实“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未有天才之前》),等等。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老实人”的精神内涵。鲁迅说,这样的人,“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
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一个边远地区的学者,有了这样的“老实人”的眼光、胸襟以后,那些一般人看来边远地区的不利因素,又都可以转化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在贵州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地做学问。贵州外在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引向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好去处”(《我的书院教育梦》)。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者也是要练“内功”的,他的办法,就是身处中心而自我“边缘化”。边远地区的学者却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被客观边缘化了,这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把它变为好事,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怨天尤人,如果进一步身处边缘而总想自我中心化,那就更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这本身就是违背做“老实人”的原则的。
应该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就是一部“老实人”写的著作。没有持续五年的生命投入和“慢而不息”的精神与功夫,是写不出这样厚实的著作的。更重要的,这里还包含了做“老实学问”的精神与方法。
首先是老老实实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其实就是本书《跋》里提到的樊骏先生和我当年建议李光荣选择西南联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近些年许多人都在关心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地方学者的作用问题。我刚参加了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中心、文学院主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下的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特别强调了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地方学者研究本地文化的意义:这是摆脱长期以来的“被描写”的地位,“自己来描写自己”的自觉努力,同时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寻根”过程。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西南联大文学、文化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文学、文化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云、贵地区的本土地方文化与西南联大师生所带来的外来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中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正是这样的有着多元文化因素的新型文化,既成为今天云南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它的研究内涵是丰富的,研究的天地也应该是广阔的。因此,我建议作者还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文学的社团,当年许多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深入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非常有意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强调地方学者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和意义,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此: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边远地区外来干扰少、便于逼向内心的特点,反倒有利于作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思考——当年王阳明最终在贵州“悟道”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或许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在边远地区是最适合于做“最实”与“最虚”的这两头的研究的。在这两个方面,地方研究者都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属于“最实”的研究。于是,我注意到,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研究策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从弄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所谓“基本事实”,包括每一个社团从何时,因什么原因而开始;有哪些参加的成员,其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什么刊物;选择什么文体,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有什么追求,做了哪些实验;各社团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一切分析、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一切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准确、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这本来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工作;鲁迅就强调,他的小说史研究,在史料上是有“独立的准备”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
王瑶先生在为蒙树宏先生的著作所作的序中,就强调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础”意义,并特地提出蒙先生为云南大学研究生开设“鲁迅生平史料研究”课,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李光荣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治学传统,给本书的写作订立了“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的原则,“坚信见解人人可发,而材料(事实)是唯一的”。
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料的发掘、搜集、爬梳、辨析、整理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不仅查阅了可以找到的一切文字材料,而且对可以找到的当事人都进行了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口头历史”材料,并且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本书就大体上弄清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而且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为穆旦、汪曾祺、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线索与思路。比如本书提到了对这一时期汪曾祺的十多篇小说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我们做研究生时,王瑶先生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每一篇重要论文、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或类似的课题,都绕不开你,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尽管后人的研究必然要超过你。我想,王瑶先生这里所说的“不可绕开”,不仅是指你的研究,是否达到、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也是指你在史料上是否有鲁迅说的“独立准备”,为后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事实。
或许更加可贵的是,这背后的学风、研究精神。王瑶先生在前引蒙树宏书序里,也是给其“反复考核、力求准确”“务求翔实”的“严谨的学风”以很高评价。本书的作者在《跋》里谈到他“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不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我也深受感动。这同样是有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本来,学问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会这样大受感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做学问的常识现在被抛弃了,学术研究的底线被突破了。许多的“研究”,可以不顾基本事实而随意乱说,或者依据未经考订、并不可靠的材料,危言耸听,大加炒作,或者抓住片面的材料而任意发挥,大做文章。在这样的虚假、浮华的时风影响之下,像本书作者这样,甘坐冷板凳,做“老实学问”的“老实人”,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并常常被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本书的出版,聊抒感怀,给边远地区的寂寞的研究者以慰藉,为这样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作鼓吹——尽管未必有多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