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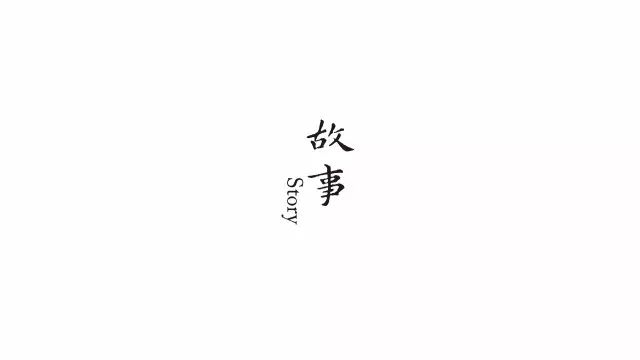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全世界我最喜爱的地方,尤其是博达哈大佛塔这里。大佛塔是世界最大的佛塔之一:洁白的穹顶,中间有一缕缕番红花才有的灿烂金黄色,最上面是金色的塔尖。佛塔的中部四面都绘上了佛陀的眼睛,这是看穿世俗混乱的神圣之眼。
佛塔大门之外就是加德满都熙熙攘攘的街景,和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一样的热闹喧嚣。这一块狭小的地方住了一百万居民:小贩们为了卖给你一只5美金的手串可以追出几条街;这儿的路灯柱子都包着蜂巢大小的密密麻麻的灰色电线,不知道是电工的灵感是来自巫师还是疯子。
这座佛塔似乎驯服了城市。祈福得旗帜在风中飘扬,数百名朝圣者沿着佛塔的基座顺时针行进。我坐在三层阶梯的最顶层,把玩着手腕上5美金买来的手串,干燥的空气弥漫着尘土和烟的味道,让我的喉咙变得沙哑。从这里我可以眺望整座城市——这里的生活似乎脱离了混乱尘嚣:游客在露台酒吧里悠闲的喝啤酒吃披萨,而来自全国124个民族的加德满都本地人,则忙着晾衣服,侍弄花草,享受属于他们的绿洲。
抬起头,我就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在灰尘和薄雾中显出淡淡的粉红色,直冲云霄。世界最高的10座山峰里有8座都在尼泊尔,包括珠穆朗玛峰,这也是大多数游客造访尼泊尔的原因。
我第一次来到尼泊尔时只有26岁,也是雄心勃勃的登山者的一员,不知疲倦的要在这些高山栈道上去挑战体力的极限。这次带着《国家地理》的采访任务,我重访尼泊尔,决心去体验这个国家更不为人知的一面——尼泊尔有着丰富而多样的人文和地貌,只是大部分时候光芒被高山所掩盖罢了。这一次我不登山,相反,我计划深入尼泊尔的古老文化和日常生活,期待揭开它的另一面。
我的旅程从加德满都西南22.5公里、靠近帕平的Neydo Tashi Choeling寺庙经营的客栈开始。
这个金顶寺庙坐落在尘土飞扬的小山上,山上的松树被祈愿者挂满了旗帜。有150位佛教僧侣住在这里,年龄从5岁到27岁不等。寺庙经营着一个有着23个房间的朴素客栈。有的游客来这里是为了放松,有的是为了学习佛法,而有些人则是想体验一下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住客可以参加寺庙例行的晨课与晚课。
我问25岁的客栈管理员Tsering Hyolmo, 允许住店客人观看僧人每日的修行行为会不会很奇怪。
Tsering答道:我们很乐于分享我们的修行行为。这里是一片僻静美好之地,也许访客对了解佛教有兴趣,那当然很好,也许他们只是想从城市中短暂逃离,不管哪一种,我们都很欢迎。
1700米的海拔使得这里的温度远远低于加德满都,我注意到Tsering在他的酒红色僧服外面穿了一件羽绒服。他打开了我房间的门,房间简朴而空旷,然而我需要的却都有:一张结实的床,一张小小的木桌,以及安在屋内的卫生间。
第二天早上,我在清晨寒冷的空气中缩着肩膀,向山顶的寺庙走去。脱掉鞋子后,我在一群和我一样的访客中找到一个位子,面对着金色佛像,在靠墙的垫子上盘腿坐下。坐在我们前面的是几排僧侣,因为天气寒冷,也都把红色或者黄色的僧袍裹得紧紧的。
念经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僧人们用一个调子不停的念诵,中间不时有鼓、号角、法螺以及钹的声音。
我慢慢从表面的噪音里找到了节奏,虽然我并不理解。就像Tsering说的,我的确感到自己被欢迎,但却很难融入他们。好像这些僧人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门,至于要不要迈进去,是我的事情。
每当我在早课中走神(还挺频繁的),我就去观察那些后排的年轻僧人。他们和学校里的男学生差不多,用僧袍的大袖子挡住不断打哈欠的脸,在垫子上扭来扭去,直到一个年长的僧人慢慢却颇有威严地走过来检查为止。
直到最近尼泊尔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因为免费住宿以及受教育的机会,很多当地孩子都进了像Neydo Tashi Choeling这样的寺庙、尼姑庵或者是阿尼度母学院(Arya Tara Shcool) 。有的孩子是被父母送来得,也有的是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Dhekyid Dolma12岁的时候选择了阿尼度母学院,现在她已经22岁了,理想是做一名唐卡教师。唐卡是一种画在棉布或者丝绸上的佛教画,以鲜艳的颜色和繁复的细节闻名。她告诉我,自己“一直就想当尼姑,做一个简单的人,有富足的性灵生活就足够了。”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离帕平西北112公里的Kurintar,在这儿的农村,生活显然不太容易,尤其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陡峭的山坡上,一簇簇铁皮屋顶的房子通过红土小路连接,一座狭窄的浮桥驾于奔腾的河水上,将小村与外面的主路相连。在这些村庄,每家都有一个男人在加德满都或者海外打工来补贴家用。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尤其是女孩子的教育,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晚上我住在Summit River Lodge,这里占地广大,然而要过桥步行才能到达。
清晨,太阳还没有洒下穿透晨雾的光线时,我就起床了,开始沿着住处后面的小径往山上爬。几个村民围着一位年老的妇女,原来她带了一篮子家里种的小番茄来卖。她是从一个小时以外的村子过来的,如果卖不掉,她还要去到下一个村子。
一个正在磨玉米的村妇看到我,站起来向我羞涩但充满善意地笑了一下,用传统方式向我打招呼:双手合十,略微鞠躬。我也照此回礼:Namaste。
她的女儿从屋里跑出来,背上背着一个小婴儿,但是很快又回到屋里了。再次出现时,她端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站在清冷的空气里喝茶,热茶很快温暖了我的手指,我们微笑着交谈,使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家里的鸡则在旁边不停地啄食。
我向她们道谢后又说了一遍Namaste,起身沿着红土路往下走,这时太阳已经晒到我的后背了。
尼泊尔让你直面人类的多种生存方式。贫穷让你逃无可逃。人生中总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平穷与所谓简单生活的界限,对那些能放下自己奋斗来的生活,对陌生人打开家门的善良人们,我们表示敬意;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个时间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值得过得生活。
尼泊尔是一块福地,你在这里仅仅需要“生活”着:丢掉精心策划的路线,你的最佳选择就是不做计划。我的西方思维在一开始总是试图挣扎,然而慢慢我也学会了放手。
正是在这两种思维的转换中我来到了Kurintar以南72公里的奇特旺国家公园(Chitwan National Park) 。奇特旺是一个政府、旅游业以及地方参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当地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是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整个尼泊尔有四处)。这座占地1500平方千米的国家公园是尼泊尔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其前身是皇家狩猎场所,同时也是多种珍稀动物包括独角犀牛、孟加拉虎、豹子、野鹿、鳄鱼和550种鸟类的家园。尼泊尔政府在保护野生动物上十分坚决,几十年前就征用了军队保护国家公园,过去三年里只发生了一起偷猎事件。
我从Barahi Jungle Lodge雇来的向导、27岁的Saket Shrouti (昵称为Saki) 告诉我:旅游业的确改善了当地的生活。“这里的人们过去完全依赖这片森林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他们也打猎野生动物。当国家公园创立的时候,人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限制。然而当旅游业发展起来的时候,电和公路都通了,医生也可以进来看病。慢慢的村民意识到,如果我们保护了犀牛,我们就可以带人们看犀牛,游客就会继续来。只要有犀牛,就有游客,而一旦偷猎者杀死了犀牛,游客就再也不来了。因此当地人也意识到为什么保护野生动物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处。”
奇特旺展现出的尼泊尔是我无法想象的:葱茏,恬静,落日朦胧而磅礴,风吹过6米高的象草,窸窣作响。
第二天早上我果然没有做任何计划,随心所欲地坐上一艘小船,沿着宽广平静的Papti河而下。薄雾覆盖在静止的水面上,唯一的声响就是两根木浆划水的声音,我们的小船缓慢地前进。45岁的Aitaram Bote和33岁的Som Kumal分别在船的前后划船,两人都来自本地的Boteh部落。用我的向导Saki的话说,Boteh人个个都是好水手,熟知这个公园的每一个角落。
Saki本人对于我们看到的一切也了如指掌:白鹭、对岸的豚鹿以及在水中像一根浮木的一种亚洲鳄鱼……
突然Saki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看向对岸。在晨雾中有一个巨大的灰色影子与四周几乎融为一体,但我还是认出了那一对突出来的耳朵。一只独角犀牛从它的进食中停下来,抬起它的大脑袋,向我们投来一瞥。在奇特旺生活着600只这种庞然大物,这都要感谢政府的反偷猎举措。能在自然栖息地看到犀牛,我感到自己幸运极了。
Saki对我耳语:“犀牛常常到河边来喝水。有客人问我犀牛什么时候来喝水,我告诉她,犀牛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是它们的领地。”
这的确是它们的领地。在饱览群山风光后还能见到犀牛,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我的内心充满了平静的满足,这种满足我在博达哈佛塔被太阳晒热的台阶上感受到过,在Kurintar的农妇家感受到过,在Neydo Tashi Choeling寺庙的晨课中也感受到过。
Som和Aitaram把我们带到Rapti河与Narayani河交汇的地方,岸上有一辆吉普车在等我。Aitaram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了几个词。说完我们都转向Saki,希望他会给我们翻译。“他说,如果你再来,可要记住我们啊。”
我想告诉他我当然会记住他的,就像我会永远记住我在尼泊尔隐蔽的山间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