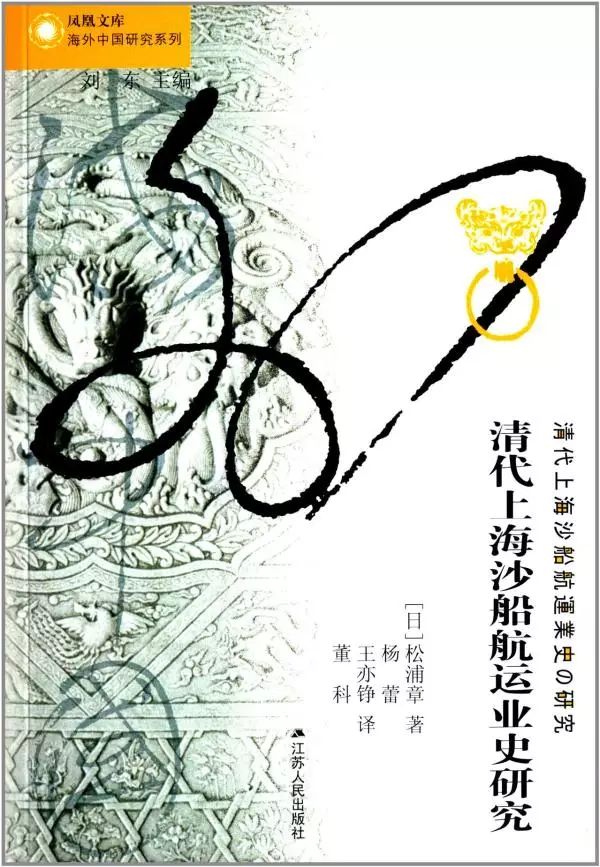
《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
文︱冯志阳
日本学者松浦章教授是一位相当高产的研究者,据出版于2009年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一书的“作者简介”,其当时便已出版著作二十二部。2012年5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又出版了一本松浦章教授的大作《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以下简称《沙船研究》)。其日文版作为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第二十五种,由关西大学出版部于2004年11月出版,范金民教授曾专门写书评向国内推介,誉其为“集大成式的专著”。
据《沙船研究》译者介绍,“与日文版不同的是,在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中,松浦先生加入了近年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清代东北和上海沙船航运业》(第三编第九章)和《清末上海与山东的大豆帆船贸易》(第三编第十章)”。(《沙船研究》“译者的话”)然而,笔者在细致阅读中文版后,发现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不过是此前研究成果的重新排列组合,不仅材料是完全从此前的研究成果中移植过来,而且对于材料的编排和解读,也与此前的研究成果没有区别。
以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为例。该章由“绪言”、“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和“小结”四部分组成,共有二十八条引文材料,全部来自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和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包括“绪言”、“明清时代的上海棉布”、“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和“小结”四部分,其中“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与第三编第九章中的“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高度重复。“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共有十四条引文材料,“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共有十条引文材料,二者有十条引文材料完全一致,即“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中的所有引文材料全部来自“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
接着来看对史料的编排。“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所引史料的先后顺序是:葛元煦《沪游杂记》、《字林沪报》第875号、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县续志》、《字林沪报》第575号、《字林沪报》第667号、《国闻报》第43号、《国闻报》第312号、《国闻报》第330号、《国闻报》第464号、《国闻报》第471号、《国闻报》第1号、《中外日报》第88号、同治年间上海知县的一则公文。此外,该节还根据《中外日报》的信息,整理了德大号布行进行沙船营运的情况,最后又根据祥泰号工作人员周茂生的口述,强调“如果缺少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沙船往东北各地的航运活动,像祥泰布号这样的棉布买卖就不可能顺利开展”。“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所引史料的先后顺序则是:葛元煦《沪游杂记》、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县续志》、《国闻报》第43号、《国闻报》第312号、《国闻报》第330号、《国闻报》第464号、《国闻报》第471号、《国闻报》第1号、《中外日报》第88号。与“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相比,“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少了《字林沪报》第875号、575号、667号和上海知县的公文等四条史料,以及德大号布行经营沙船的情况,其他方面如所引史料、行文顺序均完全不变,甚至该节也是以祥泰布号工作人员周茂生的口述收尾。
再来看对史料的解读。以天津《国闻报》第1号的材料为例,全文如下:
营口新闻 民船进出口数○营口为东三省水道咽喉,商舶咸集,帆樯林立,从前民船每岁进口,约计二千余艘,有时多至三千以外,中外通称以来,轮船渐多,民船渐少,上年计到八百号。(《沙船研究》,281、407页)
引文中“中外通称”当为“中外通商”,而两处引文皆误为“中外通称”。该段引文还全文出现在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即作“中外通商”。(《沙船研究》,293页)第三编第四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营口市地处沿海,是进出东北地区的门户,从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集聚于此,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千艘以上。然而对外开放之后,外国的蒸汽船逐渐来航,民船的数量急剧减少,时至光绪二十二年,船只数量减少到了八百艘。(《沙船研究》,281页)
第三编第九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位在东北水道咽喉之地的营口,聚集了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一眼望去帆船的桅杆树立如林。以前每年来往民船有二千艘以上,多的时候高达三千艘,但是口岸开放之后外国汽船增多,民船出入营口的数量剧减,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民船数量已减少到八百艘。(《沙船研究》,407、408页)
两处释读差不多都只是对引文材料的复述,因而内容不可能有差异。有意思的是,在引文错误都一致的情况下,两处释读文字却存在着叙述上的差异,而不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复制关系。不管这种文字叙述上的差异是否刻意为之,第三编第九章中“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内容,照搬第三编第四章中“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事实,不容讳言。
第三编第九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与第三编第五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内容照搬的情况。“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也是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两者引文材料完全一致,材料编排顺序也完全一致。如果说,“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可以算作是对“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缩写,那么“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则基本就是对“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内容的复制。此外,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中“绪言”、“小结”部分所引用的三条史料,均来自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中的“绪言”和“小结”。
综上,《沙船研究》收录的所谓“最新研究成果”之一,即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实际上就是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中的“绪言”、“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和“小结”等三部分内容,与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的“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内容的复制和重组。另一篇“最新研究成果”,即第三编第十章“清末上海与山东的大豆帆船贸易”也存在这种情况。该章第三节“依靠沙船所进行的上海和远东间的大豆贸易”之第三小节“上海的沙船航运业和豆业”,可以说就是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的第四节“上海沙船航运业与豆货”内容的略微简化和改写。诸如此类,在《沙船研究》中仍有不少,并不限于“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说,《沙船研究》一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史料的大量重复引用。史料重复引用两次的情况非常普遍,重复引用三次、四次的情况也不鲜见。如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中关于“沙船”的那段记载:
本邑地处海疆,操航业者甚夥,通商以前,俱用沙船,以其形似沙鱼,故有此名。浦滨舳舻衔接,帆樯如栉,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当时本邑富商,均以此而获利。
这段史料分别出现在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和第十一章“清末英商佣船金万利沙船的航运活动”中,被完整引用四次。(《沙船研究》,271、290、402、438页)范金民在对日文版的书评中也提到过类似问题:“原书第250页表4和253页表6,都是《道光六年海运郁其顺船运航表》,完全相同。”
范金民赞誉《沙船研究》日文版,首要之点是“挖掘出了大量罕见的珍贵资料”,表示“单凭搜集和利用的新材料,《沙船研究》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沙船研究》在资料搜集上的显著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对此也十分钦佩。对于史料相当有限的沙船航运业史研究,史料重复引用的状况似乎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同一条史料可以说明多个问题的情况下。例如前文所述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中关于“沙船”的那段记载,既可以说明沙船与棉布为主的南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明沙船与豆货为主的北货之间的关系,因而为第三编第四章、第五章全文引用。另外,不同论题的交叉和重复,也使得史料重复引用的现象变得愈发严重。例如前文所述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与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和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内容的高度重复,正是由于论题的交叉所致。因为要论述上海沙船航运业与上海棉布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涉及到棉布在东北地区的销售状况;要论述上海沙船与豆货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涉及到东北地区豆制品的交易情况;同样,如果要论述沙船航运业与东北之间的关系,则不得不提豆制品在东北的交易情况和棉布在东北的销售情况。论题交叉,再加上史料匮乏,遂使得《沙船研究》不得不大量重复引用史料。
史料的重复引用问题,本无伤大雅,特别是在一些非核心史料的引用上。然而,重复引用终究是有限度的,当某一章节的材料乃至论述,完全出自此前的研究,再将其冠以“最新研究成果”的名号,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这个“最新研究成果”,只是作为一篇论文,去参加某个会议,也未尝不可,但将其与它的“母本”编入同一本专著,让读者轻易窥破作者著作等身的“秘诀”,殊为不智。
另外,《沙船研究》中文版在翻译、排版方面的问题之多之奇,简直就是一个车祸现场。例如《沙船研究》第299页有这样一段引文:
查盛京各海口杂粮,向来查禁海运之年,惟黄豆大船准带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也就是说,即使是禁止海运的年份也允许运输黄豆,标准是大船二百石,小船一百石。
这段引文出自嘉庆年间的《山海榷关政便览》,《沙船研究》误为《山海权关政便览》。看到这段引文,笔者就觉得后一句话应该是作者自己的话,后来果然在《沙船研究》第410页看到同一段引文:
查盛京各海口杂粮,向来查禁海运之年,惟黄豆大船准带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
后面的正文内容是:“据奏文内容,海禁之时运送黄豆的船只,大船装黄豆二百石,小船装载百石是在许可范围之内的。”如果前后章节进行一下统稿,是不难发现这些错误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统稿,《沙船研究》中前后矛盾之处也十分常见。例如《沙船研究》第227页说沙船商王文瑞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十八日,而第338页又说王文瑞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再如《沙船研究》第158页所引史料表明一艘沙船“一年税银九十四两”,而在第161页又写到“这艘船的税银是一年九两四”。在引文的标点上,也常常出现错误,如《沙船研究》第294页有这样一段引文:
今年东三省大豆非常丰作,豆价及饼价逐渐低落,近来日本肥料市场稔知豆饼为第一重要品,故销路日渐扩张加之。本年饼价低廉银价,又贱核算甚为合宜,故而猛烈买进。……
如此断句,完全不通,或许应该这样断之:
今年东三省大豆非常丰作,豆价及饼价逐渐低落,近来日本肥料市场稔知豆饼为第一重要品,故销路日渐扩张,加之本年饼价低廉,银价又贱,核算甚为合宜,故而猛烈买进。……
事实上,这段引文内容并不复杂,很好理解,只要稍加用心,应该就能准确断句。还有一些多次被引用的引文,有时断句正确,有时却断句错误,如《沙船研究》第298页引用了《盛京时报》的一段话:
○锦州西海口、旧称油粮口岸。凡到口沙、鸟船均由锦城粮店,购买元豆,运往浙闽等省售卖。今秋锦属豆糖歉收,价值太昂,每斗需洋一元三四角,比较常年加半倍之,谱所以南省商船,均闻风不进云。
《沙船研究》第409页再次引用该段话,标点显然更加合理:
○锦州西海口旧称油粮口岸,凡到口沙、鸟船均由锦城粮店购买元豆运往浙、闽等省售卖。今秋锦属豆糖歉收价值太昂,每斗需洋一元三四角,比较常年加半倍之谱,所以南省商船均闻风不进云。
同一本书,同一段引文,只因出现在不同的章节,结果标点全然不同。这类问题在《沙船研究》中真可谓比比皆是。
其他诸如错字之类,更是常见,如《沙船研究》第283页,两次将《中外日报》误为《中外时报》;第206页将“捐纳”误为“损纳”,如此等等。即便是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也会弄错名字,如《沙船研究》第203页,将黄宗羲误为“黄宗义”。《沙船研究》第213页是郁氏家族生卒职业表,郁润桂和他的两个儿子郁彭年、郁松年作为郁家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列在表格最前面,在介绍郁彭年和郁润桂的关系时,表格中填着“润桂长子”,不可思议的是在介绍郁松年和郁润桂的关系时,表格中依然填着“润桂长子”。两个“润桂长子”在表格中上下紧挨着排列,别无间隔,稍加浏览,不难发现。可以说,这些错误都是不应该出现的,都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当然,一本接近五十万字的著作,出现一些文字错误,本也情有可原,但如《沙船研究》类似错误之多,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沙船航运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沙船研究》在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上固然令人佩服,然而其在运用史料时的大量重复引用,尤其是部分章节实际上是以往研究成果的重新排列组合,再加上翻译排版时的大量错误,都不免使得《沙船研究》一书的价值大打折扣。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