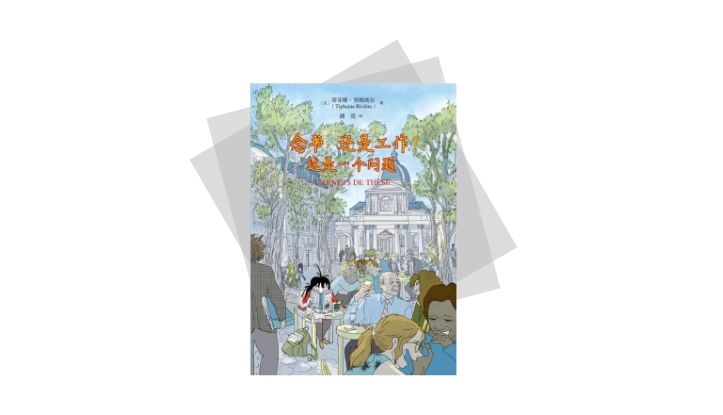《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
黄芙蓉 /译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对此我深感荣幸。本书是一部论文和演讲集,源于对象引导本体论作为显性文化力量崭露头角的那一时期。尽管早在
2009
年,列维·布莱恩特(
Levi Bryant
)创造了“对象引导本体论”一词,
但当时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已是小有成就,
即便此时还在对象引导研究的初始阶段,并且只是我研究生期间暧昧不明的研究方向,但我对此仍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或许,序言是为中国读者简单介绍对象引导本体论思潮之历史的上佳之处。因为,较之于美国读者,他们对此可能不甚熟悉。
我的初衷仅仅是为阐释海德格尔哲学,
尽管迄今为止,这一阐释仍未得到海德格尔研究学者的欣然接受,或者说时至今日,仍未获得多数学者的热情接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
20
世纪哲学的经典之作,此书的每一位读者都熟悉书中开始部分提到的著名的工具分析。尽管早期的现象学主要研究的是对象如何出现在意识之中,但海德格尔却指出这是我们与诸物打交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诸物视而不见。无论是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锤子,正常运行的身体器官,还是呼吸大气中的氧气,我们都不会注意到对象,直至它损坏或失灵才有所察觉。在此之前,对象通常处于我们意识之外。它们属于一个完整的工具体系,在此体系中,工具的个性融入人类此在具有广泛蓝图的更大整体之中。通常我们会这样理解:海德格尔认为无意识的行为产生于有意识的理论之前,只有当无意识行为不奏效时,我们最终才开始从理论出发,去探索这个世界。
然而,
这种常见解读有个严重问题。
诚然,
我们在对某个事物进行观察或思考时,
会停留在其表面,
或者还原为特征勾勒。一把椅子、一剂化学药品或一幢建筑的本质要远比我们对其感知和认识更深:对象比我们所见、所言要深得多。但与感知或理论一样,我们对诸物的实践并未能让我们与它们有更深的接触。我们在使用锤子或椅子时并未能穷尽其全部实在,海德格尔真正的意图不仅仅是告诉人们理论和实践的严重对立,而是让我们知道理论和实践都不能让我们充分认识诸物,而只是停留在了对其表面的认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若我们的实践过程能够充分认识诸物,那它们就不会损坏。损坏证明在人类与之接触之外有存余。这样,海德格尔的对象沿袭了伊曼纽尔·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的传统,即对象存在于人的接触之外,人类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却无法理解和认识。
请注意,
尽管康德在
1780
年代发表其主要著作之后,
就已经成为西方哲学泰斗,
但如今康德的继承者们认为他的物自体概念并非正确。
大部分人都接受德国观念论者对康德的批判的一般性框架:
如果我们试图思考思维之外的对象,
那么它本身也是一种思维。
因此,
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人类思维封闭的范围之外。
这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理论中是正确的,
如同德国观念论者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一样,
尽管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的确带我们追溯到关于物自体的论断,
但这并非他的本意。
这并不足以说明,
康德关于实在对象存在于与人类的关系之外的论断的正确性。
这是由于不仅人类之外存在着不能够接触的外界,
对象互动时也是如此。
一个中世纪伊斯兰哲学中最常见的例子:
火燃烧棉花时,
轻而易举就能将其化为灰烬,
然而,
棉花的很多特性与火并不相关,
火只是接触了棉花的可燃性,
对棉花的其他特性却是一无所知。
这样看来,宇宙中的每一种关系,无论人类参与与否,总是受到存在于关系之外、不涉身其中的物自体的影响。火与棉花之间的因果互动并不是火本身和棉花本身之间的互动,而是两个对象的感官特征勾勒之间的互动,因而,关系性必须总是对象间非直接形式的接触,而非直接的。尽管对象引导本体论是后康德哲学中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但类似的观点已经出现在其他领域。在生物学哲学中,智利学者哈姆伯图·马图拉纳(
Humberto Maturana
)和弗朗西斯科·瓦里拉(
Francisco Varela
)发现,细胞是稳定的单元,它极力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外界最多只是间接交流。“二战”以来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
)从中获得灵感,认为社会交流只是在交流之中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作出这样交流的个体之间。
此类论点使对象引导本体论着力强调美学在哲学中的基础作用。
尽管直接认识世界和交流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间接地进行,
通过隐喻等“不言而言”
的手段,
还有更一般性的,
间接的暗示、
威胁和影射这些在人类交流中常见的方式。
最终,即使哲学本身也是一种知识,
但也只不过是一种“不言而言”。希腊词汇
philosophia
的意思是爱智慧,但并非实际的智慧。苏格拉底从来未能给事物下个好定义,他所说的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无知,这并非反讽。
多年以来,作出此论断的只有我自己。但
2007
年,在伦敦金史密斯学院(
Goldsmiths College
)举办的思辨实在论工作坊中,对象引导本体论成为四个哲学思潮之一而闻名。不久之后,许多像伊恩·伯格斯特(
Ian Bogost
)、列维·布莱恩特、蒂莫西·莫顿(
Timothy Morton
)等研究对象引导的思想家加入了我的行列,他们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艺术家和建筑学家将对象引导本体论看成是其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后,社会和组织领域的理论家亦是如此。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讲座邀约,
2014
年
6
月,我满怀愉悦地踏上了第一次中国之旅,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发言。
对象引导本体论仍是个崭新的哲学领域,
在与无数其他领域碰撞中发展其原则。
在任何领域,
对象必须超越它们涉身其中的关系,
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
这将扩展到每个研究领域。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
能让中国读者更容易地了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自
1992
年起我便投身其中的这种思维方式,
当时,
我第一次试图开创一种对海德格尔的新的解读方式。
本书中的论文和讲座囊括了我最挚爱的那个阶段,
即对象引导本体论在英语学界逐渐被更广泛的公众认知的时期。也允许我感谢本书的译者黄芙蓉,她曾就本书内容提出了颇有见地的问题。在此,我要对她表示感谢。
格拉汉姆·哈曼
洛杉矶
2017
年
3
月
选自: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新书上架
○●
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
格拉汉姆·哈曼 著
黄芙蓉 译
2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