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一个以伦理精神为内核、以法律制度为支撑、以法律行为为表象的文化系统。
法律(包括刑法)与伦理道德的共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并行不悖并且保持一致发展方向的内在联系。
在动用刑罚手段的时候,如果不考虑一定的伦理因素,那么刑罚就将难以被社会接受
并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自由、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
在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如何使刑罚这一国家在和平时期最为严厉的惩罚手段彰显社会伦理价值,在充满刚性的外表上,赋予伦理道德的温情,充分发挥伦理对刑罚的补充作用,
这将对中国法治的进程以及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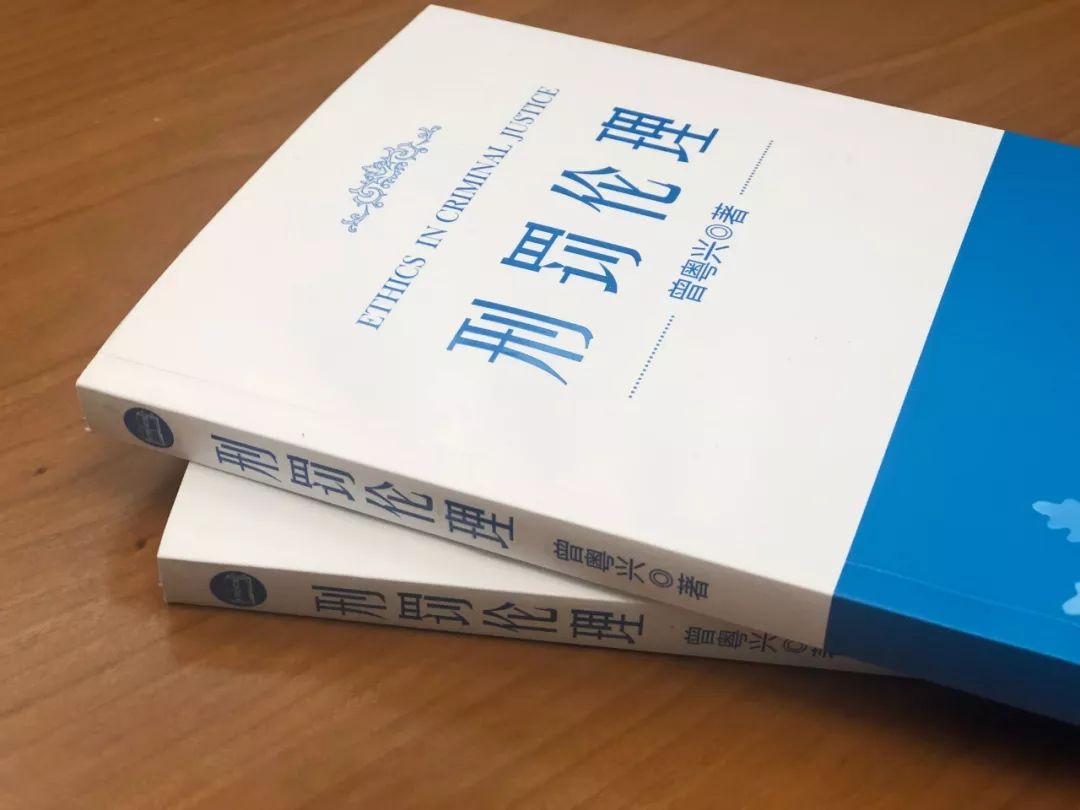
中庸与相对的公平正义,与辩诉协商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内在联系,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而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容易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而这种平衡点,也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联结点,
中庸守公平,人道出正义,和谐意味着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中庸地得到并重。
中庸之刑即公平之刑,人道之刑即正义之刑,秩序与人权并重之刑,乃社会和谐之促进手段。
刑罚作为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当然应当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政治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保持高度的一致。
刑罚应以伦理道德为根基,不管是在制刑、配刑还是在动刑、行刑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评价,尽可能地将刑罚与伦理的评价结合起来,从而使刑罚更加符合人道性、公正性等伦理精神。
要求司法人员公正处理案件,不等于要求封闭其正常的伦理道德心灵
。
个案的审判,应当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这是审判艺术实现刑法价值与刑罚目的的内在要求。
因此,所谓法网无情之类的说法,只不过是文人吸引读者眼球的艺术表现,
法网应当杜绝的是私情
,
因此才有回避制度,
但法网不能割裂人类的美好情怀
。
情、理、法和谐一致的处理结果,方能让公民感受法律的脉脉温情和亲和力,才能真心信仰法律,自觉遵守法律, 如果人类可以摆脱正常情感审理案件,那么根本无需人类充当法官,机器人会比人类更容易处在中立位置,会比人类更加胜任“无情”的裁判。
没有蕴含美德的社会经验的指引,法官的自由裁量将会带来灾难性后。
司法体现社会伦理,有必要考虑被害人及其亲属的道德体验, 不过,一般来说,社会伦理的普遍认同属性决定了被害人的道德体验与司法人员以及社会大众的道德体验具有一致性,中外莫不如此。
出于“维稳”考虑,有时司法机关明知判决与常识、常情、常理不符,仍然会一意孤行。
刑罚是群体人性要求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刑罚的产生必须符合人的理性的要求
,而符合人的理性要求,最终应符合人的世界观要求,即符合人的哲学观的要求, 因此,刑罚的运用需要有伦理哲学底蕴。
刑罚是由国家发动的
,在体现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的道德评价的同时,
还必须同时体现国家对社会道德的示范作用。
刑罚的手段必然受到社会伦理道德承受能力的限制, 国家在动用刑罚手段的时候,如果不考虑一定的伦理因素,那么刑罚就将难以被社会接受并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刑罚的过量与滥用,不仅不能起到支持伦理的作用,甚至会败坏伦理。
执法应该体现伦理价值,应该尊重和关爱个体权利,使每一个公民通过一个个与自己有关的具体案例,以及一个个身边真实的执法者去体验我们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去感受权利和人格被尊重的程度。
真正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的刑法,确保刑法内容不再是统治者单方强制意志的表现,一般会反映自由、人道、宽容等基本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
法网不能割裂人类美好情怀,情、理、法和谐一致的处理结果,方能让公民感受法律的脉脉温情和亲和力,才能真心向往法律,自觉遵守法律。
有经验的法官对案件的把握一般比较准确,而且经验的积累,会让审判人员充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充分考虑常识、常理、常情,从而作出合理的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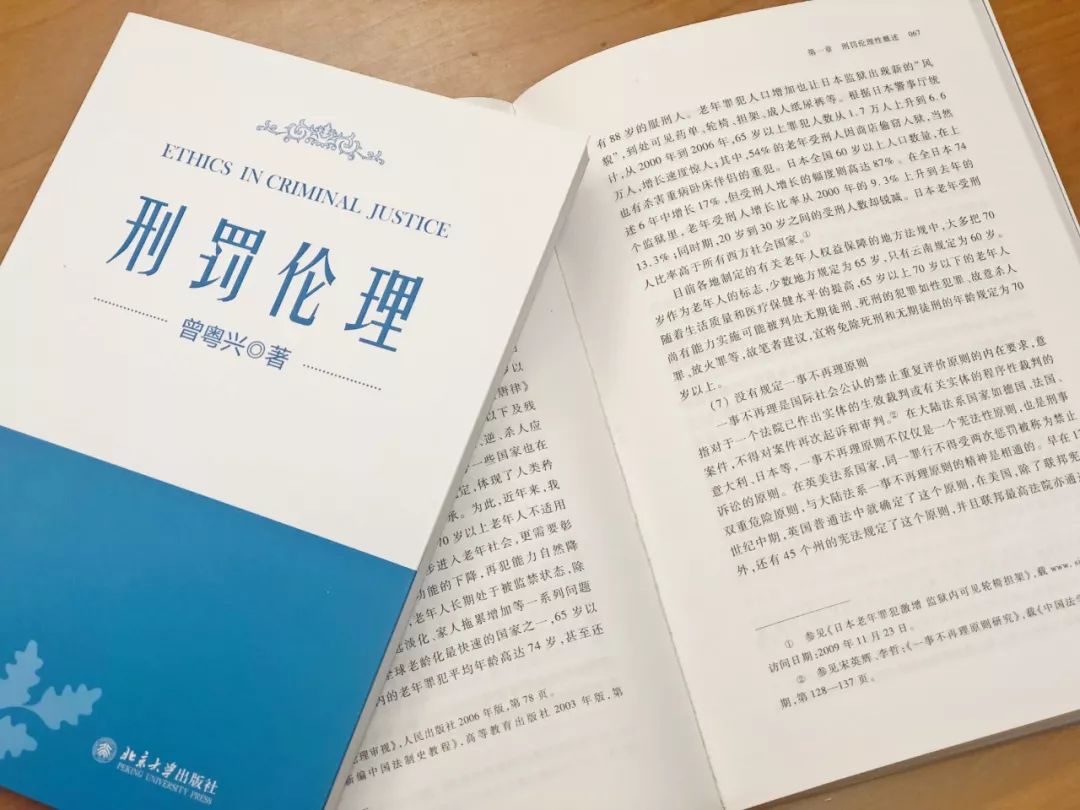
法律既是冰冷的理性,却又饱含脉脉温情, 因此,
“应当以合乎情理作为司法的指南,在每一案件中努力获得特定境况中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当然,司法活动中不宜过于张扬情理,屈法伸情无疑会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难以做到罪责刑均衡。
人权不能因为公民生存地域不同而有悬殊,公正的司法不能因为当事人生活地域不同而区别对待。
刑罚体现社会伦理这一命题不仅在立法上而且在司法、执法上都为“人情”“人道”进入刑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能促成刑罚向真正的能够理解人的、有价值内涵的人道主义刑罚转变。
八议之制,既有法理支撑,也符合宽严相济政策,还有刑罚个别化原则作为依据,对八议范围里的人网开一面,实质上是对贤、能、勤、功行为表现的肯定,有利于鼓励公民平时积极建功立业、奋勇上进。
若其与不贤、无能、不勤、无功之流犯同样的罪错,对两类不同的人作同样的处理,恰恰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
从法理上说,对实施了同样的罪行(指行为),具备了同样的人身危险性的人,应当作出同样的处理;对实施了同样的罪行(指行为),但不具备同样的人身危险性的人,当然应当作出不一样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