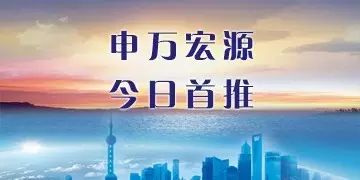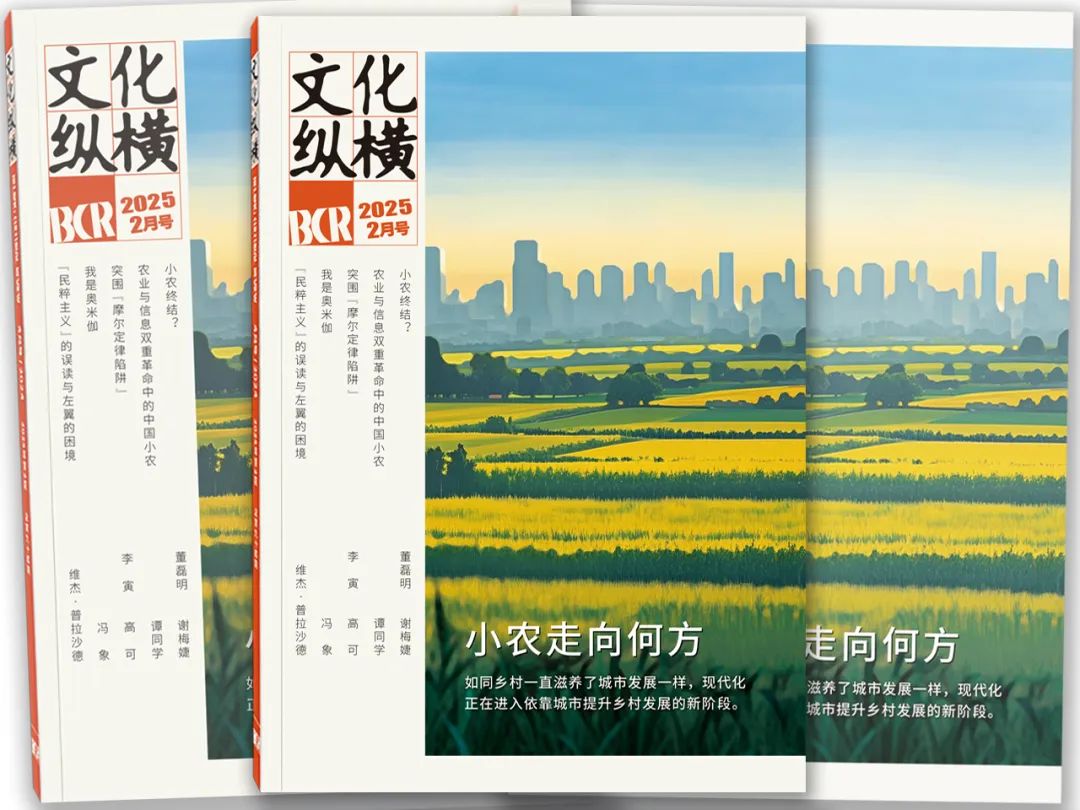
2024全年
6期一次
发货
,看得爽快,更享折扣
2024+2025双年、2025+电子刊,
组合下单更优惠
【导读】
清代政治运作,存在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的一条以内阁为枢纽的公开行政渠道,暗的一条则是甩开官僚机构的“秘密政治”,
其载体主要是上行的奏折和下行的廷寄
这两种独特的文书形式
。
清代皇帝以雍正为代表,利用这条统治的暗线,打破明面上的官僚统治的层级结构,使官员相互监视、相互猜忌、相互告发,只对皇上一人负责,使皇上能直接掌握地方的一举一动
。
然而,秘密政治也存在弊端,如廷寄缺乏法律效力,可能导致官员不配合;奏折的非公开性也使得皇帝的决策缺乏透明度和监督,容易引发错误。而到了清末,
这种政治模式所导致的信息不透明更是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时,加剧了社会恐慌和政治危机。
本文转自“读书”公众号,
原载《读书》2024年第9期,原题为《
不可告人的奏折:清代秘密政治发微》,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不可告人的奏折:
清代秘密政治发微
与历代王朝相较,清代统治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秘密政治!
清代秘密政治围绕奏折展开。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上行文书,在保密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必须亲笔书写,不得假手幕僚,而且要在密室书写;奏折经皇上朱批后发还原奏人,也要在密室启封开读;原奏人不得泄露奏折内容;官员之间不得互相探听奏折及朱批内容。
所谓奏折,实际上是绕过正常行政渠道,直接写给皇帝的秘密信件,通俗点说,就是小报告。
打小报告,古今中外都免不了,但只有在清代,小报告得到合法化、制度化,成了最高统治者决策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
清代政治的运转,以小报告为核心,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精髓,就是打破官僚体制的层级结构,使上下级官员互相监视,只对皇上一人负责。
秘密政治的载体,除了奏折,还有廷寄。奏折经皇上审阅、批示后,由来人带回。有时批示内容过长,就由皇帝口授,大臣拟好谕旨后,经皇上审阅,封缄严密,交到兵部由驿站直达该官员,
这就是所谓廷寄,清代独创的下行文书
。与奏折一样,廷寄的特点也是保密性强,不走层层下达的正规渠道。
奏折是小报告,而廷寄(包括奏折上的朱批)相当于领导批的条子。一上一下,秘密政治就闭环了。
清代政治运作,存在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的一条,以内阁为枢纽,
上行下达都遵循一层一层的公开渠道,在文书上主要体现为题本(上行,一律走驿站)和明发上谕(公开发布的谕旨)。
内阁的设置是对明代制度的继承,但其权力与明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阁臣票拟,只能秉承皇帝意旨,极少有发挥个人见解的空间。
暗的一条,就是通过奏折和廷寄,
让皇帝
得以甩开官僚机构,直接指挥广大官员。
不过,秘密政治也会有运转失灵的时候。比如廷寄,恰恰
因为其秘密性,不像明发上谕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可能会遭遇尴尬处境。
洪杨事变初起,清军一触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态势。关键时刻,因母丧回湖南守孝的书生曾国藩,拍案而起,只手补天,挽救了大清王朝。咸丰七年,他向清文宗奕詝抱怨:“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廷寄好比国家领导人私信某官员,责成他处理某事,其他官员眼红,不愿意配合,就有理由了:俺没收到正式通知,哪知道怎么回事!
同样,由于奏折的非公开性,即便皇帝在朱批中已经允准的建议,仍然需要以题本的形式公开上奏。有时候报告同一政事的奏折与题本同时拜发,一般奏折会先到。乾隆三十八年,关于一件大案,浙江巡抚三宝先上题本,数日后才呈递奏折,为此清高宗弘历下旨申饬,称其“缓急倒置”。
个中奥秘,就是皇上要尽可能抢在官僚机构之前,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雍正年间,清世宗胤禛一方面大规模推广奏折,使其逐渐取代题本,成为中央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另一方面并不打算以暗线完全代替明线,相反,刻意维护以内阁为枢纽的明线,其表现就是将内阁升为正一品衙门。此举的含义,可以透过雍正八年的一份上谕,看得清清楚楚。
胤禛首先说明,既然有了题本,为什么还需要奏折:“督抚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岂无督抚所不及知,或督抚所不肯言者?于是又有准提(提督)镇(总兵)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具折奏事之旨。即道员、武弁等,亦间有之。无非公听并观之,欲周知外间之情形耳。”提督、总兵是各省绿营的最高长官,品级大致与总督、巡抚相当。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是雍正年间有资格上奏折的官员的主体。此外,也有个别道员和总兵以下的武官获此殊荣。
所谓“公听并观”,就是让各省高级官员相互揭发,或者越级发表意见,从而将控制权牢牢把握在皇帝一人之手。
胤禛的高明在于,他深知,奏折固然能使他绕过井然有序的官僚体制,直接掌握地方的一举一动,但理性的行政层级系统一旦崩溃,政治运作会陷入混乱:
凡为督抚者,奉到朱批之后,若欲见诸施行,自应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夺。为藩臬者,则应详明督抚,俟督抚具题或咨部之后,而后见诸施行。若但以曾经折奏,遂藉口已经得旨,而毅然行之,则如钱粮之开销、官员之举劾,以及苗疆之军务、地方之工程,诸如此类,督抚皆得侵六部之权,藩臬皆得掣督抚之肘矣。行之日久,必滋弊端,为害甚巨,不可不防其渐也。
督抚可以绕过部院,通过奏折直接跟皇上联系,这一制度设计的妙用是使得天子可大权独揽。如果各地督抚只以这种方式处理政务,那就意味着六部名存实亡,中央机构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怎么整合各省?再如布政使、按察使是督抚的下属,如果他们不把督抚放在眼里,自作主张,越级跟皇帝商讨政事,督抚却不知情,地方不就乱套了吗?
早在即位初,胤禛对此就有清醒认识。雍正元年,他在福建布政使黄叔琬的奏折上批示:“
虽许汝奏折,不可因此挟制上司,无体(‘体’指上下级体制)使不得。
若督抚有不合仪处,只可密密奏闻,向一人声张亦使不得。一省没有两个巡抚之理,权不画一,下重上轻,非善政也。……奏不可频,恐尔上司疑忌。”通过奏折,胤禛让下级监视上级,但颠覆层级结构又是他不愿看到的。
所以,上引雍正八年谕旨强调,尽管你已经私信我了,我也批准了,还得再走一遍正规程序。
督抚根据情况,要么上题本,要么跟六部协商。藩臬则要向督抚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由督抚上题本或者咨询六部。担心行政体制崩塌是胤禛虽钟情暗线,却坚持不废明线的第一个原因。
他接着谈到了第二个原因:
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协助)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员、笔帖式、书吏多人,掌管册籍,翻阅规条,稽查原委也。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
所谓“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过是制造自己无所不能的神话,
但这里描绘的君主抛开官僚机构,单凭一己之力统治国家会带来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国家行政运作,依赖规则,并需参考以往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档案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而奏折只是臣下和皇上个人私下交流的工具,哪怕皇帝三头六臂,再加几个帮手,也不可能代替长期依托档案工作的专业化机构。胤禛很清楚,自己的个人考量可能会有很大欠缺,坦陈“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
一道行政命令的发布,要经过层层审批,虽然繁琐,也是为了保证其合理性。奏折在绕过官僚机构的同时,也绕过了防止出错的制度设计。秘密性是把双刃剑,能使皇帝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前所未有地掌控政局,但也会使皇帝的个人决策面临急剧增大的错误风险。
官僚体制是安全阀,抛弃安全阀无异于自取灭亡。奏折得到朱批肯定,还要再走正规程序,就是为了让相关部门起到把关的作用,以避免决策失误。
为防止安全阀失灵,“凡折中批谕之处,不准引入本章,以开挟制部臣之渐”。督抚上题本或跟六部协商时,不得透露皇帝的批示。道理很简单,皇上都同意了,谁还敢说个不字?所谓“挟制部臣”,是担心督抚以圣旨为名,“恐慌部院九卿,令人不敢开口”,从而使君主的错误决策,失去了矫正机会。这不是胤禛有意放弃独裁,而是保障行政合理性的必然要求。
谕旨的最后,是对地方官员的警告:“若督抚提镇等,以此愚弄属员,擅作威福,准属员据实揭报,或该部,或都察院,即行奏闻。若属员等以此挟制上司,肆志妄行,着该督抚提镇等,即据实参奏。”
皇帝借奏折破坏现行制度,树立个人权威,同样,地方官员也可以利用朱批突破制度的限制,为个人谋私利。胤禛明白,尽管秘密政治使独裁者如虎添翼,但不加以管控,等于引火自焚。
奏折的保密性还会带来另一个潜在风险。胤禛继位没几天,就颁布了一道谕旨:
军前(前线)将军、各省督抚提镇等处所有皇考朱批谕旨(即朱批奏折),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京师满汉大臣、官员,凡一切事件有皇考朱批谕旨,亦俱着敬谨封固进呈。目今若不查取,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考之旨,捏造行事,并无证据,于皇考圣治大有关系。嗣后朕亲批密旨,亦着缴进,不可抄写存留。
康熙年间,奏折抄录副本留存军机处的制度尚未建立,
这天底下独一份的绝密文件,因为朱批的存在,拥有了巨大的潜在能量,一旦被“不肖之徒”利用,后果难以想象
。
如果有人伪造朱批,也无从辨别真假。雍正朝建立了录副制度,但副本深藏宫中,只供决策参考,不足以防范地方上借此招摇撞骗。
所以胤禛一上台,就把奏折回收当成头等大事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