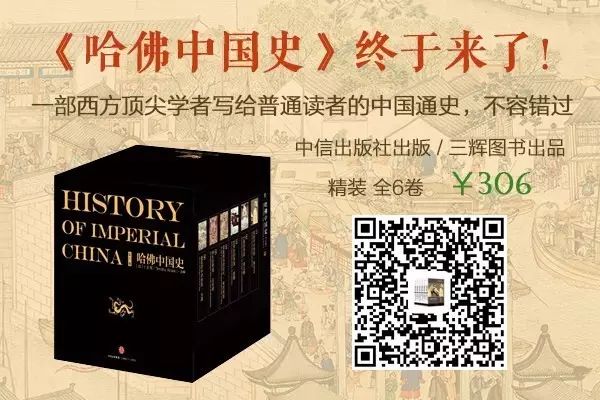随着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起势和英伦退出欧盟,媒体上的“民粹”或“民粹主义”一词如过江之鲫。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一路过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正如英伦公投成功,也是因为民粹起了作用。前些时读到微信公号“米筐投资”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很有趣,《乌合之众、民粹主义将掌控人类的命运?从万科王石、英国脱欧、特朗普说起……》。内容不论,让人感到喜剧意味的是,既然乌合,又如何民粹?这两个词圆枘方凿,价值走向正好相反,岂非不搭?
以上民粹的语用,我个人感觉是“学术不正确”,或者说“学术不准确”。“民粹主义”一词来自英语“Populism”,但是,这个词的意涵是“平民主义”。不清楚20世纪中国,最早是谁将平民主义同时翻成了民粹主义。本来是一个价值中性的词,如此一翻便转成了褒义。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翻译是神来之笔,因为它竟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现象级的。
平民主义并非民粹主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其民主就是一种平民主义的政治,但不能说是民粹主义的政治。
陈独秀反感当时议会框架内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两党游戏,认为这是少数人的政治,与全体国民或绝大多数国民无关。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呼唤“惟民主义”,这个“民”就是平民。陈独秀早期的民主理念吻合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它不是一个人的君主政治,亦非少数人的贵族政治,而是最大程度平民化的多数人的政治。
让政治成为每个人的事,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中国读者写了一本介绍英美政治的小册子,叫《政府的基本原理》,但1922年在中国出版时,罗家伦将书名译为《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其实,美国政治是精英性质的代议政治,还真不是“惟民主义”的平民政治。
但是,平民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政治的最大逻辑: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每一个人的事,不是少数人的事,不需要也不能让少数人越俎代庖。起初《新青年》坚持的就是这个逻辑,它并没有民粹的意思。不但民不粹或未必粹,相反《新青年》作为一份精英主义杂志,民恰恰是它要启蒙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自不待言。构成它的两大革命一是“文学革命”,一是“思想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回忆他当年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启蒙所以必要,正在于民众愚昧。鲁迅的作品揭露了各种带有劣根色彩的国民性,也正可见出鲁迅本人的精英立场和启蒙意识。
不应把“平民主义”翻译成“民粹主义”,恰如不能把“平民”翻成“乌合”。中性的平民,往褒义去是民粹,往贬义去就是乌合。是褒是贬,端看你是什么立场。视民众为乌合,这是精英主义。相反,民粹民粹,关键在“粹”。粹者,精华也。本义指精米,转意为美好。当一些知识精英认为民众麻木愚昧从而需要启蒙时,民粹主义却做出了相反的表述:美好在民间,民间有精粹。在后者看来,真正愚蠢伪善的不是底层、不是草根,而是那些高高在上俯视民众的知识精英。
启蒙精英与民粹精英拉锯
只是,民粹主义的概念往往被窜用。开头那篇文章把乌合之众与民粹并举不说,资中筠先生最近的一次讲话《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最大的愚昧》,也有类似问题。资先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卖菜的小贩,天天骂政府损害他的利益,可是一阅兵,一说小日本,架式马上就起来了。这就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是走向文明的一个绝大阻碍。出路在哪呢?就是启蒙,enlightment,这就是光,让智慧之光驱散愚昧。”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一、这个例子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民粹主义,与民粹无关;二、民粹不愚昧,相反很聪明。它本身就是一种精英话语而非民众话语,只不过它反的是启蒙精英。启蒙不但治不了民粹,甚至20世纪思想史,其中一页就是民粹精英完胜以民众为愚昧的启蒙精英。
就20世纪历史而言,应该是苏俄十月革命后,我们听到了民粹主义的声音。1918年10月的《新青年》发表了“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第一篇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第二篇是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李大钊的“庶民”即平民,它鼓吹的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平民革命和平民政治。但蔡元培的演讲,视劳工为神圣(劳工既非下作亦非神圣),已然带有民粹色彩了,虽然文本中没有民粹这个词。这是平民主义向民粹主义的一个转向。
彼此因应的是,1919年鲁迅写出了他的《一件小事》,这个不像小说的小说放在《呐喊》中很像是一个例外,它是外在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精神氛围的。那个人力车夫是《呐喊》草根底层中唯一的正面形象,而且很高大;当然这是作者特意将叙述者“我”作为人力车夫反衬的结果。因此,这是鲁迅小说集中唯一含有民粹意味的作品。只不过它更像是启蒙者鲁迅的一个生硬的精神插曲;正如该小说的艺术性(其实是无艺术性)绝不能代表鲁迅的小说水平一样。
20世纪中国三大革命亦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除第一次辛亥革命外,都与民粹有关。1920年代中后期,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学校和书斋,有的从事工运,如邓中夏等;有的从事农运,如毛泽东等。广义地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运动,虽然“粹”的成分不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场运动有人认为“好得很”,有人认为“糟得很”,青年毛泽东是“好派”,他给我们这样描绘农运:
“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好得很”的农民运动,不但助成了当时的“国民革命”,更助成了其后的“土地革命”。
鲁迅在《一件小事》之后,又回到启蒙主义的创作道路,并写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第七章“革命”中,当革命的消息从城里传来,阿Q决定第二天就参加革命。这一天他喝了几两黄酒,回到土谷祠,倒头便睡。由于兴奋,一时没睡着,于是开始意淫。
先是想东西,当然不是“杀猪出谷”,而是“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接着想女人,还没轮到滚牙床,却开始挑肥拣瘦了:“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鲁迅毕竟是文学家,此时此地对阿Q的心理描写惟妙惟肖;但到底不若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从毛的角度,农民是巨大的革命力量。哪怕它有问题也无妨,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但是,转从鲁迅包括认同改造国民性的知识分子的角度,阿Q们糟得很,启蒙“正未有穷期”。
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历史就这样在启蒙精英和民粹精英中拉锯展开。很快,组织形态的民粹精英占据了历史上风,启蒙精英则一步步边缘化。1930-1940年代,民众已经广泛地动员起来。此时毛泽东从“民”到“粹”,开始对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的基本盘)讲话了。这种讲话是把自己摆进去的现身说法: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粹民粹,民究竟“粹”在哪儿,毛泽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民不会自以为粹,甚至民是不会说话的,它往往自己不出声。声音的话语权是在知识人那里,是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各路精英在说话,或代表它说——正如这次特朗普主要代表的是白人工薪阶层的利益,因此在竞选中说:我就是他们的声音。
今日中国已无民粹主义
视民为粹,并非毛泽东的创举,而是其来有自。它来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正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又远祖于法国大革命。我个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以来第一次民粹主义的表演,它和革命是捆绑在一起的。法国大革命又无法摆脱其精神领袖卢梭,而卢梭本人至少也是我个人眼中的第一个民粹主义者,尽管卢梭没用过这个词。
你看罗伯斯庇尔是怎么说的:“让-雅克(卢梭)公之于众的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即只有人民是善良、公正和慷慨的;腐败和独裁属于鄙视人民的垄断者。”(《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另一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生物进化论的先驱拉马克说:“富人和贵族们都在蚕食自由;他们却伪装成爱国者来欺骗人民。这个阶层出不了什么好人,只有在高贵的人民之中,我们才能找到最纯净、最热情、最崇高自由的精神。”(《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雅各宾》)
法兰西是民粹的故乡,又是革命的故乡。自它而俄罗斯而本土,说到底,都是知识精英运作的产物。没有知识精英,便不会有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同样,没有知识精英,也不会有启蒙主义运动。和启蒙主义是一种精英主义一样,民粹主义是另一种精英主义。如果细绎这两路精英间的关系,民粹精英其实是从启蒙主义分蘖而出的;而且它身上也并没有完全与启蒙切割。
青年毛泽东显然是《新青年》的读者,他还给它写过稿。那些年轻的北大学子如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无一不受《新青年》的启蒙影响,同时又随着后期《新青年》“美俄”的转化而转化,最终走上了民众运动的运作道路。因此,民粹精英虽然比启蒙精英晚出(前者往往还是后者的学生),但后来居上,其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吸附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1927年之后,鲁迅亦从启蒙主义出走,成了一个“普罗主义”者(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再强调民粹,但不妨碍他1950年代反向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相比较之下,启蒙主义单纯一些,民粹主义相对复杂。除了主义之外,它还有相当的政治策略的成分。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概括,20世纪的历史和思想史,虽然由启蒙主义开头,但却是后来的民粹主义主导了历史。它完败启蒙主义,启蒙精英因而成了民粹精英的输家。1949年后,毛泽东对民粹的经典表述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于是,我们不难理解1970年代电影《决裂》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只会教“马尾巴的功能”的知识分子。历史至此,当年的启蒙话语早已不复存在,那些可以担当启蒙话语的知识人早已被思想改造,甚至是主动要求思想改造了。启蒙精英在民粹面前可谓满盘皆输,无论是政治上、道德上,还是智慧上。他们必须低下头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接受后者再教育。
然而,历史到此为止了吗?非也,历史很会开玩笑。20世纪最后20年,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民粹主义悄然退出时代舞台。落败几十年的启蒙主义再度风光,扬眉吐气。1980年代被不少知识人称为“新启蒙”的年代。他们认为从五四新文化开始到现在,存在着一个长达六十年的“文化断裂带”,这个断裂就是启蒙的断裂。对此,李泽厚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内在地讲,压倒启蒙的其实还有民粹,后者委实更重要。
21世纪以来,局面又有变化,一些知识人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在这个年代的末期又被中断,因此呼吁“第三次启蒙”(可见知识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启蒙”情结)。这里不对启蒙作评价,只是想回应一下资中筠先生的问题。资先生不是希望用启蒙战胜民粹吗,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民粹主义了。道理很简单,启蒙在,民粹便不在。启蒙是专治民愚的,民粹还要启蒙干什么?今天有民族主义不假,甚至可能成为大患。但民粹主义更多是今天一些启蒙者因概念疏阔而树起来的假想敌。
最后,民、民意并非民粹主义。无论特朗普走白人草根路线,还是英伦公投主要仰仗一般平民,抑或埃尔多安政教合一背后的广泛民意,都不是民粹主义,而是普罗主义。
(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59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