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史源调查(代导言)
陈爽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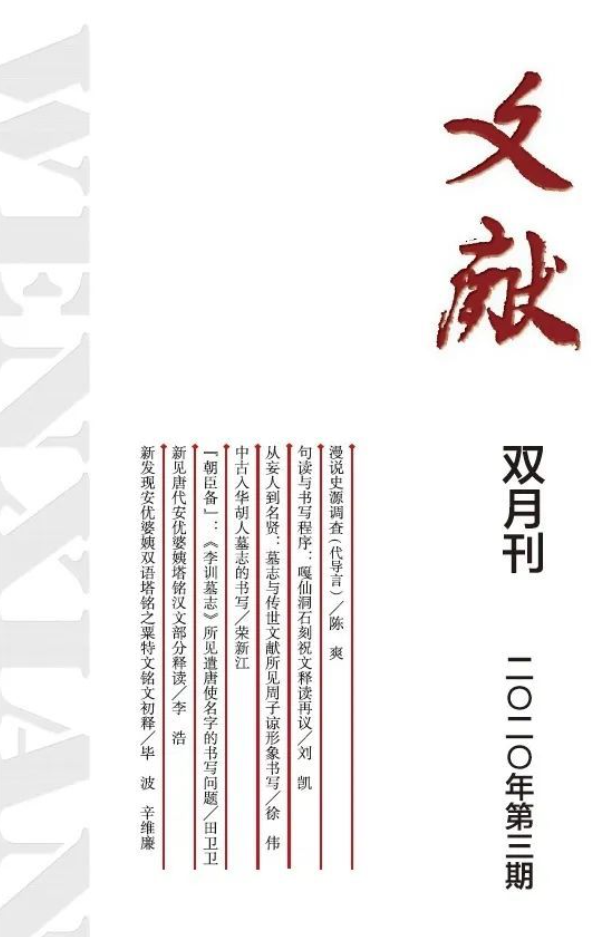
本专栏收录
8
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论文,时间跨度从南北朝至明代,涉及史料体裁包括了官私史著、文集表奏、碑刻墓志等,虽考察对象不一,切入角度各异,基本都是以史料的文本辨析为手段,以探究史源、明晰流变为旨趣,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文献研究的新取向。
一、采摭旧文:传统史籍中的源与流
重视史源,强调史料文本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是当今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的共识;但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撰述却往往并不讲求所谓的“原创性
”
,通过“采摭旧文(闻)”的方式,不做说明地抄撮转引乃至删削修改其他史传中的文字,是司空见惯的寻常操作。在传统史学观念中,也没有明确史源的观念,只有所谓“文士之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史体述而不造,史文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的说法
[1]
。
“述而不造”,是恐“言之无征”,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史料原始信息来源极为有限,且主要垄断于官府。古代从很早就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史官建置,形成了持久的修史传统。编纂史书的主要素材,包括政府的诏令和律法、帝王的起居注和实录、朝臣的行状和奏疏等,均为政府严格控制和管理的官方档案文牍,藏诸兰台秘阁。古代以私人名义撰写的诸多历史著述,作者大多有担任史职的经历,或者担任过可以接触官方档案的高级官吏;除此之外,普通士人很难不依赖官方档案而进行独立的历史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对于私家著史的限制最为宽松;这正是史部书籍在此后不久即获得了目录学上之独立地位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梁才子吴均欲“著史以自名”,向梁武帝上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予,下诏敷衍:“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后来吴均果然“自搜访”而撰成了《齐春秋》三十篇,却因直书梁武帝在南齐为臣时助纣为虐的劣迹,“帝恶其实录”,其书被焚毁,其人被免职
[2]
。与此相伴随的是,受史料来源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私家史著的题材和内容受到极大限制,或旁采掌故逸闻,风土人物自为一说;或抄撮和剪裁旧有文献,别为新书。这类在王朝正史体系之外的史籍,通常被归入杂史,甚至被斥为稗官野史,难以从结构上动摇王朝正大的历史话语体系。
朝廷对于官方档案文献的垄断和控制,也使得大量的原始史料处于高度危险的“孤本”状态,每遇王朝更迭、战乱兵火,原始史料的整体性散亡和佚失往往不可避免。所谓“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
[3]
,不过是史籍修纂的理想状态。无论朝廷首肯的官修私撰,还是朝廷史馆中的集体撰修,每每苦于前朝文献无征,只能以采摭旧文的方式,附益杂糅,连缀成篇,而因拼接不当造成种种疏误,也就在所难免。
以《梁书》和《辽史》两部正史为例。据庄芸《〈隋书·经籍志〉所见萧梁旧史考略》一文考证:梁代江陵政权覆亡之后的撰述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多部专门记录梁代丧亡的史书。姚思廉采诸家旧梁史以补其父姚察的书稿,参考了诸多萧梁旧臣的著作,却未能协调好史书间的矛盾记载,造成《梁书》存在若干处前后抵牾。如《侯景传》前载“张彪起义于会稽”,后又称其“寇钱塘”,立场全然不同,显然是拼合史料而又未加整饬所致。如果说《梁书》中的前后龃龉不合、文本错乱仅仅是局部的疏漏,那么《辽史》的编纂所造成的谬误则可能是全局性的。苗润博《〈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一文的研究表明,今本《兵卫志·兵制》实际上是元人对源出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原始资料加以拼接、杂糅的产物,使得某些本属“南朝异邦”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的常制,“结果看似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却会给后世读史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和误导”。此文虽是局部个案的研究,却足以提示读者对《辽史》记载之真实性当给予更高的警惕。
在史料传承和文本转移的过程中,与抄撮旧文、拼缀杂糅相伴随的,是对史料的不当删削。在古人的“良史”观念中,“信史”并非唯一的标准,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古人对于一部史著的评价标准,通常并不在意其史实如何准确可信,而是侧重其史论是否精彩,叙事是否精炼,文字是否顺畅。唐刘知幾言:“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4]
明人胡应麟甚至极言:“文之繁简,可以定史之优劣。”
[5]
在崇尚“文约而事丰”的理念之下,“采摭旧文”的过程,不仅是在做加法,同时也在做减法,而这种删削往往是极其危险的操作。史籍中的文字承载了具体的史实信息,为追求文字简洁和行文便利而进行的文字删节,往往会破坏史实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不当删而删、因删而致疑、因删而致误,带来“一字之误亦有可疑误后人”的恶果
[6]
。以古来被史家所广为称道的“南、北史”为例,删削后的内容仅有原南北朝“八书”总和的二分之一,除了删除一些重要诏令外,还批量删除了北魏早期部族内属记载、批量删削传主的“起家官”等。若非“八书”尚存,这可都是灾难性的史料损失
[7]
。而这种“规律性删削失当”,普遍地存在于历朝历代各种体裁的史籍当中。
中国传统史学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缺乏史料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而古人对于所谓良史的评判主要出于历史编纂学的标准,而非史料学的标准。由此而造成的古代历史文献间复杂的传承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真伪就能够解释的;仅根据史籍的成书年代先后,也不能准确地判断具体史料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我们必须深入史籍内部,对文本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方能追根溯源。
二、探求史源:文献研究的学术转型
众所周知,在现代史学范畴中,“史源学”概念的提出,始于陈垣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末,陈垣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程。“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儆惕著论之轻心”。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经验,强调引用文献的基本原则——尽量使用成书时代早的史料:“凡《宋书》有者,不引《晋书》。论朝代,晋在宋前;论成书,则《宋书》在《晋书》前,《晋书》为唐初所修也。”“史源学实习”虽主要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课程所选择的主要文献材料也并非一手史料,而是《日知录》、《廿二史札记》这样的考据性史著;但“史源学”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史学和现代历史科学研究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8]
如果说“史源学”概念在理论上的提出始自陈垣先生,那么在中国史学界,以现代史学方法进行史源调查的实际操作,从
20
世纪初即已开始,各种探索和尝试百馀年来不绝如缕:如冯家昇、陈述、傅乐焕等先生对辽金史源流的考索,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二史八书校刊记中对各史文本承袭关系的条辨,余太山先生对汉魏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史源梳理,吴玉贵先生对《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与唐实录关系的推断,陈勇先生对《资治通鉴》所引十六国史料的史源分析,都为学界作出了垂范。
近年来,无论是在文献研究还是史学研究领域,“史源”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代学术研究中“史源调查”的勃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动因:
动因之一,古代史料的相对匮乏和不可再生性,使学界产生深度挖掘史料的需求。史学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相关的研究便面临着“增长的极限”。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史料文献分布本来就不均衡,并非简单的时代愈后史料愈丰富;而过去百馀年间,以考古新发现为主导所产生的史料新发现,又极大地改变了古代史研究各断代的史料矿藏分布比例。在某些较为幸运的断代史研究中,新出文献层出不穷,可以通过消化新资料获得新知新见,实现稳定的学术增长;而在另一些断代,史料资源仍极度匮乏。刘浦江先生曾经提出,辽金史研究出路之一是要“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对于辽金史研究而言,除了发掘新材料之外,那些为人熟知的常见史料亦需加以深翻和检讨,追本溯源,订讹补阙,为学者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并使其焕发出新的学术价值”
[9]
。
动因之二,研究视角的转换所导致的史学观念的更新,为史源调查明确了方向。近年来,受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在研究中古史的青年学者中异军突起。他们利用文本分析等手段,对现有史料进行系统辨析。这种辨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考辨,而是对所谓一手史料的构建过程进行研究,以疑古的态度,对史料文本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审慎,主张对关键史料的来源进行深入解读,从多个角度反思史料,考察史料文本背后的深层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史料的再阐释与历史图景的再构建
[10]
。“由这个立场出发,可以认为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
[11]
动因之三:古籍的数字化为史源调查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普及,学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籍文献的大量扫描影印刊布和数字化传播,使得众多珍本秘籍成为学者的案头常备之书;而古籍全文检索的实现,则改变了传统学术靠记诵和个人资料积累的工作方式。古籍的数字化,使得穷尽史料,竭泽而渔这一理想成为可能,“说有易,说无难”不再是论证的难题。很多前人穷皓首之功难以完成的琐碎浩繁的文本比对,可以通过数字化处理高效而准确地完成。
三、正本清源:史源调查的工作旨趣
通过本专栏的诸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一辈青年学者手中,“史源调查”已经从辅仁时代的史学入门技能,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利器。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总结,史源调查有一些不同于以往传统文献研究的特点和工作方式:
其一,史源调查具有明确的历史学问题意识,研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史源调查对传统历史文献的处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从以文本校订和诠释等方式机械地、按部就班地、被动地整理史料,转变为主动挖掘史料,更深层次地阐释史料。如刘凯《句读与书写程序:嘎仙洞石刻祝文释读再议》一文,从文本层次最基本的“句读”和“书写程序”入手,纠正了被前人倒置的嘎仙洞祝文与《魏书·礼志》的史源关系,并以文本的改易为基础,探讨北魏早期的礼制变迁,再现历史场景。张良《高斯得经筵进讲修史故事发覆——兼论〈中兴四朝国史〉的成书时间》一文,具体考证还原乾隆年间馆臣辑佚、整理、编订高氏文集的流程,并在此基础上梳理高斯得论史奏议的文本源流,框定上书时间,从而为廓清《中兴四朝国史》修纂的真实面貌提供文献与史实的依据。李京泽《汪藻〈裔夷谋夏录〉再探》一文对这部记载辽宋金易代史事的重要文献的精细化再解读,厘清了书中所记各节的史料源头,也辨明了出自汪藻本人的史笔。
其二,史源调查以细致的文本比勘作为最基础的研究手段,选取文献往往是跨断代、跨文体、跨介质的,是多种文献学技能,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传统文献学技能的综合运用。如果说传统史源的调查主要依赖于学者的博闻强记和洞见卓识,结论多为推断性,失之模糊和笼统;那么,新的技术手段下的史源探究主要依靠扎实、细致的文本比对和具体而微的分析考证,结论务求准确而翔实。与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解题不同,史源调查需要深入到史籍内部,逐卷、逐段乃至逐字地进行文本比勘,通过文字的雷同程度发现文本间的史源关系。如苗润博《〈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陈佳臻《〈析津志·名宦〉史源考——兼考元初中书官员刘肃的官职》、邱进春《明洪武二十四年榜进士辨正——兼论洪武三十年春榜名录》等文章中,都有大量翔实的文本比对,通过对数种同源文本或“平行史料”进行细致对勘,梳理有承继关系的史料群中的相关文本,尽可能追溯其祖本,探知传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讹误。这种工作虽繁琐而艰辛,结论则往往准确可靠而不易动摇,为后继者节省了大量的考据成本,达到了陈垣先生所倡导的“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目的。
其三,史源调查既讲求正本清源,也重视文本流变,重视考察文本传承和变迁背后的历史动因,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作出阐释。“相互矛盾的史料可以看作是不同历史叙述长期竞争的残迹,对这些历史残迹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地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