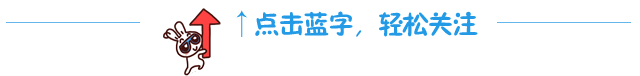

2017
年
12
月
22
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周其仁
李志轩提示
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国处理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
5
块人民币,据说当时
5
元钱可以买
40
斤大米、
7
斤猪肉。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伊拉克蜜枣的特点是:
1.
实行市场经济,随便买;
2.
价格高,回收量大;
3.
有钱的,多买,等于向高收入家庭收了一道“通胀税”;
4.
没钱的,少买或不买,反正蜜枣不是必需生活品,吃不着也没啥不满。
再看现在的房地产,其特点是:
1.
体量够大,据估算,中国房地产市值约为
270
万亿元人民币
,
为
GDP
的
4
倍
,
股市的
6
倍;
2.
易于管控,限购限售限贷限房价限面积,进去的出不来,出来的进不去,流动性易控;
3.
房价长期上涨,为获得财产性收入(就是躺着挣钱),人们争着抢着借钱也要买房;
4.
卖地收入归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债务危机;
5.
房价上涨,控制好二套房、三套房的银行按揭,可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由于房地产体量、安全性和管控性的优势,最终成为了我国疏导超发货币的蓄水池和分洪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可能是在政府为了防止全面通胀,又不能实施全面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的情况下,主动网开一面留个破绽,将房地产市场变成了巨型的伊拉克蜜枣。
与伊拉克蜜枣相比,蜜枣吃完,吐个核,咂咂嘴,就没事了。而房地产的处理,估计就要通过房产税这个杠杆来调节了。
以下为正文
原标题:
“
伊拉克蜜枣
”
与治理通胀
——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
该文刊登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经济观察报》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
但是,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流行之见,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来来回回是一回事。
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结论。不是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商品与服务,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拥有的货币资产别无他用,主要就是用来花的。可是在通胀环境里,钱多商品少,人们一起花钱势必抬升物价,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不但显示出通胀,还会加强通胀预期,进一步鼓动人们购买商品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物价。
一个办法是加息。
讲过的,那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
1988
年大陆通胀高企之时,有重量级智囊到香港向有关台湾财经人士问计,对方的经验之谈就是大幅度加息。说
“
利息不管用
”
,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利息岂能不管用?
问题是加息要产生其他代价。
譬如当下的情形,中国加息将进一步拉高与欧美日本息口之间的差距,结果
“
钱往高处流
”
,进入中国的货币老虎不小反大,令人头痛。还有加息会冷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多人是不是承受得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现实世界,加息不到位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办法,是管制物价。
直接管价,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横竖
“
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
”
是自古以来的现成罪名。虽然经济学家从斯密以来,支持直接价管的少,批评的多,但到了风口浪尖的关头,无论东方西方,执政者多半不加理会就是了。一个原因,是公众也常常支持价管,或干脆要求价管。这是价格管制挥之不去的原因。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
“
管理需求
”
。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说的是,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可以达到限价的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得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
“
撵
”
向另外一个商品。忙来忙去,把整个物价水平都运动上去了。
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追根溯源,通胀还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
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
“
平稳
”
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
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
“
漫游
”
,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换个角度想问题。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只不过
“
反映
”
通胀,其本身也会
“
释放
”
部分通胀的压力。先这么想吧: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人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
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是不是就
“
消停
”
了?
有读者会说,那可不一定。买家付钱持物,那卖家不是正好倒过来,售出物品、收回货币吗?那些卖米、卖面、卖车、卖房的,他们收到了钱再花出去,存量货币资产继续流动,市场里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减少,买方以货币购买力压迫物价上升的压力岂不是依然存在吗?
好问题,终于点到了货币的迷人之处。
货币(
currency
)者,流通之中的钱是也。所以货币的显著特点是不断地在市场里转。买家付账、卖家收钱,完成一次流通。轮到卖家花钱的时候,他又充当买家,付出货币得到商品,钱又完成一次流通。如此生生不息,钱在市场里不停地打转,协助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生产体系实现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不断换手。
明白了这一层,再深想一个问题吧:
当货币不断在天下无数买家卖家之间转来转去之际,是不是存在某种可能性,
那就是处于某个流通环节的卖方,收入的货币很多,再花出来的钱却很少?
这一多一少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是可能暂时地、甚至永久性地退出货币流通,以达到让货币老虎
“
变瘦
”
,从而根本降低市场的通胀压力?
让我以经验来说明,这样的
“
好事
”
还真的是有的。
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故事,我在上海读小学、升中学。记忆之中,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诱惑。
那是
“
三年困难时期
”
,粮食和副食的供应极度紧张,政府松动政策,允许
“
自由市场
”
开放。于是通向学校的街道两侧,摆满了各式食品摊位。
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价钱不菲,比凭本计划供应的,要贵上很多倍。
可惜家母教育孩子的准则,是从来不给零花钱,惟有她认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拨款。这样,我对路边诱人食物的需求当然
“
刚性为零
”
。好在家里还有网开一面的地方,就是把伊拉克蜜枣装在大口瓶里,锁在柜子之中,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我几个过过瘾。
那时的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
5
块人民币
——
那可是
1960
年代的
5
块钱!
后来读《
陈云
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
60
年代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
陈云同志说
,
“
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
。
(《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7
页)。
这里的
“
几种高价商品
”
,也包括本文作者当年吃一个就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计划经济也有通货膨胀吗?
有的。成因也一样,
“
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
”
。
当时钞票多发的原因,是
“
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