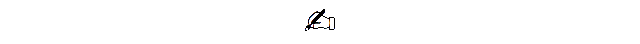

白石洲城中村“农民房”林立,同不远处的别墅群形成鲜明对比。 视觉中国 资料
密密麻麻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的楼。不少楼间距只够一个人通过,从楼里伸出的电线和网线在楼外缠绕交错,纠结成半空中的一片蜘蛛网。
距离深圳“世界之窗”——一个知名的微缩景区不过一两公里,网约车司机柳庆租住的城中村白石洲是另一个世界。

在白石洲,许多招租信息就张贴在门口。以下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这里有深圳规模最大的“农民房”。根据2015年的调研数据,白石洲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下了2527栋出租房,有约14万人在此生活居住,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为12万人。
南北纵跨深南大道,西至沙河东路顺接科技园,东连华侨城、世界之窗、欢乐谷——如果从空中俯瞰白石洲,它像是前述深圳地标建筑包围中的“塌陷区”。就在两个月前的9月底,不远处的华侨城一处新楼盘卖出“总面积6平方米,单价15万”的“天价鸽子笼”,事后该项目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深圳市规土委责令整改。

白石洲内的公共区域很少,江南百货门口这片空地成了许多孩子的乐园。
在来到深圳后的第19年,柳庆凭借计算机高级职称申请到本地户口,他希望接下来申请到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一套保障性住房;“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和朋友合租一套农民房的小白领傅俊正为租住一个环境更好的小区而奋斗,在房租再次上涨500元后,他决心“再涨一次我就搬!”而从四川老家来到深圳六年的清洁工李阿姨,在高企的房价前从没想过在深圳安家落户,“打工打工,再怎么,你最后还是要回去的。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第36周年。过去三十多年,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曾聚集此地,用青春、智慧、勇气和汗水缔造了“深圳速度”和“财富神话”。作为关内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地,白石洲正是许多人“深圳梦”开启的第一站。
9月,外媒报道称,美国经济咨询公司Longview Economics一项研究显示,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站在36周年的尾巴上,深圳之于外来者的问题是,这座曾以“包容”著称的城市,如今是否仍向他们敞开大门?
老房东,老房客

沙河街上的人流。
晚八点,沙河街灯火通明。
服装店门口的小妹拼命摇晃着塑料手,清脆的“啪啪”声在一片喧嚣中甚为清晰。发传单的小哥左挪右腾,稍不留神就撞个正着。旁边正吆喝着叫卖袜子的大姐可能会扶你一把,顺便问一句:“丝袜十五块两双,要吗?”
街南端的“湾畔百货”,和“江南百货”并列为白石洲购物“两大圣地”。一个小时前,这里正对的白石洲地铁站A口每两三分钟就出现一片密集的黑点晃动着蜂拥而出,接近出口时化为行色匆匆的人群,浩浩荡荡上了沙河街,最后流散入转角处横七竖八的小巷。
柳庆(化名)在巷子里住了近二十年。这里楼挨着楼,室内光线昏暗,加上室外密如蛛网的电线网线,显得加倍压抑。
柳庆给不少租户拉过网线,收费比运营商便宜,挺受欢迎。晚上十一点多,他坐在楼下朋友的店面里,对面麻将馆还有人跑出来找他:“哎,刚好!给你把网费交了。”
其实他的“正职”是网约车司机。每天早晨7点起床后,他给孩子做早饭,送上学,然后就去跑车,一直忙到晚上9点。深圳户口是三年前凭着计算机高级职称申请到的,妻子的户口也随迁,孩子因此得以入学。
“刚好赶到好时光了,不像以前办暂住证都很难的。”柳庆说。一条小黑狗在他脚边摇着尾巴跑来跑去,他笑笑把狗赶开:“别怕,这是我朋友养的,不咬人。”
“朋友”是他聊天时常冒出的词,包括早年教他架设服务器拉网线的IT人士,一个做装修起家做出了口碑的老板,一个在白石洲里开小旅馆的生意人,一对从梅州来的客家夫妇,对面麻将馆的老板娘,以及附近住了好几年的老住户们。
“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这么多朋友。最难过的就是还窝在这儿(白石洲),也没混出多少出息。”回顾来深圳的二十多年,柳庆感叹道。他的老家在湖北农村,1994年经老乡介绍,来到深圳打工:“(老乡)他们回老家的时候经常说嘛,都说深圳特别好。”
柳庆南下深圳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汹涌的打工潮。那一年,《春天的故事》刚刚被写就,歌词里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深圳经济特区,在第一批南下的人眼中,像是黄金遍地的热土。
对本地人,那也是一个变革的年代。
尽管建立特区仅30余年,但深圳的人类活动史却有超过6700年。这片临海之地曾是夏商周时期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驻脚点,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以捕鱼、航海为生。在后来1600多年的城市史中,历经时代变迁,深圳也只是人口规模几十万的小县城。
1992 年,《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将特区内原农民全部一次性转变身份成为“城里人”。至2003 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转化为 27 万城市居民,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转为国家所有。
此间十余年,塑造了如今白石洲的形态。“建房子最早是80年代,改革开放嘛。比较大量和集中(建房)就是90年代末和2000年左右,五湖四海的人来了,外地人口增容有(住房)需求嘛。农民也没有地了,要依靠出租来生活。”吴子仪说。
吴子仪是本地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白石洲。如今,他在白石洲村拥有一个小庭院,里面四栋楼,临街一栋粉红色的有七层,2001年在原二层小楼的基础上改建。小楼80年代初建,就在鱼塘边。“第一批建的房子从来没想过出租的,都是用来改善自己家生活的。”他说。其余三栋于1992年和1996年前后分两拨填塘兴建,都只有三五层。
房子建好没多久,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的定位从特区设立时的工业出口产业基地和新型边防城市,逐渐向具有全国意义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与香港功能互补的区域中心城市转变。土地出让、转让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同时进入加速轨道。
白石洲仿佛城市中的一个岛屿。商业综合体、高层写字楼、高尔夫球场、花园小区公寓……不同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将这里包围,城市在扩张中挤压了村民的生存空间,却也让他们看到了致富的新出路:建房。
1999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启动了大规模违法建筑拆除活动,违法建筑里的居民失去居所,相反城中村私宅出租市场的需求量上升。生计变谋利,白石洲“抢建农民房”的高潮期到来了。
“大家都觉得只要建了都能租出去。家家户户都在抢建,实际上是不好管。”吴子仪说。他形容当时的情景“也是很艰难,像打游击一样”:总有人来查,但管了东边管不到西边。停水停电的举措也常有,还是挡不住大家先把新楼地基打起来的热情,政策稍微松懈或是一个长假之后,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头。

由于楼间距过窄,白石洲的农民房被称为“握手楼”。
新建的楼大多在七层以上。为节省土地,建筑间距被牺牲,“握手楼”因此形成。平面设计上,两室或三室的房型也不再适用,单户或一室一厅更多,一层可分好几间单独出租。
“我家就因为以前是鱼塘,别人圈不走,所以还比较宽敞。”吴子仪的四栋楼间距宽、能透光,地面也干干净净,按一楼租户小叶的话说:“和其他农民房比起来太舒服。”吴家的小庭院里几十家租户,他每月房租收起来有六位数。
深圳市规土委资料显示,白石洲自2014年就已列入城中村(旧城)改造范围。从实地情况来看,已有两个工业区被拆除,但大部分的民居还未动工。

沙河街上的宣传条幅。
吴子仪是赞成白石洲改造的,觉得这里脏乱差、没有规划:“能(改造)升级就升级,不能升级的也就转型了,其实就是一种规律嘛。(租户)没有这种条件就去别的城市啊,惠州、东莞相对又可以成本低一点,现在珠海那边不是也慢慢发展起来了?”

沙河街靠北一个小区内,月租金700元的隔断间。
柳庆不知道产业升级会不会把自己抛下。他1998年搬到白石洲,两年内从石棉瓦房住进了“握手楼”,再一住就是16年。起初因为没有暂住证,总要东躲西藏,开的旧货买卖铺也总被警察查。“收容所我进去过三次。”他说。
再混不好,毕竟也生活了二十多年。全家都已是名副其实的“深圳人”,柳庆希望能赶在白石洲改造完成之前,申请到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不过我房东的爸爸七十多岁,我上次问他,他说,在他活着的时候,白石洲估计是拆不掉的。”
转瞬间他又犯愁起来:“我有个朋友,申请了三次(保障性住房)都没申请到。系统里怎么个算法也不知道。他都有十多年的社保了,我社保才交了六七年,希望不大吧,唉!”
黄金年代的打拼者

白海彬在挑生蚝。
32岁的白海彬提着大麻袋在批发市场中走来走去挑选生蚝,黑色尖头皮鞋在满地的污泥里显得锃锃发亮。
“哐!”一麻袋生蚝扔进他那辆白色商务别克后备箱,白海彬转头笑笑:“自己做生意嘛,就是这样子。”他的餐厅开在白石洲,最近刚开始卖烧烤。开车回去的路上他的手机响个不停:有前妻的,有同事的,有帮朋友问事儿的,还有一位姐的儿子过生日,催他帮忙取蛋糕。
“深圳是个没有距离感的城市。情谊呢,比我家乡好太多。”他说,朋友们没事从来不打电话,有事打电话也不客套,直说事儿,看似无情实则务实,他很喜欢。儿子过生日的这位姐就是他做小区保安时的一位业主,曾想带他出来做保险,后来也帮过他不少忙。
13年前,山东人白海彬来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小区保安。那时,有业主劝他,在小区做保安没前途,又帮他找了附近五星级酒店的工作。后来,一步步地做,他做到这家五星级酒店的安保总监,如今出入都是身材板正、西装革履,正职外他还在白石洲开了家餐厅。

白石洲的夜市摊档从晚上六点开始陆续摆出。
“如果去做了保险,可能又是另一个状态。那时候做保险的现在都发啦,好几套房的都有。”白海彬说,在深圳13年却没有早买房,是他最大的遗憾:“肠子都悔青了。”
和白海彬不同,与他同一年来到深圳的房产中介杨善庆已经买下了两套房。
杨善庆来自安徽,精瘦,皮肤黑黑,身穿一套不起眼的短袖和中裤,单肩背着红色的双肩包,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这边刚好有个客户之前要看房,我先问问看她在不在啊。”
2005年,在深圳一个小区做了两年物业后,他跳槽一头扎进了房产中介行业。2009年,他在距深圳90多公里的惠州买了一套房,每平米两三千元;2011年他又在深圳买了一套,时价一万出头。如今两套房价格都已翻了四五倍,“跟我一样做房地产的,谁身上都有两套房”,他说起来却是云淡风轻。
深圳的房子买在南山区的繁华阶段,杨善庆以6500元每月的价格出租掉。他自己则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在白石洲租了套两房一厅的小区房,月租4000元。差额刚好用来还房贷,杨善庆的人生字典里暂时还没有“享乐”这两个字:“以后当然要享受,现在年纪轻轻的,享受什么?而且钱花光了就是花光了,没有了,要拿去生钱(才对)。”他一脸严肃地说。
其实他已经年薪百万。近两年深圳房价暴涨,他手上去年卖出近40套房,佣金就赚了好几十万。前几年和朋友合伙投资的两套房也卖出去一套,分下来每人又净赚几十万。“去年过年的时候不得了,天天看房,电话打爆,关机了!没电了,关机了!我有充电宝,我两个手机都打关机了!”他指着自己红色双肩包里翻出的两个手机说。
杨善庆喜欢深圳,在他看来:“北京尘土太大,租房子压力也大,地下室不透气很难受;上海冬天好冷又没暖气;广州治安感觉没有深圳好;深圳呢,气候宜人,去香港方便,海边多也适合居住。”
“关键是一点也不排外,这是很主要的原因哦,你只要肯吃苦你能赚很多钱,真的,多劳多得嘛,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机会都是有的……打工我觉得也挺适合的,确实发展快,各行各业的门槛也很低的,它不是很看重你的文凭,做房地产也是这样子的。”
杨善庆初来深圳的那几年,房价还没有涨起来,生活成本也不算太高。在同时期进入深圳的白海彬眼里,深圳是一个只要有想法、有行动力,就能出头的地方。
2007年,白海彬的妻子生孩子后辞了工作,夫妻俩每天五六点起床,到沙河医院门口摆摊卖豆浆,九点他再去酒店上班,一个月下来,赚的钱抵他在酒店工资的两倍多。不过因为总被城管查,三个月后不了了之。
他闲下来,又跟着酒店的老板一起炒股票,工作和摆摊赚的二十万投进去,赶上北京奥运前后的牛市,眼见着数字涨到四十万、六十万,最后变成了八十万。白海彬很是摆阔过一阵,谁料后几年后股市低迷,百万家底一夜缩水,连本钱和工资都搭了进去,他刷爆信用卡又贷款补仓,一时间压力剧增。
一咬牙,他注销了所有玩股票的账号,和已分居的前妻在白石洲开了一间小餐厅,做晚餐和夜宵。每日从酒店下班后就匆匆来看店,一直做到深夜。一天睡三四个小时,血压就上去了,低压120,比正常人高压都高。
起初每个月流水20万却还在亏本,后来发现是被请来的厨房班子坑了。2016年春节后,店关了整整一个月,前妻带着新请的厨房班子专门去武汉学做小龙虾,调口味的时候他吃小龙虾吃得都想吐。好在夏天生意火,住华侨城附近的有钱人开着豪车到店里来,两人一桌就能消费一千多。三个月,一年的本钱便赚回来了。
白海彬打算,今年帮前妻把餐厅左右两边的店都盘下来扩大规模,之后自己再去开一家新的。合伙人已经找到,正在筹备中,目标是三年做到一百万:“现在还年轻嘛,再撑个两年还行。……高血压啊?也没办法,深圳这个地方只能这样子啊。你算算,我1984年生,现在都多大了?再不折腾就晚啦!”
当白海彬计划着三年折腾出一百万的时候,杨善庆的财富目标已多了一个零。
经历了几轮市场动荡,如今身处行业顶端,杨善庆自我总结:“坚持时间长的都是精英。”他说,房地产销售行业,每逢政策调控就“不开单”,新人生存难,总要淘汰一批,像他这样年限长、有家底的才熬得过去,但市场总体还是火爆的。
乐观之后,他又觉得深圳房价快到顶了:“再涨关键是打工的人承受不了,房子也租不起,买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就凭你那工资……一句话,绝对买不起!你想嘛,零几年到现在,从几千到几万,翻了十几倍了。”
新移民们的未来
早晨八点半,209路公交车缓缓驶入白石洲站。等待的人骚动起来,距离远的以百米速度赛跑,距离近的呼啦啦围了一圈。车门开,人群蜂拥而入,直到前后门的上下客区也留不下个落脚的地方。后面人胳膊顶着前面人的肚子,最外面的像耍杂技般一手拽着包一手够着栏杆,勉强扒住保持平衡,等车门蹭着后背艰难地关闭,晃晃悠悠开出去。

早上八点多的209公交车。采访对象供图
傅俊举起手机默默拍了一张照,附上评论:“又没挤上去。”他决定明天开始骑自行车上班。
早年白石洲只有一个公交站,后来政府下大力气整治,设置三个站台分流,加上地铁开通,已经好了很多。如今开往科技园方向的车不少,但傅俊的公司不凑巧,只有一辆209路经过。
起初他还七点半出门,后来就晃晃悠悠拖到八点十五——反正去早了,前两三趟也还是上不去。好在九点半前到岗即可,他还来得及。
早上九点之前,李阿姨就要完成科技园写字楼里的清洁工作了。她是吴子仪的房客,住在小庭院最里面的铁皮顶平房,月租 800元。“涨哦,越涨越贵。”她小声抱怨。又补一句:“别的地方也涨。”她说,“老板还算是公道。”

李阿姨住的屋子是铁皮房顶,夏天非常热,衣服挂出去也是半天就干。
“老板”是住客们对吴子仪的称呼。吴子仪有一个住户们的微信群,发放各种通知、活动信息,管理得像个小社区。周五傍晚从学校接回上高三的儿子,他到平时收房租的屋子里摆功夫茶,看到李阿姨,招呼一声:“进来嘛,进来喝茶。”李阿姨站在门口犹疑半天,坐下笑笑:“不好意思,喝老板的高级茶。”
六年前,李阿姨经老乡介绍从四川老家来,除了清洁工作,还负责为附近一家美发店做午饭和晚饭,顺带洗毛巾。两份工作加起来,每个月有四千元左右收入。她很满足:“反正在家也是做一天吃,在这儿也是做一天吃,都一样。”

李阿姨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为美发店的小姑娘们做好饭,分成十几份送去店里。
比起十年前在家里务农,她说如今的工作还算轻松,每天下午和晚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前几年,她和丈夫靠打工赚的钱在老家盖了房,每年春节都回家过年。她挺喜欢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对,都这么说,挺好的。” 但落户、买房这些事她从不敢想,那是“城里人担心的事儿”: “打工打工,再怎么,你最后还是要回去的。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傅俊调侃。在这个年轻人眼中,他租住的白石洲就三个字:“脏、乱、差!”平时和朋友出去散步,他们都是沿着深南大道往华侨城的方向走,走到欢乐谷,绕一圈,再回来,从不在白石洲里面逛。
在傅俊看来,白石洲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他和两个朋友合租两室一厅的农民房,共摊2800元的月租金。他现在拿五六千的月薪,打算等薪水再高一点,就搬去环境好一点的小区房。
作为创业公司的高管,曾峰现在的月薪是两万,但他还住在白石洲的“握手楼”里。两室一厅的房子,一室放着房东的东西,另一室被曾峰转租出去,他自己住客厅的位置,靠窗一张床,电脑和水果摆在一米宽的书桌上,加上两把小椅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老婆来看过他一次,心疼他过的辛苦。他倒无所谓:这屋子虽然旧但还干净,楼层高所以不吵,比起二十年前刚毕业五六个人住一间房的时候好多了。
曾峰是江西赣州人,在传统服装行业从底层开始一步步做到经理。去年在网上看到深圳一家服装公司招聘高管,本以为是行业内一次普通的跳槽,后来发现自己居然进了一家做“智能硬件”的创业公司:生产全部自动化,由机器代工;设计除了有设计师外,还可以由用户在app上根据基本款式自行搭配定制。
从江西到深圳,年逾四十的曾峰跳槽后像是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周末出门散步路过科技园,一排排高新科技企业的办公楼让他忍不住心生感慨:“我们看的电视、(电子科技)产品就他们研发的哦,是不是?(以前)就是你没看到这种风景和这样一种想法,那你站到越高的时候,(就知道)哇,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的。”
他此前从没想过创业,笑称自己没有爱拼的感觉,只想要保守一点——万一亏了怎么办?经过新公司的洗礼,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假如说某一天我失业,我可能会借一笔钱,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他说起前一个同租室友,也是像傅俊一样刚毕业的小白领,薪水一涨就搬出了白石洲。曾峰说,他这个年纪的人跟“90后”的处境不同: “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读书啊,还要养老人,对不对?以后自己养老也要考虑。”他每个月工资除了约四分之一的必需开销,和给上大学的女儿一笔生活费,余下的他都会攒起来。
曾峰在老家县城有一套房,妻子儿子都在那里,深圳只是他工作的地方。他说,年轻人不一样,公司里有个产品经理,每每准备下手买房,房价就又涨了:“我就说你不要在这里买啦,买到东莞、中山去。不行,他还是在深圳有一个创业的梦想,还想在这里扎根。”
其实,傅俊也想在深圳扎根。当初若不是朋友怂恿,他应该还在厦门远方亲戚开的公司里做销售。可他不喜欢,人家一鼓动便索性辞了职,揣着4000块钱就来“投奔”。
两年内傅俊换了三份工作,原因分别是“试用期最后一周,被告知项目也完结了没有新项目”、“应聘的运营岗最后发现又要承担销售任务,实在不想做”和“公司烧完了天使轮的钱,没续上A轮”。
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一度全身上下只剩两百块钱。偏巧遇上发高烧,医生说要打吊针,医药费要两百五六十元。傅俊问医生:“我先付一针的钱,打一针行不行?”一针140元,当天高烧退下去了,他就没去打第二针。
即便是这样,他也没后悔来深圳,更没想过要回去:“如果我没有来,混好混坏就那样得了。但是我来了,混不出个样子我不会回去。”
傅俊说,深圳是个见世面、拓视野的地方,高中校友群700多个人,逛“知乎”也认识了不少“知友”,这两个圈子隔三差五的聚会让他接触了不少相对年长和有本事的人:“要是还在老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他的计划是,等月薪达到三万的时候,就在深圳买房;但如果35岁之前还买不起,大概就只能回厦门。
“月薪三万,35岁之前买房,你觉得是有可能实现的吗?”
“月薪三万在深圳,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能不能在35岁之前买房就不知道了,毕竟房价也在涨。”他嘻嘻哈哈地笑了:“但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对他来说,白石洲只是个过渡。如果最终回了厦门,深圳或许也是漫长人生的一个过渡。但无论如何,一段青春奋斗的日子,总是值得。
每个周六的早晨,傅俊都会去楼下的肠粉店叫一份五块钱的肉蛋肠粉。老板是一对潮汕小夫妻,见他来,熟络地打个招呼,端一份上桌。“汤不够,太少啦。”傅俊理直气壮地抱怨。老板不声不响地抄起勺子,多浇满满一勺。和普通的酱油不同,这家店的肠粉是配勾了芡的汤汁。
“你可真不客气。”
“熟嘛。我都可以在这边赊账吃一周。”傅俊笑笑,有点小得意。
此时,餐厅夜宵生意结束后的白海彬可能刚睡下不久;周末不用去写字楼打扫卫生的李阿姨也可以睡个懒觉;吴子仪多半在和妻子女儿以及好不容易周末回家的儿子共进早餐;曾峰正匆匆赶往公司和老板开周末高层会议;杨善庆大约已走在带人看房的路上。

企业求报道、约采访、内容合作,请加微信:ylennon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商界APP,悦读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