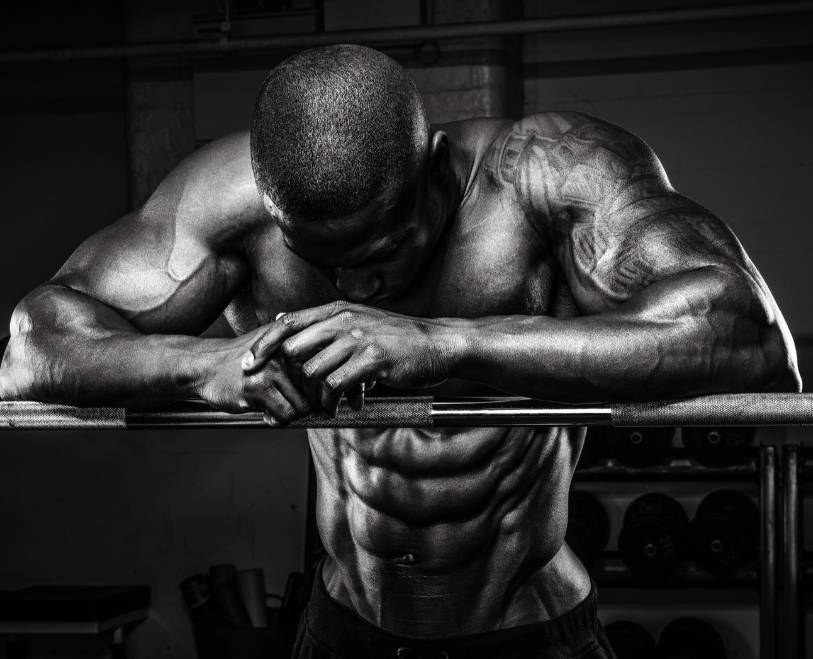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说谎、伤害或冒犯他人是不对的,对父母的残忍行为以牙还牙而不理解其中的好意是不对的,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孩子说真话,对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忽略父母行为的残酷性,接受父母的思想但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当对他有所期望时不会闹别扭,这些都被认为是优秀而正确的品质。这些近乎普遍的价值观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为了教会孩子,成年人认为他们有时必须诉诸谎言、欺骗、残暴、虐待,让孩子遭受羞辱。然而,对成年人来说,这些行为并不涉及“负面价值观”,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教养,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只为达到一个神圣的目的:让孩子在未来不再说谎,不再欺骗、仇恨、残忍和自私。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这个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我们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是好还是坏。这一原则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强者发号施令,战争的胜利者迟早会得到掌声,而不管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犯下什么罪行。
在我们热衷于向孩子灌输上述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以下情形并不总能成立,比如: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说真话,在不撒谎的情况下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忽视父母的残忍而仍然成为独立自主、能做出批判性判断的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些在整个童年时期被允许做出适当反应的人,也就是,对有意或无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错误和否定表现出愤怒,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将会保持这种适当反应的能力。在成年后,当有人伤害他们时,他们将能够意识到并表达出来。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猛烈地回击。这种需要只出现在那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自身感情堤坝破裂的人身上。因为一旦大坝决堤,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由于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会回避任何自发的反应;有些人则会偶尔对替代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或者反复诉诸谋杀或恐怖主义等暴力行为。一个能理解自身愤怒并将其整合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会变得暴力。只有当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愤怒时,他才需要攻击他人。如果在小时候不被允许熟悉愤怒这种感觉,他将永远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体验,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周围的环境中完全不可想象。
考虑到这些因素,近年来德国60%的恐怖分子都是新教牧师的子女,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情况的悲剧在于,父母的本意无疑是好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善解人意、有教养、随和、不苛求、体贴、无私、自制、感恩、不任性、不顽固、不叛逆,最重要的是温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孩子们灌输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他们甚至准备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些优秀的教育目标。如果孩子们在青春期表现出暴力行为的迹象,那么他们既在表现自身童年缺乏活力的一面,也在表现父母心中没有生机、被压抑和隐藏的一面,而后者只有孩子能感知到。
当恐怖分子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以完成一项“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时,他们做的事情真的与父母曾经对他们所做的有所不同吗?当他们还是充满活力的孩子时,父母就怀着做一件伟大善事的感觉,把他们作为祭品献给了宏伟的教育目标,献给了崇高的宗教价值观。由于这些年轻人从未被允许相信自己的感受,由于教育理念的原因,他们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些聪明且常常十分敏感的人,曾经为一种“更高的”道德而牺牲,成年后又为另一种——通常是相反的——意识形态而牺牲自己,为此,他们允许内心深处的自我被完全支配,就像他们童年时的情况一样。
但如果一个孩子的“教养”完全成功,以致他身上没有丝毫的自发性,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就好比阿道夫·艾希曼和鲁道夫·霍斯二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得很听话,“教养”十分成功,以至于这种训练从未失效。在他们的心灵结构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裂缝,从来没有渗透过一滴水,也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情感冲击过它。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些人都在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从不质疑命令的内容。他们执行命令,并非出于对命令内在正确性的认识,而仅仅因为它们是命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审判时,证人最动人的证词都不能令艾希曼流露出丝毫情绪,然而在宣读判决书时,忘记起立的他经人提醒后却尴尬得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