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写《冰鉴》,认为看一个人的面相,首先要观他的神骨,神骨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状态,而对一部作品而言,神骨就是它的艺术风格。
《大护法》是一部水墨动画,水墨电影是我国动画史上的明珠,它本来就具有自己强烈的美术风格和艺术底蕴,而当它被一个创作者独有的脾性,思维和心灵能力进行运用的时候,又能重新激活它多姿多彩的艺术价值。
艺术风格即作者心灵的表象,在动画电影里,他的重要性不亚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而语言决定了文学的艺术高度,只有语言,才能衡量一部作品的文学性和它的最终价值。语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审美是对我们的生活的重构和升华,一个人只能这么说话,就意味着他只能这么生活。这正是《大护法》艺术风格所起的作用,一部作品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的情感的伟大与热烈,而在于它艺术作用的强烈。
同样,创作的主题不能孤立的存在,无论我们从《大护法》中看到什么内核,比如说反乌托邦或者是追求自由,只要是忽视艺术风格去评论主题,无异于丢失了作品最重要的审美品质。
然而在事实上,在《大护法》看到反乌托邦或者追求自由,都只停留在最浅显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作品的内部。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考察电影中每一个人物的行为动机,我们就会发现,整部电影的艺术风格,完全围绕着一个词语产生,就是“丢失”。
“丢失”塑造了电影从头到尾的诡异和阴冷的气氛,也发展了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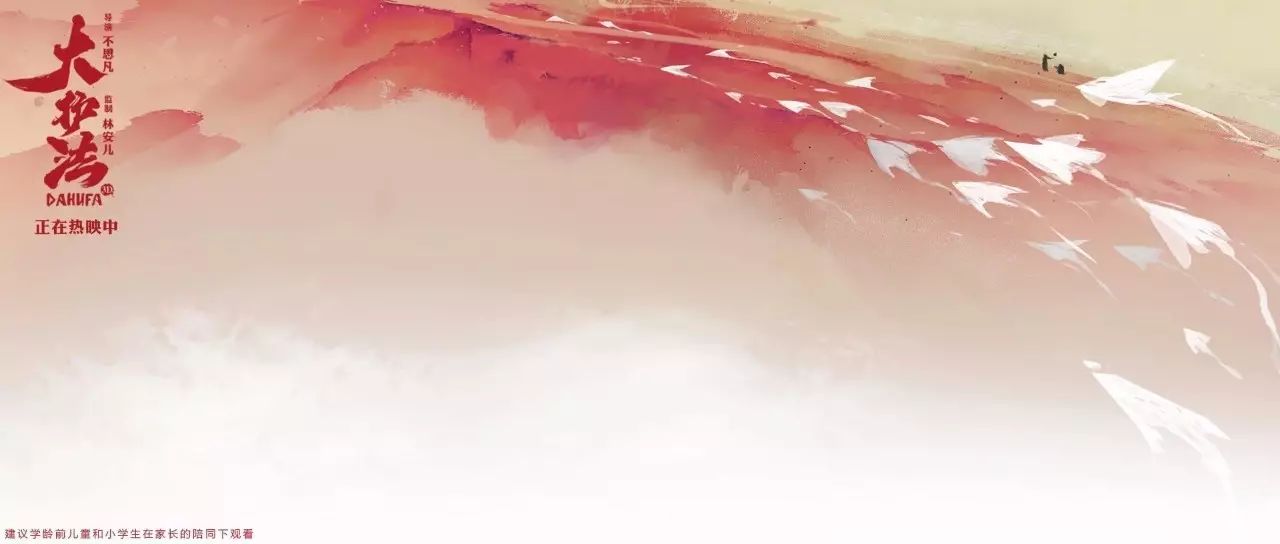
电影开场,主角大护法出现,他的第一句话“我要寻找太子。”就自然的将我们带入了主线。他为什么找太子,因为太子“丢失”了。太子为什么不愿意回皇宫呢?因为在皇宫里,他就要承继皇位,他的梦想丢失了。
丢失了作为人的资格而活着的花生人被当做猪崽一样圈养,他们丢失了记忆,也丢失了语言,而圈养他们的吉安神仙,丢失了自己荣华富贵,所以要在一个偏僻的城镇里宰杀花生人收集黑色的异石。
电影中几次故事的推进也是因为“丢失”,大护法的武器权杖的丢失,大护法找到了太子,太子又丢失了。
丢失,就意味着找不到,所以要去寻找,然而是终其一生都在迷宫里瞎碰乱撞,花生人老巢如蚁穴般复杂让人迷失,庖族后人找不到自己祖辈的荣耀苦练刀法,最终惶恐而亡死在自己刀下,黑衣人丢失了自己道路,不敢直面内心的恐惧,甚至在电影里,我们连他的脸都看不见。
花生人的诡异,歪斜的小镇,人人孤立的气氛和各种迷路的人物,都让我们发现,其实花生镇是一个如迷宫般的囚笼,它带来的阴冷和不安的气氛,与其说是一种恐惧,不如说是一种苦闷的象征。
这种“苦闷的象征”就是《大护法》的艺术风格的最终呈现,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美学,是通过表达主体的消极性来体现的,主体的消极性,是时代对人的主体的伤害,人的主体性的“丢失”,它来自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存压力。

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失语,现代文学一直在写它的失语,失语就是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说不出话?因为被损害了,压抑了,控制了,异化了。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会说话,会使用语言,在电影里,花生人只要说话,就会被枪毙,因为他们不是人,没有资格说话。他们长着人的样子,却不能说话,所以不能算人,只是被异化后的人,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个象征异化的甲虫,有人的思维,但没有人的语言,不被他的家人承认算人。
电影里塑造的荒诞和诡异的世界,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处境,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人被异化的环境里,就像《大护法》里面的人一样,面对着空白,人格分裂,丢失感,不断的寻找,失语,噩梦,孤独,因此也诞生了这部电影的阴冷的艺术气质。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存在主义者处境,绝对不能把它理解成反乌托邦和反法西斯,反乌托邦是彻底绝望的,你说花生人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来追求自己的自由,这也不是反法西斯的,因为作为极权的压迫者吉安老神仙也是一个“丢失”的异化人。所以《大护法》里面的自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由,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自由,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就像花生人一样,语言是我们的生存家园,他只要说话,他就成为人了。
从波德莱尔开始,我们的艺术审美就开始走向复杂和多极,冷的,恶的,丑的,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审美对象,比如你看大护法做得那个噩梦,害怕不害怕?但它也美,不过它的美是妖艳和诡异的。同样的,我们文艺作品里的主角,也从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走向了一个个有缺陷的普通人。

《大护法》里各色的人物也是这样,作为主角的大护法,拯救花生人的英雄,是一个矮冬瓜的形象,花生人更连作为人的权利都已经丧失,他们都是非崇高化的人,畸零的人,被异化的人。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审美对象,悲剧不是一个英雄去承担,因为在《大护法》里,每一个人物都是迷失的,都在承担这种悲剧,哪怕到了故事结尾,人物的最终去向也是扑朔成谜。
所以我们看花生人,其实更像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他写到:“世界的毁灭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电影的最后,花生人抬头看向天空他们黑色葫芦的母体,就像这“嘘”的一声。所以也许这些人物本身都不是英雄,也不崇高,但对我们自身有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