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3 日下午,《单读 14 :世界的水手》新书发布会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行。这一次,单读首次将目光跨越海洋,聚焦他国文学。
从 2016 年开始,从美国总统选举、英国脱欧,到最近法国大选,好像世界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和政治的历程。保守主义重新兴起,民族主义重新泛滥,但人们似乎对全球化进程,世界主义,人类的普适价值等更具整体性的议题失去了兴趣。因此我们希望把人们从个人欲望中抽离出来,再次把目光放到人对世界的认识上。
本期新书发布活动,是单读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联合出品,特邀《辛德勒的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记者、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记者周轶君,作家、媒体人袁凌和纪录片导演吴琦展开对谈。主题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寻找历史真相。为了凝练地呈现这次对谈的精髓,我们将整场活动凝聚成六个问题。

问题一:用记者的眼光和作家的眼光来看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 Brooks 在《单读14》新书发布会
Brooks (澳大利亚记者、小说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昨天( 5 月 12 日)我时隔多年又重新爬上了长城,而且是和我们澳大利亚知名的作家 Tom Keneally 一起去的。
站在长城上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象千百年前那些修筑长城的工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如何一砖一瓦的把这么多的砖块、石头全都搬到这么陡峭的山峰上去的,而且我又不禁想象在过去这么多年间那些在长城上站岗的士兵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每天晚上在那上面站岗会有怎样的心境呢?这些种种的想象和想法都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的一些心境和想法。
如果我是一名记者的话,那其实我可能在理解长城的问题上更加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防火墙了,我可能就会想到通过中国的防火墙,进入防火墙的信息有哪些,被拦截的信息有哪些,是哪些人在监管这些信息,这都是作为一名记者我会思考的一些问题。
而且最近正好中国在开“一带一路”的会议,所以我也在想会议上讨论的是不是除了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的问题之外,还会多多的讨论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呢?是不是这样的会议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比方说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呢?这些都是我希望看到的。

Brooks 在单读新书发布会上半场“在全世界的家中”发言
其实虽然我现在是当一名小说家,靠我的想象力来写作来生活,但其实我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世界公民的心态。因为现在我主要是住在美国,每天我回家都会打开报纸来看看特朗普他又为美国干了些什么事情,在他的统治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美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一直还是非常关心时政的。即使现在我是一名小说家,其实过去我作为记者的一些经历和背景都不断为我现在的写作在汲取养分。
问题二:中国的传媒行业本身有什么问题?怎样在写作中逼近真实?
周轶君(记者):之前这两位的作品我都有看过,对他们的一些评论我都比较熟悉。刚好我处在他们中间的一个状态, Brooks 她是做记者慢慢转向作家,后来写历史小说当中虚构的成分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她写《奇迹之年》,一些虚构非常有意思。
袁老师(袁凌,作家、媒体人),我看过他很多的作品,在中国的题目比较多,而且是非常扎扎实实的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调研报道。他们一个是国际的议题,然后再一个是中国的议题,我是在中间是一个桥的感觉。

周轶君在单读新书发布会上半场“在全世界的家中”发言
中国的国际报道,写人的、非虚构的,我感觉力量比较薄弱。当中有很多的原因,你需要有金钱和时间,其实更多的是有金钱,媒体有闲置性。在过去传统媒体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比如说一些大的央媒的机构,他会派你很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可以有时间去观察。
但也不是你有时间就可以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要有观察的能力,还要有这个观念在你脑子里,你要去观察。
我觉得西方的作者比我多一个优势,他们常常在两个世界里面跳跃,东方和西方的,他看到中国的时候会联想到他自己的背景。比如说他看到中国的一个城市,我联想到美国的一个地方,有个多维度的比较在里面。作为中国的作者来说,你可以比较的没有那么多。
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些技法的学习。其实我觉得写作当然是一种天赋,你要有这个环境。但是你能看到别人有一些非常新的写法,他们会拓宽你的视野。
比如说我看到她( Brooks )在写《奇迹之年》的时候,她虽然自己真的去学习放羊了,因为她当时看到很多领导者都从牧羊人开始,她就觉得为什么放羊那么重要,她就真的去放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就是说我真的要去尝试这个事情,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技法,不同的空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单读新书发布现场聆听的观众们
我在新闻第一线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 2014 年我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我给了我自己时间,我一个人重新回到东欧去采访,那一年对我来说也是写作上非常大的转变,不过那一年的作品到现在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我觉得以前作为记者来说我去采访的时间、空间都非常有限,你基本是到那个地方,把一个麦放在那里的意义要多过于你真的采访到了什么东西。
2014 年的时候就完全是我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摄影机。因为人们对于摄影机它说话的状态跟你真实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去采访我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时候采访过的那些人。隔了三年的时间、空间重新去看他们的生活。你可以拉开一个时间距离看到变化,这样一个时间距离是你单纯做一组采访难做到的,它不一定有这个空间让你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学习阿拉伯语,中东特别是埃及,我都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又会有自己的一个观察,所以我的故事变得多维度,变得我觉得比过去要厚实许多。你拉开距离,不断的去采访一个人的话,你看到的故事远远比一个记者到那里看见一个人拉着他说几句话要有意义得多,要丰富得多,而且那样才更接近于真实。
问题三:女性记者在过去几十年内都面临着身份的变化。就像海明威的妻子韦尔什,她的战场报道非常准确和快速,甚至要好过海明威,不知道是不是性别偏见导致了人们对他们作品阅读了解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中国其实这样的女记者更少,女性身份在这个行业有什么变化呢?
周轶君: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我会觉得女性的身份给我的好处比坏处多得太多。说实话,今天中国战地记者非常多,当中作为一位女性其实是更受关注。另外一个,其实在中东那样的地方,作为女性我觉得很少有地方是我们不能去的。你戴个头巾,甚至是比如说我去一个葬礼去采访的话,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葬礼,那我不能进到,但我试过我跟那个人去说,他都会让我去说,因为他尊重你是一个记者,其实没有问题的。
因为是女性的身份,我也可以见到一些领导人的夫人,我之前看到 Brooks 她也写过,她会被带到那些王后的宫殿等等。你会有自己的渠道去交流,特别是当地一些家庭里面,我可以一直走到他们家里面最深处,看到那些在哺乳的妈妈。
那时候我去采访一个犹太人地区点,离那个地区点最近的一个人家,我在他们家住了一夜,他们特别好客,就把床让给我睡,然后整家人都睡在地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他不太可能让一个男性住在他们家里。
所以我觉得女性其实在写作,在采访方面优势非常的大。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困难肯定会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带头巾不太方便,如果别人看到你没有戴头巾可能会对你丢石头,或者是动手动脚这些事情都是有的。那时我们当成一种常态,甚至可以去忽视它的一些细节上的困难。

Brooks :我非常同意周老师的说法,因为特别是在中东女性记者是有非常多的优势的,而且比方说像我们男同事他们就觉得没有机会接触当地妇女的生活,我就拥有这样的便利。但是有时候其实即使有种种不便,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不便转变为便利。接下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玛丽韦尔什与海明威
刚才提到了海明威和他的某一任妻子韦尔什的故事,想给大家说一说,在二战的时候,当时美军他们是不准女性记者上前线进行采访的,海明威他就因为是男性记者,就可以到前线去报道这个诺曼底登陆,但是韦尔什是女性,她就不能直接大摇大摆的上前线。她自己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就说我要坐船到英国,我要去报道当地的这些护士的生活和故事,但是其实这并不是她的真实目的,她就借这个借口登上了一艘船,然后想方设法留在那,并且成功地写出了比海明威更加精彩得多的诺曼底登陆的故事。
问题四:不管是纪录片工作还是写作,或者是写其他历史类小说的工作,前期的巨大的工作量会不会对后期的自由创作、想象力的发挥形成某种限制?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怎么把握自由创作与真实的界限?
Kenneally (澳大利亚作家):其实在写《辛德勒的名单》的时候,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在接受采访之前都有个要求,那就是成书之后他们有权先看过这本书,并且对这个书提出修改意见。其实这也离不开我写这个故事的初衷,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了更好的呈现这个故事,我必须要用一种所谓的纪录片式的小说,或者事实加小说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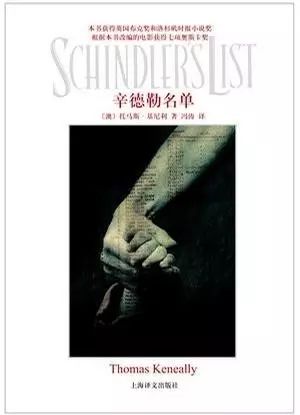
《辛德勒名单》
作者: [澳] 托马斯·肯尼利
所以在成书之后,这本书经过了 36 名幸存者的修改。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希望确保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声音被错误的传递出去。他们一方面这么做,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否认这段历史,会抹消这段历史的存在,他们所以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境;另外一方面有很多人甚至会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希望抹去这段历史。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确实存在这样一段历史,希望提供一段历史的证据。

Keneally 在单读新书发布会下半场“找寻辛德勒的名单”发言
吴琦(纪录片导演):你是说的虚构,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真实。你说这个直播是真的吗?但是你说现在这儿出现另外一个人,我们在直播,出现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人,导播完全可以切他进来,然后你还是看到大家在这儿探讨问题。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叙述视角存在就没有绝对的真实,它一定是他所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非虚构的一个原则是,我的道德是为了接近于真实去做一个表达。因为我们的世界那么复杂,本来就有很多蛛丝马迹。
现在西方包括在美国,非常流行剧情的方法,在我们纪录片里面也有这样的方法,他们就问这个边界在哪。我说我们做这个非虚构写作中就跟拍摄的人,其实有点像一个考古学家,当我们在一堆考古的废墟里头发现一些陶片,我们就开始试着要拼它,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为它很像一个陶罐的形态,但是我们找不齐所有的碎片。
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那些缺失的碎片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时候考古学家会用白胶泥把那些缺失的碎片填上。于是我们经常在历史博物馆看到很多陶罐是带着白色的胶泥待在那儿,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罐子,而是一个通过想象恢复再重建的一个罐子。
那个罐子带着白胶泥我觉得它就是真实的,因为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告诉你那个东西丢了,我们补了它。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罐子重新刷漆再烤一遍再搁到那儿,这个就叫赝品。

吴琦在单读新书发布会下半场“找寻辛德勒的名单”发言
我们在做历史的书写和非虚构写作的时候,试图用一些东西去弥补那些缺失的叙事的段片,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事件的发生,而不是为了去掩盖这个事件的真相,这个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罐子刷上新的漆又重新烤,这就是一个假的。虽然它含有原来的残片,但是对于公众来说这就是一个假罐,我带着白胶泥它就是一个真罐。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形象的说一个真实,我们在非虚构在纪录片拍摄中面对真实和我们自己的叙述之间的一个边界。

Kenneally:我发现我跟吴琦之间想法有太多的共同点了,我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虚构类的作品。也做了很多研究,比方说我研究到一个故事,过去有一家被流放澳大利亚的家庭,他们流放的这个地方在 19 世纪初的时候跟拿破仑被流放的地方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一家经常会拥有一些特权,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到拿破仑被流放的地方,去跟他交谈一会儿或者有时候甚至一块骑骑马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谜团一直给我留下来,那就是为什么这一家子他们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特权,可以这样完全零距离的接近到拿破仑。那么现在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一个理论可能说他们家有一个人同意去做间谍,去接近拿破仑换取情报,但是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确实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这就是历史,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信息和真实的信息之间的一个缺陷,也就是刚才吴齐说到的白胶的那个部分。写小说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手上没有很多现成的材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创造出很多的想象力的这个内容,来把现实和小说的情节联系起来。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们经常用一些虚构性的所谓的谎言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问题五:《辛德勒的名单》这本书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而且它涉及了人类历史上非常多的苦难,甚至是一些非常敏感的,像大屠杀这样的话题。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是到哪一步才决定真的要写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写作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和困难?
Kenneally: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叙事,把这个故事真正的写出来。因为通常我在写书写到一半的时候多少都会遇到一些瓶颈,《辛德勒的名单》是这样的,其实我发现写任何书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写书就好比是结婚一样,写书跟结婚一样都是需要激情,需要有感情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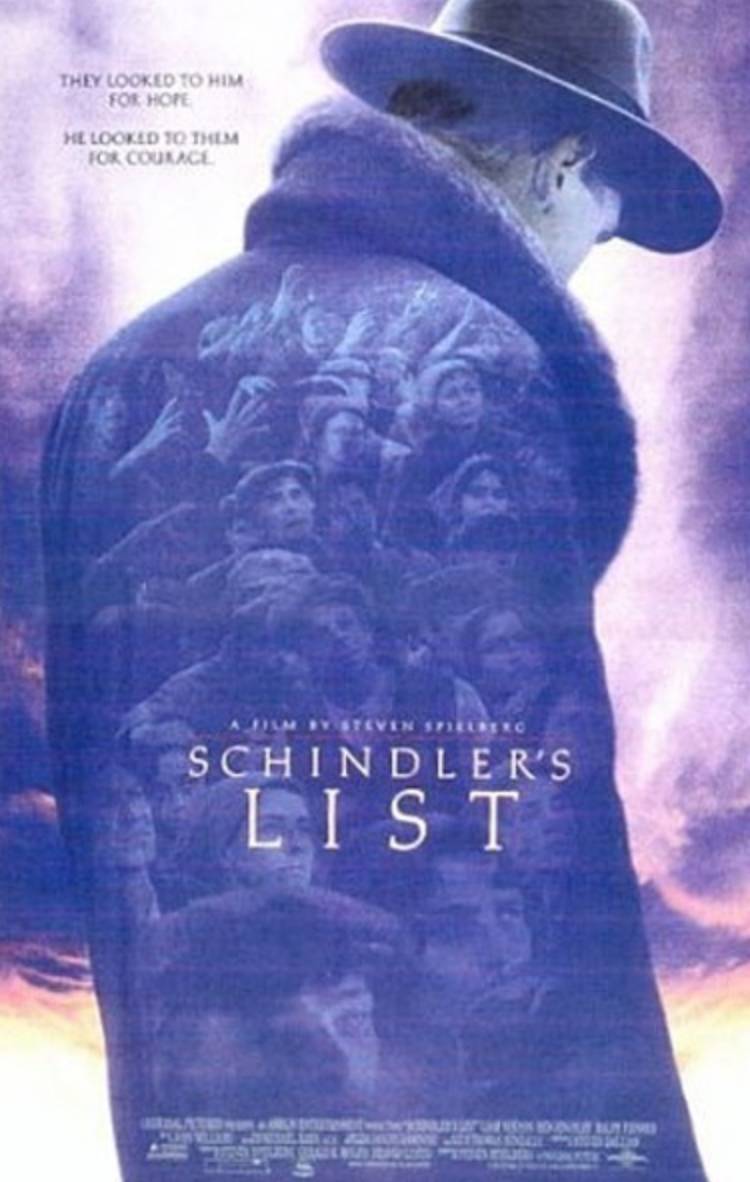
根据《辛德勒名单》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可能哪天写书写到一半或者是结婚的过程中突然激情不在了,可能会自问,我当初为什么要结这个婚。但是其实有这样小小的疑虑和顾虑有可能,过了两周之后你的这个对象或者是你的这个伴侣他又做了一件让你觉得非常贴心的事情,你又愿意继续跟他过下去了,其实写书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短暂的瓶颈,但是最后我会愿意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因为其实写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写书只能自己写,这个事情别人没法帮你干。所以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尽可能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来把自己心中的声音传递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跟拍纪录片也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在描写这样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尽可能的不要用形容词。因为可能在描述这些大屠杀或者是种族屠杀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非人性或者是犯罪这样的词汇,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汇绝不足以体现出这类行为背后的本质。所以我认为我们只有用那种最直接的,用纪录片式的语言来呈现才能真正的还原事件的原貌。

我另外一本书写的是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多人最开始写故事的时候,可能希望在那简单的做一个报告,随意的提取一个故事就好了。但是你写作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到实地去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当你越深入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本身,当地的人们会一直不断的吸引着你,让你了解更多,写的更多。
问题六:如何理解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的界限?
袁凌(作家、媒体人):确实我很早就同时写这两种东西,一开始界限比较清楚;后来开始写特稿包括现在的随笔,这类也属于非虚构的东西,我也感觉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到底有什么区别,可以结合我的小说来说。

袁凌在单读新书发布会上半场“在全世界的家中”发言
我这个小说是写重庆的,我在十几年前写好的,但因为它过去了十几年,我感觉我需要加一些现在的东西。所以我就又到重庆去了三次,然后去补一些现在的东西,但我补的东西,都是非虚构的东西。
比如说重庆的变化,各种表面的深层的变化。比如我当时挂的户口在重庆,我觉得我需要去看一下我当时填的地址门牌号什么是不是真的。但我这个门牌号是假的。这种非常真实的去调查中可以看到很多魔幻的现实。
比如我写重庆的“棒棒”,我在这里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有这么大的必要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要加这个帽子,一个非虚构的帽子,我就感觉有必要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以我就去补一下,他们现在住在哪里,通过别人去找到很大一个房间,全是架子床,觉得还是很震惊。

重庆“棒棒”
现在我这个小说有个将近三万字的非虚构的帽子,还有十几万字的主体,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写,但是我觉得我反正要这么写,所以我把它写完之后,我找了几个我熟悉的杂志编辑和小说家让他们看,但是他们还没给我回应。我现在比较一下,到底三万多非虚构的帽子和后面的主体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感觉还是有的,非虚构的这部分是更强调时政性,我就是表达那样的变化,通过我的亲身的去还原,去到现场去交谈表达,把它比较确实的搁在这里。
我觉得小说的经验当然它可以张冠李戴,但是经验都是真实的,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产生化学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虚构作品你需要有自己的感受在里面,这种感受我觉得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真正无法延续的东西,这个是深层次的区别。以后在写作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都不会考虑太多这个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他们应该是在同一个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方向,一个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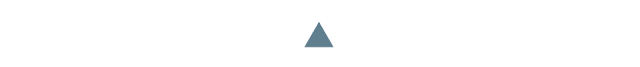
编辑 | 关关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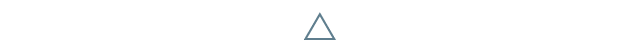

识别图中二维码,预购正在印刷中的《单读 14 ·世界的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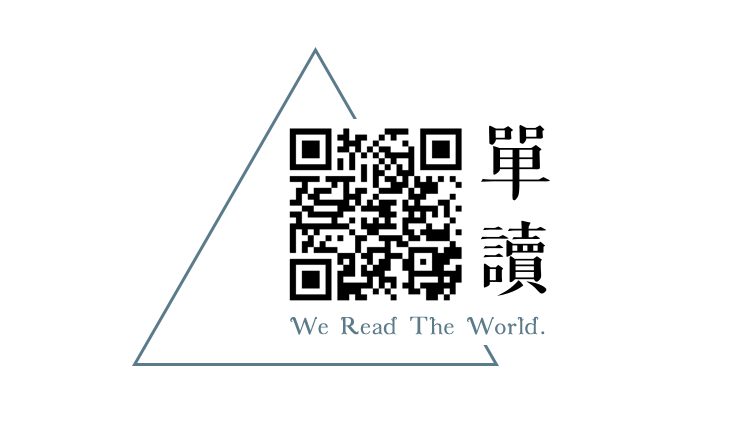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抢先预订正在印刷中的最新一期《单读》,成为与我们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