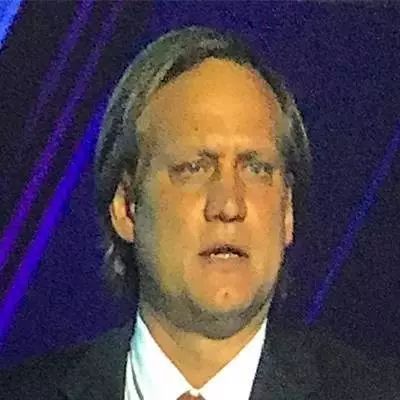这篇文章主要书写半导体相关的知识。算是有一个开头,远没有写完,或者说毕我一生精力,也无法将其写完。文章中涉及了较多的半导体相关知识,仓促间整理,必有疏忽,希望大家不吝指出。
其下是原文链接与前言部分。
https://pan.baidu.com/s/1y9wFB0gN0__sjSbYYw98Ag
前 言
上帝造人,而后创造半导体。
地球的表面,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氧,然后是硅。人类无法离开氧,也同样离不开硅。两百五十万年以前,我们使用硅的原始形态石块制作工具,从那时起的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一万年前,古人抛弃石块,进入青铜、铁、蒸汽与电气时代。在上世纪中叶的某一天,伴随晶体管的出现,硅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等待,做为半导体而不是石块,被人类重新发现。
在渐别石器时代长达万年的时光中,人类与半导体相关的历史不足百年。在这百年之中,留下记载的仅是几个剧烈跳动着的与半导体有少许关联的事实。在这些事实之间,因为几段关键记忆碎片的遗失,半导体发展的萌芽期已无法完整复原,或许这些碎片从未真实的存在过。没有人能清晰地阐述,半导体从何而来,做为半导体的硅的演进全貌。
公元1823年,Jöns Jakob Berzelius在整理与穷举化学元素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硅,此时的硅对人类的意义远不及玻璃[1]。公元1833年,法拉第成为第一个观测到半导体现象的人类,他发现硫化银在温度升高时电阻降低[2]。在当时,这一发现自然无法与他对电光磁的贡献相提并论。随后几十年,这一发现始终生活在证明与证伪的争论之中。
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认为半导体不过是因为在其中存在着一些导体杂质罢了,化学意义上的纯半导体材料并不存在[3]。公元1931年,Alan Wilson使用量子力学的原理解释了半导体材料的许多特性,出版了一本名为《半导体电子理论》的书籍[4]。学识渊博如此的Alan也在质疑着纯半导体元素是否存在[3]。
上世纪前半叶,在这个仅属于理论物理的大时代中,半导体在安静地等待。公元1900年,普朗克发现了最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常数,量子从潘多拉魔盒中飞出,席卷了整个经典物理世界,引发了一场异常激烈且旷日持久的论战。这一论战从波动与粒子之争开始,甚至讨论到上帝是否掷骰子,直到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教皇玻尔先后离世,这场论战终告段落。
除了论战双方的两位主将,科技史册还以黄金为体,钻石为笔铭刻了薛定谔和狄拉克的方程式,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与矩阵力学,泡利的不相容原理,玻恩对薛定谔方程的统计解释。量子力学伴随着这些先驱们的努力,在周边的质疑声中,不断前行,为凝聚态物理的出现提供了富饶的土壤。
1928年,海森堡的学生布洛赫基于三大近似,修订了量子自由电子模型,通过傅立叶函数分析,解释了电子如何自由地潜行于金属之中,创建能带理论雏形。1930年,Léon Brillouin提出布里渊区。1931年,Alan Wilson分析了导体、半导体与绝缘体的区别。这些理论在安静等待着半导体的诞生,等待因此带来的在当时无法想象的计算能力,来验证这些理论。
为半导体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场无法用损失来计量的大战之中,因为雷达对晶体整流器的需求,极大促进了硅与锗的提纯工艺[5]。1941年Russell Ohl发现了基于硅的PN结与光伏效应[6]。这些零星的发现为半导体产业的横空出世,提供了无限接近的可能性,却没有提供必然性。半导体萌芽期的真正秘密也许被这场战争永久封存。
战争与科技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多与战争相关。青铜与铁器始于刀剑;战舰是蒸汽机的巅峰之作;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用于枪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使中子物理学蓬勃发展,原子弹的出现震惊也唤醒了整个世界。
大乱大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得到了自诞生以来,最珍贵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人类至今为止,所收获的第一份没有与战争直接相连的礼物。公元1947年12月16日,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发现晶体管[7]。至此人类进入电子信息时代,因为硅的特殊贡献,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为硅石器时代。
硅的某些单一特性也许不如锗、不如碳、不如化合物半导体,综合特性却是最优,与其他化学元素的结合堪称完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硅替代锗,登上半导体的最高舞台。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为基于硅的集成电路插上翅膀,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硅半导体在到达了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之后,终于放慢了脚步。
成也摩尔,败也摩尔。摩尔定律是硅半导体行业跌下神坛的催化剂,在这个定律持续正确的时光里,硅半导体发展的速度超越了上帝的想象,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走尽了一生之路。硅半导体发展的举步维艰,叠加着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坍塌,这个行业遭遇了自诞生以来最大的萧条。一瞬间,半导体从宠儿沦为被资本抛弃的对象。
面对不断下行的行业,参与者恍然醒悟,昔日的竞争对手衰老到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剩下。在摩尔定律的失效声中,在一阵阵并购重组的喧嚣中,硅半导体产业长达六十余年的辉煌宣告结束。从这个产业的最高处向下俯视,会发现一个以十五年为周期的波翻浪涌。当科技的命运被供需左右,受应用场景牵引时,在顶级从业者的心中这个行业已然老去。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高频、高温、强电流等应用场景始终有一席之地,却难以在更为广阔的集成电路领域替换硅。碳基材料始终被寄予厚望。人类对钻石的渴望,对石油的依赖,植物、动物与矿物质对碳的追逐,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碳循环。这个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创造的壮观,强烈暗示人类需要再次发现这个为世界带来生命的元素,碳。
宇宙万物遵循着几乎相同的规律,外表的差别无法掩饰内在的一致。假如这个星球的出现不是偶然,上帝不会让稀缺物质作为时代的基石。我们可以利用无处不在的光,凝聚态物质除了固体,还有许多选择。人类寻找新材料的努力未曾停歇,也许我们毕其一生无法取得发现,也许明天会有新的发现。这些新材料没有出现之前,整合接近完毕的半导体世界原本一片静谧。
逐步强大的中国,为历史牵引,走到了需要升级世界工厂的时刻,半导体产业再次成为关键选择,打破了这个世界原有的平静,为这个在不可知命运中前行的行业,注入了生机、喜悦、动力与无畏,也带来了萎靡、忧伤、阻力与恐惧。对于半导体行业,新势力的进驻,总会带来变化。相对于不变,有些变化总是好的。
半导体晶圆的边缘处没有多少用途,我愿意将这些变化记载于此,将能捕捉到的瞬间出现的美丽记载于此。本不想在这里过多记载与技术有关的话题,只是面对着这个厚重的行业时,不得已使用了一些与技术相关的语言,以求少许安宁,以求本篇能在最小的集合内做到自我封闭。读者可以将一些晦涩的内容略去而不会影响阅读的连续性。
书中涉及少许自然科学与半导体相关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代表过去,也是在近距离观察着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同的历史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解读,也因此在每一刻都有重温历史的必要,历史与今天常有惊人的巧合。历史是一面镜子,在镜中我们可以寻找未来。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本书的部分内容发生了少许变化。在接朋友女儿去大学报到的路上,因为堵车,聊了一些数理化的基础知识。并不惊讶,这一代孩子所受的教育比我们当年系统,在基础知识的综合层面上远胜于已经将这些知识忘却的成年人,他们只是不熟悉一些高级的数学技巧。因为这个原因我将原文中出现的所有高级符号调整为最基础的数学运算。书中的有些内容也许你们现在还不明白,我也不算完全明白,我愿意与你们一同讨论。
在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中,有少许优秀的孩子在数理化层面已经不用继续上大学了。这并不奇怪,布拉格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不过25岁,海森堡、狄拉克、普朗克与泡利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均年少成名。18至25岁是最有创造力的时间,倘若能在自己的兴趣点上做到专注,必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
一代胜于一代。事物的发展如此,人类的进步更是如此。以一个大的时间段划分,一代强于一代庚古不移。某一年代也许会出现某个人,震烁古今,也无法违背这个规律。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些中国人足够勤奋,也许也足够聪明,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在科技领域基础层面的落后。这个国家需要年轻一代人的持续努力,为这个星球做出与人口比例匹配的贡献。
如果因为这篇文章的原因,使一些年轻人了解了一些半导体行业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喜欢上最基础的物理化学,喜欢上能够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材料科学,进而有意愿去重新发现这个世界,这将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永远并不算远。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年轻人承载希望,更需要珍惜现有时光.花有重开,人无少年。
这篇文章的主要书写对象是18至25岁的年轻一代。对于这些年轻人,半导体科学中涉及的知识点过多、过于复杂。每一个知识点,都有多本千页的书籍描绘。一步一个脚印读过去,耗时极长。年轻时记忆力好,可以粗观其大略,空中越过许多步骤,搭建对半导体科学的整体认识,之后再聚焦于自己的兴趣,补齐剩余知识。
在明了为何而学后,面对着貌似枯燥的数学、四大力学与化学,将会乐在其中。这些知识是半导体科学的基石,不可不察。掌握这些基础学科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如果有,我认为最终的捷径是规规矩矩地学习课本中的知识。能在大学中能够流传下来的知识,均千锤百炼。互联网的便利,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学习到最顶级大学的课本。
不限于国内,在国外的教科书中,复杂的公式也如汗牛充栋。少有书籍会沿着历史的足迹,将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抽丝剥茧。这些呈现在学生面前的繁琐公式与推导过程,起初非常简练,仅需寥寥数语即可解释清楚。在多数情况下,越是复杂的公式越是公理推导而后获得的结论。经典公式并不复杂,质能方程与麦克斯韦方程组皆一清若水。
治学先治史,在自然科学中尤显重要。在文章中,我会尽力沿着历史的轨迹,阐述半导体知识的来龙去脉,和大家一道探索这些科学家们,在获得这些发现前后的思想方法与脉络,不再苛求这些知识点的细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远胜于学会从公理开始推导并记忆一些结论。
在书中,出生于19世纪中叶之前的著名人物,与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均使用中文名称。这里不仅是为了表示尊敬,更因为这些人,以及与对这些人的称呼,在中文世界中已经有着约定俗成的说法。
我从今年的元旦开始整理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期间写写停停,大多数时间是在学习与思考。这篇文章不算长,却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完稿时,中国的南方下了一场大雪。
王齐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