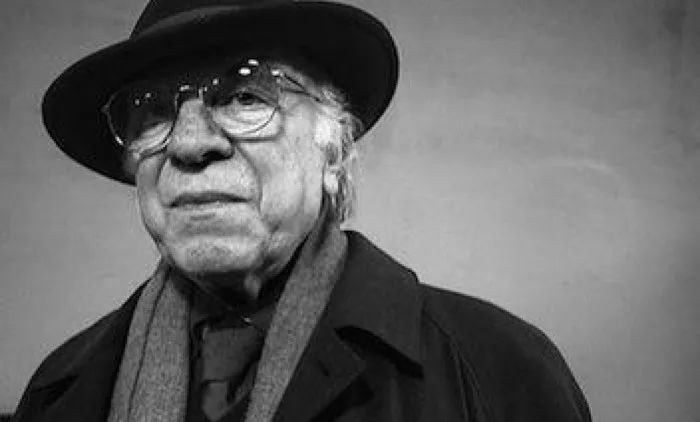
preface
究竟是什么样的期望能够让我为了谈论一部书而写下另外一部书呢?这个疑问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批判,但是我就是为这一问题感到着迷,因此我写下了一部书,它是关于《瓦尔登湖》的。我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测定《瓦尔登湖》何以自身就是这样一部书,它谈论的便是自己作为一部书这件事本身,它何以能够如此的自足,以至于它就是在谈论自身的写作与阅读的。它也让我们浸入那些切实的体验之中,由此我们能够测定一个哲学文本如何是被另外的文本所激发的,为什么哲学史就是这样一种文本之间互相激发的历史?由此我们又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那个最原始的,或者说一切缘起的那个文本呢?我为这样的视角所吸引,对我来说,《瓦尔登湖》就是这样一系列不断闪烁的微光,它如此的向我显现,也如此的召唤着我。它如其所是,在它被写下的时候,它所属的文化还处于哲学化的前夜,那是一个纯然的时刻,在那转瞬即逝的时刻,一切还没有被狡黠的智术和专业化的哲学所污染。在那个时刻,哲学、文学和神学(也许还要算上政治学和经济学)还没有彼此孑然独立,但离异的阴影已然黑云压城,前途未卜。这一前哲学的时刻是德国和英国哲学传统开始形同陌路的前夜,而这一时刻又奠基了美国自己的时代。《瓦尔登湖》,我希望在我自己的哲学基点之间辗转反侧,并由此来呈现它,如果事如所愿,那么我也许就能够重现那些古朴的互动,它们曾发生在这些不同的传统之间。(对于那些我所看重的概念,我勾画了某些不同类型的韵律,这样的韵律属于遗世独立者,属于教导者,属于日常,也或者属于那些思想的黎明、澄清和解决。这些概念就是如此的翩然于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戏台之上。)
我总是把写作抽离于言说之外,正如列维
-
施特劳斯和雅克·德里达的写作中所扯开的缝隙,一面是我所说出的事物,一面是文学作为一种“写作”(
ecriture
)这一观念中所暗含的事物,我总是被问道,在这两者之间我究竟是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我曾一度认为我应该在这本书中对这一问题略加谈论,但是最终我认为这样做会是有误导的,我这么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
)《瓦尔登湖》对于写作的宣告是我必须要谈论的问题,而这使得我必须抽离于上述这些写作者之外,就仿佛我从来不曾知晓他们的思想那样。关于这一问题,《瓦尔登湖》仅仅是显现而非加以耸动,而我不能专断而又冒昧的将这些哲学辩驳施于《瓦尔登湖》之上。(
2
)实际上对于上述哲学家的观点,我并不真的熟知或理解,我无法说我同意他们,也无法给出自己的辩驳。比如说,如果他们是在暗示那些写下的语词(对立于说出的语词)是退化为一种文化表达(对立于已经被文化了的)的工具,那么毫无疑问我无法认同这种看法,实际上《瓦尔登湖》的作者也不会认同。在我看来,或者在我所认为的《瓦尔登湖》的作者看来,这两种表达的流转方式,它们既是回退的,同时也是一种展望。它的作者所坚持的是,如此的写作不意味着一种将其思想神秘化的企图,从而使其避免变革的洪流。正相反,如此的写作正是为了证明他所处文化言说方式中蕴藏着令人恐惧的神秘主义,而他要保护这部书中的语词,以对抗当时文化中的那份想要伤害或者否弃这些字词的癫狂倾向。(
3
)我对于写作的这样一些看法并不意味着我要给出能够施于一切文学之上的普遍性,我只是要提供一种独特的认识,它关于这部书作者的意图,并且主要是关于这种意图的两个层面:首先对于他所促成的写作条件的拾遗,而这又如何使他的写作成为了一种原初性的经典;其次,是关于他如何对他所处的文化保持警觉,他的发声即是对它的拒斥,比如他所获得的默识总是即疏离于所谓的社会,又疏离于我所说的绝望的沉默的“阴谋”,后者使得真正的社会既不能成为他的,也无法成为任何人的。不过,尽管我们如此叙述这这两个层面,但事实上这也并不是说这种拒斥就是一种单纯的逃避,而是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折返,是一种向其切近之物的恒常的返还。这意味着,首先他已然笃定的将他自己建立为一个邻人;而紧接着这也意味着,他同样笃定的将自己建立为一个异乡者;如此回转往复,也就意味着他建立了这样一种概念,而这就是处于邻人与异乡者之间的认识;而这又将意味着,他的读者被如此这般的建立为了他的异乡人。

我们终此一生皆应经受洗礼,为那些印记、誓言的洗礼感到欢欣;我们得自由,因舍此之外一切皆已与我们无关,一切迷雾皆已摈除,唯洗礼之所是除外,此一自由即朝向死亡,亦朝向重生。我们此一自由之荣耀,此一对洗礼之知晓便得长久,荫庇我们的时日。
——
马丁·路德
林云柯 /译
一读
平白常识呈现
——二而读
——三而读
方得朴素之美。
对于那些最伟大的经典作品来说,如果我们抱着赤子之心接近它们,显得言不尽意的缺失感会是很恰适的。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抛开一切限制,那些未说出的东西总是比任何我们说出的东西更美妙。《瓦尔登湖》的教诲最本然的部分几乎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它说明了这种缺失感是如何的无法逃避。
无论其他人如何理解梭罗作品的主题和进程,作为一个作家他最后还是变得著名了。但是相比于这种容易接受的看法,更困难的地方在于,在《瓦尔登湖》的写作中,我们无法通过综合梭罗的字词(至少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得出他究竟想要写一部怎样的书,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他那些严肃的批评总是被溶解在他所写下的神秘的旅程之中,以至于我们不能通过某种细查对《瓦尔登湖》的奥秘进行解释。我要以这样的假设开始我的论述,即这是一部已经被完美终结的书,也就是说他所要说的就在他所写下的每一个字词之中,而这就是对它奥秘全然的觉察,也是对奥秘的全然的开放。
让我们从最显而易见的地方开始,转动第一个齿轮,暂且设定下一些标准,也就是来看看梭罗在早期题为“阅读”的章节中所阐明方向是怎样的:
英雄史诗般的书籍,哪怕是以我们的母亲的口吻(
mother tongue
)拓印而出,对于一个堕落的时代来说它也是全然不敏的;而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辛勤劳作以搜寻意义,探寻一个比字词的一般使用更宏大的意义,由此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勇敢与良善才能呼之欲出。(Ⅲ
,3
)
[1]
这段话听起来有些许虔敬感,这样的句子有点老式沙龙或者读书俱乐部的腔调,在这些场合,这样的腔调用以表达说话者高尚的精神属性。但是,要进入梭罗的意图和雄心,这样的语言确实是我们需要率先涉足之处,他所描述的是他的篇章在我们的手中要如何被阅读。也许在一开始这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对于他所说的“经典”的赞誉显得很极端,而“在高义处阅读”与他对于“先人”的忠诚铰合在一起,这又似乎暗示着在当时的美国,那个被他描述为“躁动、神经质、忙乱、琐碎的十九世纪”的美国(ⅩⅤⅢ,14),写下这样的一部书,一部英雄史诗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瓦尔登湖》中自明的却是作者没有称颂任何他没有经验过的东西,除非是他所尝试过的,否则也决然不会被称为不可能之事。具体说来,所谓于高义处阅读是说“那些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才能阅读的,并且只有投入我们最高的警觉与情醒的时分方能阅读的东西”(Ⅲ,7);并且“存在着之于我们处境最恰适的字词,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倾听与理解,就将比春天与清晨更有益于我们的生活。”(Ⅲ,11)。在这部书中,清晨与春天都出现了,那么什么样的字词能够比它们更有裨益呢?但我们又看到,书中还有比如这样的句子“清晨是这样的时刻,此间醒来的我,黎明仍在其中。”(Ⅱ,14),我们会看到清晨也许并非由日出所带来,也许它根本尚未到来。如何获得和释放我们最为清醒的时分——无论我们所做之事为何——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整个《瓦尔登湖》的工作;而随之而来的工作概而言之便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读者来说,就是要探索什么谓之在高义处阅读,尤其是如果《瓦尔登湖》是一部英雄史诗般的书籍,那么阅读《瓦尔登湖》又意味着什么。相应的,对于《瓦尔登湖》的作者来说,他的任务就可以被概括为要去探索写作是什么,尤其是写作《瓦尔登湖》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难将这部书的英雄就是它的作者这一事实长存于心。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亨利·戴维·梭罗,那个被安葬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作家本身——尽管我这么说也是完全没有异议的。我指的是书中的“我”宣称自己是一位作家。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位英雄在太阳底下所进行的一切劳作,而写作这件事只是零星出现。我们需要费一点精力才能认识到,他的诸多活动实际上都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活动,每一个他用以定义它自身的字词,或者是描述他的劳作和他的世界的字词,实际上都服从于他文学著作的需要,这些字词定义并描述了他对文学的理解。如果这种说法看上去拉低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切身经验的身段,那也许也只是因为我们对于一部著作应当为何报以一种还原论的视角罢了。
“英雄之书”这一段落提及了荷马和维吉尔(Ⅲ,6),他们支撑着这一命名显白的意义,那就是“一部关于英雄的书”,一部史诗。作者将自己与英语诗歌中主要的那些传统联系起来,这一传统中充满着雄心勃勃的后裔,而至少从弥尔顿开始,这一传统萦绕着对于现代史诗的召唤,因为一部英雄之书以其中所蕴含的理念总是能顷刻间对民族教令破旧立新,而民族的诗歌资源就是最显然的证据。对于第一代浪漫主义者来说,也就是梭罗的父辈一代,最直接的史诗事件,也就是使得他们的文学史诗从中汲取力量的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在青春期他们拥有着全然的希望,但是成年之后,这种希望就支离破碎了。《瓦尔登湖》的作者举出了三个在他的时代最能产生共鸣的革命运动。对于清教革命他说到,这几乎是来自英格兰的“诸多新事物中最后的有意义的残渣”(Ⅱ,19)。为什么要说“几乎”?也许我们不必对这个问题太过执着,但是梭罗还是给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钥匙,在瓦尔登湖居住期间,他曾在关于卡莱尔的评论中写道:“对于这漫长的时日来说,来自英国的消息到底是什么呢?多年以后,英格兰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来说,我们有能得到什么呢?除非它能够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如华兹华斯的时代那般去经历它,在那里,少数更年轻的缪斯们正振翅欲飞……自从柯尔律治去世后,卡莱尔独自承担着这来自英格兰的承诺。”我们一般会把梭罗看成是愤世嫉俗者,他在一种私人的空想中宣称自己的遗世独立,然而正相反,他是如此坦然而公开的接受来自一个国家的承诺,并且持存着这样的国家承诺,以此来辨识一个来自那个国家最重要的消息,并且这样的承诺只在极少数作家的手里才能得到捍卫,这是梭罗更值得被我们聆听的心声。
对于欧洲大陆上持续燃烧的诸多大事件,《瓦尔登湖》的作者显然是不屑一顾的:“如果你能判断出一个人是不常看报纸的,那么对于他来说国外就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情反生,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Ⅱ,19)大概在同一时间,马克思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只是角度略有不同。在《雾月十八》中他似乎暗示,只有我们如报刊那样思考,我们才能将1848年(或者1830年)的事件看作历史的头条事件;它们属于剧评版面,或者在一篇讣告当中。但是用《瓦尔登湖》的方式来说,这样的印记也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绝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这场革命首先就发生自我们家附近,它开始于距离作家的案牍“南边两里路远”的地方,发生在我们这里“唯一有名的地方,康科德战场”(Ⅱ,10)。对于一个美国诗人来说,想要让这样的历史在本土生根发芽,美国独立战争自然是更为恰当的题材,它建构并将那些史诗事件容纳于自身之中。不过这样的做法还是有两点不足:首先,美国本身的史诗事件会使得这种吸收显得黯然失色;其次,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并未发生。殖民地的人民确实发动了奋起反抗英格兰殖民者的战争,并且他们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所赢得的战争却并非是一场独立战争,因为我们尚未因此获得自由;事实上我们并未全然的脱离出来,因为我们仍然寄居于英格兰所遗留下来的生活世界之中,我们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生活仍然寄人篱下。
至少我所理解的《瓦尔登湖》的作者想要谈论的正是这些,他以他的方式宣告了他自身第二轮“实验”的起航:“当我第一次用木头垒成我的居所,就这样开始夜以继日之时,如此的偶然,那就是我的独立日,那就是我的七月的第四天,我仿佛置身于1845年的这一刻,凛冬将至,而我的陋室未成。”(Ⅱ,8)。如果读者足够真心诚意的理解,至少如帕灵顿(Parrington)那样,当他们把梭罗描述为写下了“独立之超验宣言”的人时,这样的片段就在他们的背后辉映着。但是为什么作家要说这是一个“偶然”呢?也许仅仅是为了模仿美国关于什么是独立这个观念来临时候的情况吧,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又感伤的承认他无论如何不过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但他确实从一而终的坚持这些看法。那么他对独立的设想又是以何物为凭呢?很显然不是来源于社会这样的东西,这本书本就是在市侩俗事之上打孔。那么是来自于社会的信念与价值观么?这样说有一定道理,因为至少社会实践中的信念与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可能来源。不过作者要说的是一种内涵于美国本身之中的东西,是殖民地初民骨髓与灵魂中的东西。
起初就像初次见面时候的引介,我们在英雄自身的经验当中认识了他,关于他建造自己的房子的事情,他列出了两份长度一样的账单,一个关于此时之事,一个关于接踵之事。初民建造自己的第一个庇护所,他们要以此度过他们世界中的第一个寒冬,它看上去是如此的新奇(Ⅰ,57)。我们知道在那些凌冽的年月,新英格兰的先人们是如何用木头垒砌自己的居所。这样的原初的民族时间在《瓦尔登湖》中重演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当重做,而它的遥远又证明了重演的不可能性:探索并栖居于土地之上,把诸多疑问的种子播下,如此一劳永逸。这就是为什么在7月4日建起居所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个先人。
只要你是美国作家,甚至只要你美国人,你总要适时的回应这一事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殊途同归;我们也总会认识到美国的存在只存在于它的探索当中,而他的探索永远都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对自由着迷,总是想着用新的精神构建起新的人类存在结构,让它变成人类的惯习;我们也总将接受这样的预兆,即这样独一无二的契机已然永远的遗失了。《瓦尔登湖》的作者对此异常的清醒(我想,这就像《草叶集》的吟唱者,《白鲸记》中的幸存者)陷入一种恒常的情绪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这种情绪的在那绝对的希望之顷刻的道成肉身,同时也是那些绝对的挫败的道成肉身,是他自己,也是他的国家。在他的平铺直叙中必须直面这样的压力,并且在每一个时刻毅然决然的抵抗着它。只要还能,就必须在这样的压力下生活,在历史与天堂之间斡旋:
在任何气候任何时辰,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21)
这是对他的神秘主义的展开,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对通向它的道路的澄明,他也将这段叙述献给这样的道路。这就是“在手杖上刻下记号”的意思——他如此写道,他的写作和他生活彼此澄清了对方。《瓦尔登湖注释版》的编辑瓦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非常确定这里运用了鲁滨逊漂流记中辨析时间的方法,但是仅是如此并不能诠尽《瓦尔登湖》,因为它的作者通过时间的辨析所要意谓的,尤其是他所宣称的铭刻所意谓的绝不仅仅只是时间的流逝,而是时间自身的某种进展。每当他踏过那些在他谋划之中购置的连绵的田野,来到自己的木制居所,他说道:“我接下来要做的实验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要尽可能清楚的描述它。”(Ⅱ,7)当然,这里他所说的实验是关于建造自己的房子(而这也就是关于他的书的写作)。但是他另外的意味已然由字词自身显现出来:那便是此时所做之事亦是他的实验,是对此时的探索,是两种永恒的交汇(“上帝之伟大极显与现实之中”(Ⅱ,21))。这部书中最为顿开的时刻即是技艺与现时性的交融确证永恒之时,这就是该书结尾处那个来自克洛的艺术家的预言,由这些理念交织而成的纯粹平面,被铭刻在手杖之上。
我们说作者将我们带回到大移民时期这块大陆上第一批栖居者那里,这并不是要说我们对他的阅读只不过是在历史事件与木屋之间建立了一种表面上联系。如果仅仅是这样做,那么两边的重要性都会被我们遗漏,因为清教殖民这一事件的字面意义从一开始就掩盖了它的真实意义:这一事件是自我超越的行动,为的是让其自身得以存活;你可以称之为对于自由的超验性宣言(在“恳求约翰·布朗船长”中,梭罗赞颂这位船长时而是一位清教徒,时而又是一位超验主义者)。这意味着在作者这些人的成就中,在对这些人的描述中,私人、隐秘和孤立像其他一些东西一样都是成问题的。作者越是深入的探索清教徒们的独立意识,就越是在每一步、每一个字词中达到对清教徒的认同——不仅仅是对于他们的殷切的希望,同时也关于他们对自己背弃希望时那份深深的谴责,这样的两极逐渐成为了他们的哀叹(这样的立场对于美国自身的批判来说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基督教也是;美国人和基督徒总是倾向于说一些他们自身的行为中所蕴含的悲惨的背景,并且表述的比外人想象的还要悲惨。)他所认同的要远远超出移民事件的字面意义:这是一项实验式的表演,一场对于某一真理的公共的论证;去成为榜样,脱胎于那依然逝去的自己;去建造,正如他们对自己所说的,“一座山巅之城。”
这是我所理解的作者把自己定位于“据我邻人一英里远”意义之一。想要看的清楚,这个距离足够了。不过,紧接着梭罗又对这些聚集起来的浪漫主义元素进行了“文学取消”,为了遗世独立,也为了身处自然,在《瓦尔登湖》中,他对这种取消的描述是站在一种清教公理会(Puritan Congregationalists),这一视角属于教堂会众中的一员:一种可见的神圣。在这一视角之上,作者笔下的文字以及他的自身的行动,它们的观众是全然的共同体,他们聚集于此。对于梭罗来说,最初也是最终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学会如何对他们言说,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的问题是,他要如何建立自己宣告的权力。
当我在书中看到这样的句子时,我开始信任《瓦尔登湖》,我开始相信它对自身的意图有着准确认识:“如果你在事实面前毫不胆怯的直面它,你就会看到太阳的微光从它的两面袭来,像刀俎一般,它甜蜜的利刃将你彻底的于心于骨髓之间割裂,而此时你会欣然的接受你易朽的人生。”(Ⅱ,22)。我不能说这样的写作会随时随地的把我带向这样的终局。但是它确实经常如此,而往往如此的厚重,以至于我还来不及意识到它是否已经充斥我心,或是我已充斥于其中。我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外在于这些字词的主体,能够去感知它,去衡量它;而这意味着我通过作者自身的蜕变知晓了作者那些细致入微的特质,同时也定义了我心中的那诸多的观众,它们关涉于作者的特质,并且也由此创造。于是我理解了我是谁,在这样的路径上我应当如何被称呼,以及作者是如何确立了自己是谁,他在自己身上预设了某种身份与隐秘的关系。对于那些无法屈从于梭罗文字的人,或者那些无法彻底屈服于那种能够割裂他们的力量的人来说,我的主体看上去会是空洞的,甚至是怪异的。爱默生并没有真的分享到这样的热情,虽然他和其他一样知道梭罗是如此好的一个作家,在梭罗的葬礼上他的悼词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句子来自于他未曾发表的手稿。但是正如爱默生自己所说,阅读梭罗的写作更让他感到“紧张与艰难”。我发现对于《瓦尔登湖》的阅读来说这样的反应同时也是准确与根本的——但还不止如此。(《瓦尔登湖》的作者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有时我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检测我所知道的东西。”(Ⅰ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