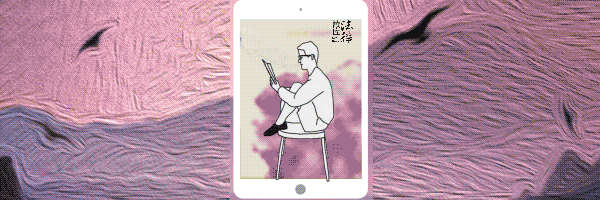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今天来说《西游记》五庄观的故事。
之前有读者评论说不要跟小说较真,又有读者说不要拿今天的价值观去评论历史上的事情。
我写关于西游记的文章,当然是较真,但不是跟小说较真。不较真的话,就不写文章了。而一写文章,就不好藏拙,难免露怯,比不上静穆养气来得圆满。
至于价值观,不好绝对地说,有亘古不变的价值观。但问题还在于,我们谈价值观,其实总未免流于抽象,甚至当说到“价值观”这个词语的时候,不同的人的理解和定义就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常要强调,尽量在基础概念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其他,虽然老生常谈,但要在一些基础概念上取得基本共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下的一些争论,似乎就是在重复以前,譬如可以对比一下鲁迅写于近一百年前的《论辩的魂灵》,会让人生出“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今天我拿西游记里五庄观这个故事,来就此谈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对于西游记的评论,近年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评论的视角就是
佛道的权力斗争
。
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看法,并不是时髦的新潮流。对西游记这部小说的评论,自来就有说是关于佛(学)教的,有说是关于道(家)教的,自然也有说是关于佛道两家的斗争较劲与妥协融合的。
从文化的根底上看,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外思想的斗争与交流是难免的。
在先秦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思想源流,主要是儒家与墨家之争,到后来墨家逐渐消亡,儒家被当权者利用,兴盛至近代。
但与其说只存了儒家一家,倒不如说,在学说思想门阀之争的表象下,真正斗争的两派,是老实之人与取巧之徒。
而这两派,无论在哪种学说思想或者价值观的门楣下,都是分别都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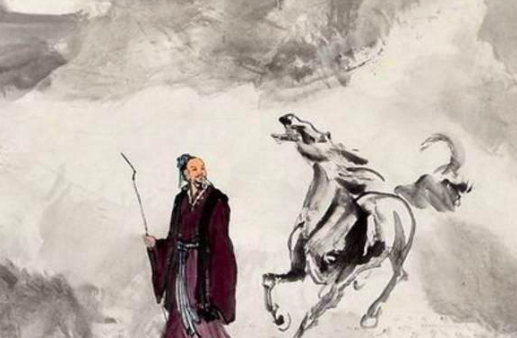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
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身符之用了。”(鲁迅《流氓的变迁》)
倒不信墨者之徒里真老实的死完了。其实,历史上,老实的刚正的儒者,也是侠士,常以身赴险,历代不乏其人,燃灯有续,但如风中之烛,总是处于弱势。但是,墨学式微,是后学以为道胜于术,而轻视“方法”“证据”“逻辑”的一个原因。
那么,之后便又有儒家(教)与道家(教)的斗争与交流。以致于汉初,儒者会被信奉道家的当权者关入猪圈。
其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本土的思想,遭遇外来的佛家(教)。
与异族思想自然免不了激烈的斗争,以致于韩愈上奏谏迎佛骨,跟皇帝说佛骨只不过是夷狄的枯朽之骨,忤逆龙鳞,差点被唐宪宗杀掉。
至宋明,又有所谓儒释道三教同源,三家合流。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掺入了许多佛家(教)的思想。知名儒士常与禅宗和尚交相往来,成为士林佳话。

到近代,再固执己见的传统人士,也不再会觉得佛家(教)思想是异类,更不至于导致朝议风波。
接下来,西学东渐,便是与西方思想的斗争与交流了。
我们看西游记里,镇元大仙去赴元始天尊之约,离开五庄观之前,交代清风、明月用人参果好好招待唐僧。
二童道:“师父的故人是谁?望说与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道号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等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做甚相识!”

清风、明月说拜佛的唐僧与自家是“道不同”,引用的却是儒家孔子的话。可见,在《西游记》作者心里,还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在当时,同是发源于中土的儒、道,互相之间已经不再视对方为水火不容的异端了。
五庄观一劫,
起因便是唐僧固执于表象
。在进五庄观之前,唐僧看到万寿山景色非常好,以为与灵山相近。倒是孙悟空让他见性志诚,不要执著于外在表象。
唐僧道:“悟空,你说得几时方可到?”
行者道:“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但是,到了清风、明月把人参果端出来给他吃,他之前自己都说五庄观真是西方仙界,也知道今岁年丰时稔,却执著于人参果的表象,质疑五庄观在丰年作荒吃人。
而此前,连一向不说话的沙僧也说:“此间虽不是雷音,观此景致,必有个好人居止”。孙悟空则说“这里决无邪祟,一定是个圣僧仙辈之乡”。
可见,“不应吃人”,在唐僧这里,就只是一个抽象的价值观。在他眼里,自己是“道”也就是“正确价值观”的守护者,而与自己对立的五庄观则是让人吃人且不以为错的地方。
他的这种对别人的质疑,有违常识在先,未详究细理在后,便以恶意度人。根源在于:没有跳出自己。
但是,跳出自己,的确是很难的。孙悟空有本事分出元神,跳出自己。但当他用柳树变成的化身遭到鞭打的时候,他的真身仍会打寒噤。
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个寒噤道:“不好了!”三藏问道:“怎么说?”行者道:“我将四颗柳树变作我师徒四众,我只说他昨日打了我两顿,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罢。”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
在孙悟空还被压在五指山下的时候,在真的历史上,倒有所谓的蛮夷,有时能跳出自己的。这倒是真正的自信而不是自卑,是自尊而不是自亵。
“一百多年前的苻坚留下的影响如今还在,这就是世界之义。苻坚认为,在民族差别之后,还有人类的文明,而把人民引导到文明的最高水平就是政治。既没有胡也没有汉,只有文明。如果现在文明的最高水平是汉人的一套,让它为我所用才是人民的幸福——唐灭亡之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的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