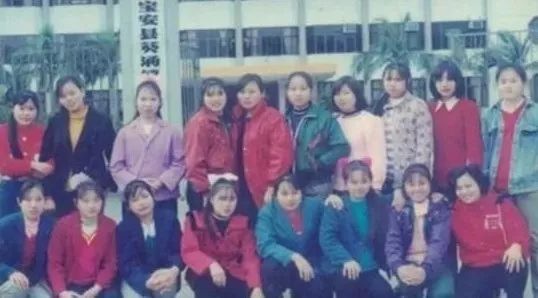18年以来大的变化,我觉得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美贸易战之外,还有四个方面的感悟,对我来讲还是印象很深刻的。第一方面就是16、17年的棚改货币化翻财政驱动的一轮经济很强的复苏周期以后,在总杠杆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17年的名义GDP已经到了12%的高位,18年其实经济是从一个高位,受资产新规的影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信用政策收紧的影响等等,出现了一个台阶式的下滑。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各个行业中的最头部的企业出现了非常强的穿越周期的能力,从各个产业中的头部企业在市场份额,净资产收益率、成长性、现金流含量等诸多指标上,都出现了远远超越行业均值的一个现象。
这个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并且延续到了今年的疫情期间,因为疫情期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一季度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危机时刻,但是我们长期跟踪的这些最优秀的企业的免疫力是很强大的,基本完美地扛过了这次压力测试,高信百诺根据五个维度选择了中国,我们认为最有竞争力的50家头部企业,编写了一个内部竞争力指数,指数每个季度的财务数据,我们都会跟整体的行业和整体的全A有一个对比。我们确实发现这50家最有头部竞争优势企业创造Alpha的能力,就是超越行业平均的能力,在18年以后有一个很显著的提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利率环境方面,塔勒布讲过未然历史,可能我们并没有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低利率低增长的一个年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可能现在科技和资本两大阵容绑架了全球的产业阶级,而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举一个数据,美国的FAAMNGT,T是特斯拉,七大科技型公司的就业人数在2019年是130万,新增就业大概每年在20万左右,但是全美的劳动力人口是有1.65亿,也就是说7大科技型公司的就业只占全美所有劳动力人口的不到0.8%,但这7家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是非常聚集的,这7家科技型公司占纳斯达克市值的比重超过了40%,他们的税后净利润,因为科技型公司有时候利润分布在远端,并不是现在,即使我们算19年的净利润也占到了全美上市公司的接近10%了。
所以我们发现价值创造以一种巨大的不对称性来展开的,数字经济巨头的崛起和资产泡沫的持续会进一步加剧传统部门居民薪酬的分配的不均匀。所以很多人老担心通货膨胀的出现,其实我们恰恰可能会有一种担心,通胀不会那么轻易的出现,因为分配不均在资本和科技两大阵容的挟持下会进一步加剧。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时间很久的低利率低增长低要素生产率的年代,资产估值的泡沫化很可能会不基于我们的历史经验为主导。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事就是19年中国科创板的诞生诞生,中国的资本化率在科创板诞生之后,出现了非常快速的打造,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本质是中国的监管层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跟定位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创新型科技型公司的融资需求设置了比较高效率的一个快速的绿色通道。随着注册制的实施,我相信中国未来两年的上市的数量和速度都是全球之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考虑港股红筹股和中概,中国的证券化率其实已经超过100%了,A股加中概加红筹已经超过了中国GDP的总量,所以我感觉这件事儿也是很大的。资本市场的定位,包括创新型企业的大量优质供给的出现,也给我们的投资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
最后一点是18年之后,外资在非常深度的参与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固定收益债券类的市场,并且我感觉这个趋势未来5~10年会确定性的持续下去,而且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迫切性会很强。第一,其实做一道对比题的话,会发现中国是全球很罕见的文化高度统一的一个大陆型经济体,文化高度统一很重要。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文化统一跟文化分歧可能在政府的管理成本上差距会很大。另外中国有广阔的消费人群,有高效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的领先于全球的一个创新场景,给我们投资人提供了很丰富的产业供给。所以我们也跟很多外资的机构有过交流,首先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的欲望非常的强烈,他们也做了一道对比题,觉得从高质量高回报稳健增长的角度,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其实中国市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再加上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股票资产和海外市场的相关性比较小,对很多海外的投资机构分散组合风险和相关性的波动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投资理念的一个转型,方向是明确的,A股目前向成熟市场靠拢,这个方向一定是明确的,但这里的节奏会有一定的差别。我们公司是绝对不看任何基于相对估值的东西的,PE、PS、PEG、EV/EBIT、PB/ROE这些相对估值方法,可能都是绝对估值DCF模型的一个简化品。我觉得首先可能外资还是比较看重绝对估值;第二点我觉得外资可能对于资产的久期的长度和治理结构的优秀性看得很重,而国内可能相对更看重股票资产的短期的增长如何,当然我也看了很多基金经理的采访,这几年国内也在向比较成熟的公允的一些投资方法理念去靠拢。所以我觉得可能外资跟国内的选股的一些东西还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不会像10年前那么的大。所以大家也都慢慢的理解了,增长的质量的重要性,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包括资产的久期的长度的重要性等等。
关于估值与核心资产的理解,在我们看来,资产定价方式有唯一性,就是DCF模型,但并不是用这个模型去精确的计算一个结果,而是将DCF当成一种深刻理解估值的思考方式。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反常识的认知。首先,企业经营久期,即DCF模型中的永续部分对于最终估值结果的解释权重很高,可能超过50%,所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能具备永续的部分就非常重要;其次,当分母端折现率从高位向下调的时候,如果从10%调到8%和从6%调到4%,虽然都是下调了200个bp,但对估值结果的影响差异是巨大的,折现率越低,下调的时候估值变化越敏感,而当我们用自由现金流折现的思考方式去看待资产定价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敏感性的角度来看,折现率对内涵价值的影响很大,其中的关键因子就是利率,当利率在很低的水平下,具有长期经营确定性资产的内涵价值,反映到估值上的弹性影响会特别大,而今年以来疫情的意外出现并没有让利率变成均值回归,反而加剧了利率的继续下行,进一步推升了估值膨胀。所以在当下这个低利率环境中,如果市场预期利率有进一步向下的可能或者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估值泡沫化;还有就是短期增速其实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权重并不是很大,特别相对于永续部分而言。核心资产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标签化的概念,我们定义的核心资产需要满足极致的生意模式,显著的竞争优势,优秀的治理结构,以及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等特征,这种情况下的核心资产,目前并没有明显的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