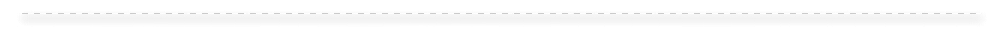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涌现出大量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本期推荐2015年发表在
The China Journal
上的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一文。作者将研究中国农民工的传统路径称为“征服模式”,宿舍劳动体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论点。基于对深圳工人信件分析和民族志研究,作者认为,今天的农民工在住房、伙食、时间安排、发展期望、维持社会关系方式等方面,面对着迥然不同的外部环境。但是,年轻的农民工仍然会调用根植于家庭和农村的社会关系,来应对日常困境。农民工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旧有方式的断裂,而是夹杂着延续与变革。
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农民工的传统路径是
“征服模式”
(subjugation model)。这种模式认为,农民工屈从于各种结构与制度的力量,体现在中国的户籍政策、许可证制度、血汗工厂,以及基于性别和地域/亲缘关系的歧视。这些结构和制度力量,反过来又为工作场所滋长剥削和压制的车间文化提供了条件。按照这一路径,中国重返全球经济,以及国家吸引外资的现代化战略,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工的困境。征服模式中的一个论点是“宿舍劳动”(dormitory labor)。Pun Ngai和Chris Smith着重论述了“宿舍劳动体制”的独特性,认为这种劳工体制是为了全面控制农民工的生活。
作者观察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邻近工厂的社区租房。虽然征服模式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但却不能延伸至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1990年代的工厂农民工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文章主要探讨了工人生活方式的具体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征服模式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1990年代初和2000年代末的工厂农民工进行了比较研究。为考察1990年代初深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特点,作者分析了来自深圳致丽玩具厂工人的76封私人信件。1993年,一场大火吞没了工厂,造成80多名工人死亡,严重烧伤的有数十人。死去工人的信件被工厂丢弃,后被学者发现。其中有些信件是致丽工人撰写的;但大部分信件是在其他工厂工作的亲友寄给致丽工人的。许多信件包含了工人社会和物质环境的细节描写,工人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婚姻和恋爱,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同乡、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同时,文章还引用了潘毅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和李静君《性别和华南奇迹》(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的数据,这两项都是对1990年代深圳工厂的民族志调查。
2010年,作者在深圳玉镇进行田野调查。他与三名在深圳制衣厂工作的农民工合租了一套房,共同生活了6个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作者试图捕捉工人态度的转变,包括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婚姻计划和职业期望。另外,为更完整地把握2010年农民工的处境,作者对六家制衣厂的工人进行了厂区门口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89份。
作者从宿舍、工时、伙食消费、社会关系、职业期望等方面,刻画了1990年代初深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特点。有关宿舍劳动体制,作者认为致丽厂具备1990年代初中国外资工厂的特征,利用特殊的空间安排,占有工人的劳动力。在工时方面,深圳普遍的工作日至少12小时,超时加班被视为正常工作日的一部分。雇主还会对工作迟到的工人进行惩罚。
我很开心,3月25日(1992)收到了你寄来的钱。妹妹,其实你不要再给我寄钱了,我终于领到工资了。(1992年)3月15日,工厂管理部门支付了到1991年12月的工资。我拿到了140元。我已经寄了100元回家。我准备将下个月的钱寄给哥哥。妹妹,请保管好并存一些钱自己用。离家远,一切都要花钱。——引用致丽工人信件
作者总结到,1990年代初农民工生活的特点是:贫乏的物质生存、严苛的工厂节奏和孤独感。女工尤其受到僵硬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关系的困扰,无法逃脱返乡命运,在城市工厂生活多年之后还将再次成为农民。
对2000年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描述,作者从村庄治理、社区出租屋、闲暇时间、工作时间、城市消费、职业期望、地方网络、对家庭和婚姻的态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政府和本地村民对农民工的态度略有转变,虽然农民工仍无法享有任何当地的福利待遇,但政府不得不正视他们的存在,并为他们提供公共设施。农民工地位的提高,是由于他们庞大的数量,以及他们为村里创造的财富。
虽然工厂也不再有严格管控的宿舍体制,但为逃避规制,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生活在出租屋中。年轻工人不喜欢宿舍门禁等“时间规制”,认为这些障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作者对一位合租者一天的日常时间安排进行了白描,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工人的平均工时约为10-11小时。与1990年代的工人相比,现在大多数工人的闲暇时间要多一些。
虽然有生产旺季和倒班工作,但今天的农民工并不像1990年代初的工人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对“自己”的时间有更多控制,即下班后的闲暇时间。他们也能够与工厂管理层协商他们的休假时间。
中国农民工沟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手机和网络的使用。工人频繁使用信息技术,不仅为了与亲友保持密切联系,还可以分享劳动力市场信息。虽然工人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缺钱。像1990年代的工人一样,借钱有可能制造很多问题,尤其是亲戚,或有亲缘关系的同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
1990年代的工人只想暂时在工厂工作,以后还是会回到农村。与此相反,今天的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梦想自己能够从普通的产线工人转变为承包商或小工厂主。
农民工对地方网络的持续依赖并没有减弱,尤其是让男工和中年工人面临沉重的家庭负担。
因此,与以往关注女工的研究不同,本文提出,与其说长辈是家庭权威体制的行动者,不如说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不论男女,许多农民工并没有按照农村习俗,在20多岁结婚。虽然年轻农民工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态度日益凸显,但他们仍要与传统农村的价值观相抗衡。
与1990年代初的农民工相比,2000年代末的农民工摆脱了边缘化的生存、工厂宿舍的禁锢、社会孤立和听天由命的状态,工人有更多的生计选择。然而,
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旧有方式的断裂,而是夹杂着延续与变革。
工人的新式生活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并非完全被抛弃,而是对2000年代末的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工人的世界观和社会关系网络并非完全“城市化”,而是类似于农村小镇。第三,移民通常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临时的,这促使工人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更强大的力量和制度变革,推动了农民工代际群体间行为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宿舍体制被逐渐削弱;同时,政府对厂区外农民工流动的严格管控也放松了。
征服模式隐含的假设是,中国农民工的社会和物质生活受到不同形式权力施加的影响,而只要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简单加总起来,就能解释所有的支配效应。但作者提出,各领域的权力集合对农民工生活的影响,只有在特定时间段内才是真实的;二十年来,宿舍体制的重要性逐渐被工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所淹没。工人不断上涨的工资、新的沟通方式和技术变革的爆发,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工人提供了从简单的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的机会,也使得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发展日渐分明。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需要将厂区外的生活情况纳入进来。
文献来源:
Kaxton Siu (201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 No. 74, pp. 43-65. DOI: 10.1086/681813
文献整理:钱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