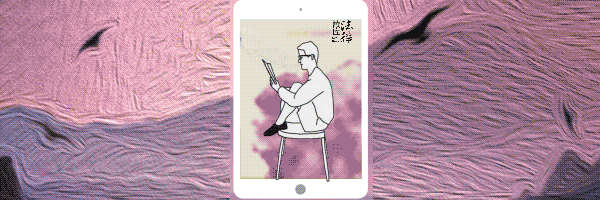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编者按:法律读库近日收到上海政法学院大一学生袁庆婷同学的投稿。我们每天接收大量投稿,这么年轻的作者还是少见。为了鼓励年轻人的积极性,编辑考虑约请专家点评几句,没有想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欣然应允做了点评。相信此举会令这位大一学生的成就感放大,说不定从此她就树立了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的远大志向。

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思考
作者:袁庆婷,上海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大一学生。
前段时间在法律节目上看到了两个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案件,这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以下是这两个案件及本人一些粗浅想法,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思考。
薛某,25岁,是一名网络技术人员,在A公司任职期间因不满其部门经理而擅自篡改了该公司营业网站以报复,导致A公司利益受损三万元以上;薛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黄某,23岁,是B工厂原车间工人,工作期间为陷害上级马某使其不能按时交工而往工厂里的涂料中加凝固剂。经调查此事是黄某所为,其被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所幸后马某补齐涂料按时交工避免了工厂更大损失。
看完这两个案件后我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要件的思考
这两个案件让我联想到一节视频教学里讲到的一例:某人对他人网店的商品"反向刷单"被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破坏生产经营罪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讲课者认为该条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在现实空间的物理破坏,按照同类解释、体系解释的解释方法,条文里的"其他方法"也应指的是物理破坏手段,这个案例不应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可以考虑定毁坏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若后一罪名也不成立则此人不能被定罪。
本文开头的案例一薛某也是通过虚拟空间的网络技术破坏生产,那么按该讲课者的观点,她的行为则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客观要件,也就无法被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
我将疑惑告诉本校一位老师后,老师则提出当今网络时代,在大量的数字化且实际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财物出现的情况下,传统观点是否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观点。
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有其道理:
前者
用按同类解释、体系解释的解释方法解释法条,在刑法条文自身未变动的情况下,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审慎定罪;但这种解释比较传统;
后者
则考虑到了时代因素,用扩张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也可将其解释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然而这或有解释限度不明之嫌。
本人认为这跟该条文自身陈旧有关,在说明破坏生产经营的手段时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且列举的犯罪手段都是物理手段。严谨地按同类解释看,确实不能把虚拟网络行为纳入其中。但法律应与时俱进,在现实生活的信息时代中,非物理意义上的诸如网络技术的手段也能造成生产经营的损害。
简而言之,本人认为法条内容应紧跟时代,不致使法条陷入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矛盾观点的境地,这也能更好地将定罪判刑规范在罪刑法定原则,彰显法治精神,促进法治进步。
第二,对案例一、二中行为入罪化的质疑
犯罪的含义之一是"危害社会的、为刑法所禁止的,而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案例一、二中两人行为皆是在刑法条文上推断定罪的,也就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判刑。但令我不得解的是,这种行为真的严重到犯罪了吗?我的观点是,这不足入罪:
首先,它的社会危害性不够严重。
我们知道,当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时,这种行为才会被纳入刑法,定为犯罪行为。而像案例一、二中两人的行为虽然的确给经营者带来了损害,但严重到要用刑罚惩罚他们吗?
其次,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启用法律中最严厉的刑法。
这两个案件里他们都是造成了经营者财产损害,但从解决问题的目的来讲,财产赔偿的民事手段、开除职员等方法便已足够弥补经营者造成的损失。且案例二中,黄某给工厂带来的损害几乎为零,但仍被刑事处罚。
再者,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
案例中尽管两人都被判缓刑,但却留下了案底。薛某和黄某都是二十出头刚入社会的青年,年纪轻轻便背上了案底,这无疑是他们人生惨痛的教训。就这两起案件看性质并不非常严重,用非刑罚手段也能起到教育惩戒作用;可用上更加严厉的刑罚手段虽然让他们不敢再犯,但相对于给他们的人生添上刑事污点便显得有失法律的公平。
这两案只是个案,至于对破坏生产经营的所有行为是否入罪化的态度还待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通过个案联想到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行为入罪化存疑的情况,刑法严厉,入罪化谨慎才不致让公权力伤及无辜。
以上便是我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思考。

张建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