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问西东》最近正在热映。这让被认为是抗战期间“衣冠南渡”、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火种”的西南联大,再次受到关注。“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经历了什么?”“当年学校中的师生的生活怎样?”这样的问题成了不少人关注的话题。而这一切都要从1937年说起。

资料图:2017年11月1日,游客在西南联大旧址前留影。当日,正值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日。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战局急转直下,长沙也不再安全。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往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学校师生分几路入滇。其中一路200余人步行横穿湘黔滇三省,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步行团的师生一路尝尽艰辛。旅途刚开始,很多同学脚上就“都磨了泡”;途中不时遇上阴雨天,更是狼狈。“草鞋带起泥巴不少……曾先生(指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之半截泥巴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当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步行团师生在旅途中。图片来源:《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截图
途中,风餐露宿更是难以避免。张曼菱编撰的《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记载,步行团常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也曾宿营荒村野店和破庙。
吴征镒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步行团行至盘江、夜宿安南县时,便是一例。“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
即便是在这样的旅途中,这些年轻人依旧充满活力。抵达安南县的次日晚,步行团的学生们还在县城里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两日后,吴征镒又写道:“又二十里经芭蕉阁,风景可观。复十五里上坡到普安县。全日行五十三公里……路上同学大肆竞走。”

资料图: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外的西南联大校徽。中新社发 刘冉阳 摄
一路西行至当年四月末,200多名师生抵达昆明。全程随团步行的闻一多当时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
但事实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闻一多后来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也坦言,“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饭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饭菜确实寡淡。有当年在此求学者这样回忆联大的伙食,“早晨是稀饭,用煮蚕豆作菜,午饭晚饭是多土多砂有壳子的红米。米饭也不够的,因此大家围着饭桶,硬把胳膊向里插,菜是清水煮的萝卜白菜,没有盐,更说不上油珠子了”。
这一年的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校舍不足。
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

资料图:西南联大校舍。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这正应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这些校舍非但不是大楼,甚至可称是简陋了。即便是1939年落成的“新校舍”条件也极为有限。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沈克琦用“土墙泥地稻草顶”形容之。“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
还有学生在一篇名为《我住在新校舍》的回忆中写道:“虽然墙上的白粉大都脱落,而天花板上全是灰尘蜘蛛网,同学们大都还在寝室里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赏的明星和pin-up girl来补偿这破烂于万一。而床上或是桌上照例是东一堆,西一堆,臭袜子和笔记本揉成一团,从没有过整齐清爽的时候。”
虽然“每年都要修补一次”,但这样的校舍“一碰上倾盆大雨,半夜里床上就可能成为泽国”。“油布,脸盆都成为防御工具,打伞睡觉的事,也并不稀奇。”

资料图: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教室旧址。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不少迁滇的师生仍将这里看做“故京”。
和闻一多类似,当时任教于联大的陈寅恪有诗云,“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南渡”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寓意。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即有此句:“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与其说是“景物”“似故京”,倒不如说是寓居此地师生的心境的一种反映。
与此同时,年轻人的生活是“热烈,痛快而鲜明的”。
初版于1946年的《联大八年》序言中这样记载,“到昆明以后……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咏,壁报,集体旅行,集体学习都蓬勃一时”,上课和其他的习作也“在学校严格的规律下照常的进行着”。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虽然图书馆的条件并不比校舍好多少,阴雨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但当时“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排队预约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长”。
从流传至今的回忆文章来看,当时学生去图书馆堪比现今的“春运”。“图书馆是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天未黑,馆外便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或是手指头挤破了。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的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那时,自修是天经地义……”
而无处读书的学生只好到附近的茶馆去看书。李政道曾回忆,“钱很便宜,老板娘给你放上水,再在炉子上坐上壶,就悄然而去,不打扰你看书。一坐就是一天,也没有人来赶你走”。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本为后方的云南成了前线。一时间,昆明也开始遭到日军空袭。
在费孝通的回忆中,当时在昆明“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他还总结了一套经验。“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
1941年,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当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此次共征调70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又有400余人应征。
在联大从军学生题名纪念碑上,刻有殉职的五位烈士的名字。他们有的在抢渡怒江时牺牲,有的随士兵冲锋时牺牲。
而事实上,此前西南联大已有一次“从军潮”。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就有295人申请参加抗战工作。其中不乏牺牲者。如经济系三年级的何懋勋当时在鲁西北任游击总司令部抗日挺进大队参谋,1938年8月中旬在济南齐河被敌人包围牺牲。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是年,200多位联大同学报名参军,到青年军二〇七师炮一营入伍。当年11月,西南联大理学院、工学院又有14位同学考取了青年军征集的空军甲种领航兵种。这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的第三次“从军潮”。

西南联大旧影。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统计,西南联大中有“从军旅者八百余人”。不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次年5-7月,联大学生分批乘卡车离开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使命宣告结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迄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为止,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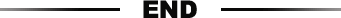
募格科聘,一个科研科技领域专业招聘平台
「募格学术」现正式向粉丝们公开征稿!内容须原创首发,与科研相关,一经采用,会奉上丰厚稿酬(300-500元),详情请戳。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mugexue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