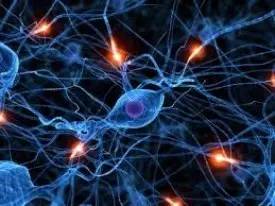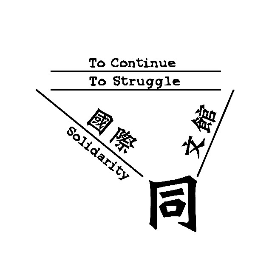最终,Berivan哭着离开了办公室。尽管提到了她烈士父亲的牺牲,甚至用了“鲜血”这样神圣的词汇,她仍未能建立一种能够让她脱离困境的道德权威。相反,她敏锐地意识到,基于她父亲(以及其他烈士)在革命斗争中的牺牲而建立的道德等级已经消失。那么,她父亲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次交流是我在田野调查期间遇到的诸多深刻的矛盾之一。这些例子展现了革命事业与库尔德治理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对一些人来说,民主化时期需要以革命原则为指导:基于英雄和重大牺牲优越性建立的道德等级,以及包括自卫在内的争取自治的政治斗争。而另一些人则欢迎这种变化。对ta们来说,新的库尔德革命政治需要展现处理日常事务(如垃圾处理)以及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如家庭暴力与性别平等、生态生活与基层民主)的能力。像Berivan这样的烈属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忽视,价值被否定。在2011至2015年的Diyarbakır,这些裂痕在库尔德革命社区内部演变为激烈的两极分化的语言,在库尔德运动终于获得了权力的时候破坏了长期的友谊和同志关系。Ta们的确赢得了市议席,但革命的成果呢?
库尔德研究的学者通过综合而多层次的方式分析了民主化时期显现出的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差异,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紧张与失望情绪。Zeynep Gambetti(2009)将库尔德治理置于去殖民化脉络中,指出了早期运动被新自由主义侵蚀的迹象,这种侵蚀塑造了新的阶级身份。Cuma Çiçek提到,民主化议程未能解决运动中民族与经济集团之间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Çiçek 2017, 107–27)。Bülent Küçük(2019, 7–10)展示了这些经济紧张如何反映并受到两种政治主体性(激进化的青年与合法化的中产阶级)的影响。他还强调了PKK将其暴力策略强加于民主政治所引发的紧张局势。Umut Yıldırım(2019)则展示了库尔德治理在新自由主义结构和去殖民化双重议程中,同时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创业家主体性(neoliberal entrepreneurial subjectivity)的渗透与“失调”的情感状态。
基于前人的研究,我聚焦于围绕这一新政治项目的道德困境与不确定性:如何将革命牺牲的价值转译为重塑社会与政治的民主斗争?正如本民族志所展现的,这种转译不仅仅是政治议程的转变,而且是库尔德运动中价值观、主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深刻变革。在Diyarbakır的日常生活中,革命牺牲在当下的对应关系将如何体现?谁来完成这种(对应关系的)转译?Ta们将如何在民主项目中塑造新的政治?
牺牲是道德等级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早期的人类学理论颠覆了将牺牲视为献给神的礼物的古老观念,认为不存在“免费的礼物”(Mauss 1992)。赠礼与牺牲开启了基于道德和社会债务的关系;“或许没有任何一种牺牲是不带有某种契约元素的”(Hubert and Mauss 1981, 100)。通过牺牲仪式,社会形成一种“更广泛的、非个人化的且超越生命的统一体”,并将其“生命力”塑造成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结构(Bloch 1992, 42)。牺牲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共同体帮助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主权国家控制并产生影响,使其臣民以越来越广泛的方式紧密地连结在一起(Rashid 2020)。
与这些早期研究相反,近期的研究拒绝从功能的角度思考牺牲,而是聚焦于其破坏性、解构性和革命性方面。这些研究认为,过分强调互惠性会将一种潜藏的债务逻辑植入社会关系中,从而排除“真正的”赠与或牺牲的可能性(Derrida 1992, 24)。批评者们认为,礼物和牺牲中存在一种无法化约为债务的过剩性(Derrida 1995; Bataille 1991)。赠与可以有意义,也可能看起来像摧毁或失去,这一原则排除了交换性或互惠性(Bataille 1991, 68–70)。牺牲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它从现有现实中创造出一种绝对的断裂,并释放出一种无法预见、无法控制或无法管理的转变。牺牲引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从而蕴含政治干预的潜力,其本质上构成了一种革命行为。
尽管这些关于牺牲是否可以被偿还的观点都从仪式内部探讨这一问题,我建议将焦点转向对其时间性的探讨上。牺牲存在于离散的、变化的,有时甚至是重叠的时间性中,这些时间性与其背景、参与牺牲的行为者、牺牲物以及被视为神圣的东西相关。这篇民族志中涉及两种时间性:第一是按时间顺序的时间(从紧急状态到民主化时期),第二是神圣时间(革命性牺牲作为神圣物的中心性及其去中心化)。殉道是最具戏剧化的牺牲形式之一,相关的研究大多从其神圣时间的视角进行分析,即通过牺牲创造连结,释放被认为是神圣的能量,并将暴力转化为一种“形成”(Feldman 1991)。然而,神圣时间与按时间顺序的时间既有区别,也有融合,同时两者也相互关联。例如,马达加斯加人以“巧妙”的方式在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当下的时间性的牺牲之间交替,以化解紧张局势并重塑其社区 (Cole 2001, 197)。在安哥拉,现在时作为:“一种对乐观主义的邀约和变革的具体化”,被用于革命者的自我牺牲实践中(Blanes 2021, 136)。按时间顺序的时间,特别是现在时,在人类学理论中对牺牲的时间性的探讨中是最被忽视的,它通常被归入神圣的过去和神圣的未来。然而,替代性的当下为神圣时间性投下了不同的光芒,重塑了对损失、债务和革命的评价。
在本文中,我使用牺牲的“后世”(afterlife)来探讨民主化社会中的道德困境。在按时间顺序的时间中,后世指的是由于冲突的放缓而带来的致命损失的不确定但逐渐滑移。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因为牺牲的死亡从未完全消失,而生存、常态和未来的观念开始浮出水面。在神圣时间中,牺牲的后世指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后世:在紧急状态/民主化时期的历史时间内对库尔德运动的道德/社会时间秩序所带来的变化。它既包含“胜利”,也包含这种胜利并未完全显得如愿的挫败感。为了探讨这些后世的混乱性,我转向了人类学中关于“后世”的最新探索。
“后世”一词复苏了那些被认为已死的、失去的或消失之物的幽灵。人类学家探索事件发生之后挥之不去的存在或“余音”(hauntings)(Gordon 2008),这些“余音”会挑战我们对事件及其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理解(Schäfers 2020; Navaro et al. 2021)。Alice Wilson(2023, 3–4) 研究了杜法里(Dhufari)革命的价值观、理念、社会网络和希望,这些“持久的遗产”即便在革命失败和威权压制下仍然存在。Wilson(2023, 13)拒绝通过静态的成败视角来解释革命的后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潜能,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断延展出新的经验和见解。在土耳其,Aslı Zengin(2019, 92–93)追溯了酷儿的后世:跨性别性工作者女性遭受仇恨犯罪,正是她们的跨性别朋友们通过照顾她的遗体、为她哀悼,并在她们之中创造一个家和酷儿家庭来为逝者创造后世。通过这种照护,跨性别女性从她们的亲密生活中培养了自己的主权形式。无论是一场运动、一种愿景还是一个被宣告死亡的人,后世都表明了它们以其他方式的延续,这种延续往往带有颠覆现有秩序的批判性洞见和潜能。
牺牲的后世指向一种潜能,它为牺牲的损失以及它旨在再生的神圣赋予新的意义。在库尔德人的案例中,我们在牺牲的时间顺序时间性和神圣时间性的交汇点——即“胜利”中——看到牺牲与其仪式形式中的分离。Berivan和其他烈属的经验则是,ta们亲属的牺牲未能积累成一种对革命未来的希望、一种革命社区的共享价值,或一种对世俗生活的掌控力。Marlene Schäfers(2023)展示了烈属普遍在意通过烈士的照片形象来为其建立后世。这些“潜在”的图像携带了牺牲再生性、霸权性但又不确定性的力量,它既可以投射主权,但也会给这种投射注入矛盾。牺牲不再意味着“诞生”(Lambek 2007)或“同一性”(Holbraad 2014);它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和混乱。
无论革命性牺牲的去中心化多么令人不安、衰弱和沮丧,牺牲在事后都会延展出新的形式。失败,或者说“无法感受到的胜利”,开启了多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被新自由主义共谋、革命怀旧或无望的极化叙事所笼罩。Catherine Alexander(2023, 24)将失败描述为“一种超越或融合尺度与时间性的过剩与拒绝模式,从工作扩展到亲属照护,威胁着将道德失败的指控反击给原告,且在时间与空间中产生回响”。牺牲的后世帮助革命者将自己的时间性、脆弱性和抱负强加于革命事业之上,并指向新的革命可能性。
革命时间性的扩展,通过牺牲的后世,打破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线性承接的逻辑(Walton and İlengiz, 2022),这种线性逻辑也深深根植于革命计划之中。后世的开放性允许时间在现时的干预下得以保留,从而避免被神圣时间所吞噬。通过牺牲揭示的多重时间性(其中一些或许是平凡的)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革命政治——它不仅是断裂的事件,更是缓慢的、逐步展开的过程,以一次牺牲为单位,不被其加速的时间性所吞噬。在这些时间性之间,以及政治与道德领域之间,甚至在革命与其“他者”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这些互动滋养了对革命未来的乐观想象,因为它们是“那些不可能却仍然发生的事件”(Al-Khalili et al., 2023, 12)。
在库尔德运动中,这种互动使牺牲的多样化表达成为可能,并对推崇英雄式的重大牺牲的道德秩序,以及新的革命政治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世中,我们谈论的是多元性 (plurality):“革命遗产的经验与革命的经验一样具有交叉性”(Wilson, 2023, 10)。同样,从牺牲到后果的转译形式也如对革命的经验与愿景一般多样。受伤与死亡的经验与不同的脆弱性及照护它们的方式相得益彰。生命的概念也因此多样化:它不再仅被想象为揭露主权权力弱点的武器(Bolton, 2023, 165),而且还被想象为一种充满激进脆弱性(radical vulnerabilities)、连结性(connections)与关系性(relationalities)的世界。
通过牺牲及其遗产,本篇民族志展示了革命如何超越正式权力与秩序的结构,深入到重塑世界的道德、亲密与日常领域。这项调查反映了我在民族志研究中的转变。我于2011年来到Diyarbakır,进行为期11个月的田野调查。在那里,我跟随我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朋友与熟人,她们奔波于一个又一个非政府组织,同时也在一家人权机构做志愿者。随着时间推移,我的田野调查逐渐从非政府组织办公室、仪式与抗议等传统政治场所,转向更为平常的空间,例如美容院、体育中心、咖啡馆与家庭。在这些地方,我目睹了人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牺牲、失落与希望,自下而上地培养出一种新的革命文化。牺牲仍然意味着为更大的事业放弃某些东西,但这种牺牲的形式、时间性、情感、空间与规模更加多元。这些交叉的现实与脆弱的库尔德-土耳其和平进程(2013–2015)重合。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简要展示这些创造牺牲后世的初步尝试。
民族志研究涉及转变,它也改变事物。在Diyarbakır,我第一次不得不思考,拥有库尔德母系血统对我意味着什么。此前,这一事实既不重要,也不值得骄傲。我一直将其视为家族历史中一个被压抑的部分。在田野中,我的亲密朋友视我为库尔德问题方面的新手;然而,其他人却正确地从我身上看到了许多特权的迹象:土耳其身份、在西部小城镇中由国家公务员父母抚养长大的共和主义教育背景,以及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在研究期间,我感到自己无法完全认同这一遗产,但也不能忽视它在这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环境中缓慢而亲密地显现出来。这种疏离感让我远离库尔德运动中更为积极和激进的部分,却使我能够与运动中的普通成员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我们各自的距离中,我们找到了时间和空间,讨论ta们在民主化进程中应对困难问题的经验,而这些对话构成了本文的基础。
革命
THE REVOLUTION
在库尔德工人党烈士崇拜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牺牲在其中交织:牺牲作为建构秩序的“无赠之债”(debt without gift)以及牺牲作为绝对的赠与的“无债之赠”(gift without debt)(Bolton 2023, 164)。前者体现在库尔德工人党的话语中,这些话语围绕着“我们对烈士的债务”(şehitlere borcumuz)展开,这一理念鼓励了新的游击队员和激进分子继续作为革命事业的牺牲主体存在;后者则强调牺牲者的英勇抵抗,ta们作为神圣的化身,其牺牲推动了通向乌托邦未来的飞跃。这种“神圣”的赠与无法以类似的方式偿还,但人们依然心怀亏欠,并可能通过进一步的牺牲行动(以债务的形式)来回应这一赠与,从而效仿这种英勇抵抗。在1984年至1999年间,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国家之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高潮期,该组织关于烈士的话语将典型的牺牲行为描绘为新道德等级的基础,而债务凝聚了一个牺牲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初是在山区形成的,后来扩展到了城市。本文这一部分提供了这种发展的背景,展示了基于牺牲死亡的道德等级的建构,以及将偿还债务作为一种抵抗形式的概念化过程。
自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战开始以来,“解放之火”(özgürlüğün ateşi)便成为伴随其斗争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1980年至1983年土耳其军事政权残酷统治期间,部分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逃往黎巴嫩,另一些人则被捕入狱。库尔德工人党创始成员Mazlum Doğan便是后者之一。1982年,为抗议臭名昭著的Diyarbakır监狱内的普遍实施的酷刑,他选择自缢,他死前点燃的火柴造就了一段他以自焚的方式牺牲的神话(Hakyemez 2017, 122)。后来,其他激进分子也在监狱内外,包括在欧洲地区,效仿了类似的自焚行为。这些壮烈的牺牲行为成为吸引库尔德革命者的奇观事件。Doğan的牺牲后来得到了铭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学院以其名字命名,这将其牺牲行为制度化,纳入了库尔德工人党向类国家转变的进程中。
火焰这一意象、从毁灭中创造的观念,成为199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日益激烈的战争中“抵抗神话”的核心。该神话围绕着一个本土春季节日——Newroz展开,这一节日源于反抗亚述暴君的史诗故事,这一故事被重新叙述为库尔德工人党自身抵抗运动的寓言,其传统的篝火也被重新定义为“解放之火”(Aydın 2014; Gunes 2013)。库尔德工人党的抵抗神话将库尔德人与从亚述人手中赢得解放的古代伊朗民族米底人(Medes)联系起来,标志着该党与古老权威的斗争。但正是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在监狱内外的自焚行为,特别是在Newroz节当天(3月21日),为这一抵抗神话注入了生与死的力量。这种火焰、死亡和反叛之间的字面与隐喻联系,促进了将牺牲死亡确立为道德确定性的基础,亦即革命的“真理”(hakikat)。阵亡的游击队员,包括Berivan的父亲,被视为烈士,是库尔德工人党抵抗神话的新基石。
制度化的、乌托邦式的、被认为是真实的斗争,从这种牺牲能量中逐渐浮现。1996年Zeynep Kınacı(代号Zilan)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将这一建构推向了新的高度。她伪装成孕妇,在Dersim(现称Tunceli)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和七名士兵。这是库尔德工人党实施的第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也是在土耳其境内的第一次,她的死亡进一步神圣化了“自由的库尔德斯坦”这一革命目标:她被Öcalan尊为“女神”,她的自我毁灭被视为库尔德民族的隐喻性重生(Çağlayan 2013, 16)。在山中及其他地方的女性激进分子使用“成为Zilan”(Zilanlaşmak)这一表达,通过牺牲来建构她们的激进主体性(Düzel 2018, 1)。库尔德工人党将自我牺牲提升为库尔德人斗争的典范行为,这插入了一个性别化的烈士道德等级体系。自我牺牲的行为促进了新的游击队员的动员和招募,并塑造了库尔德工人党为自由斗争的形象(Gunes 2013, 263)。
库尔德工人党追求超验的自由斗争,通过将牺牲与死亡结合起来,ta们创造了自己的革命神学,以激发对烈士身份的渴望及对乌托邦未来的信念。正如Banu Bargu(2014, 259)在对土耳其社会主义绝食抗议者的观察中所指出的,每位烈士都象征着未来的共同体,ta们通过“细胞式”的方式逐步建构它并确保其不朽。事实上,绝食者和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员都是“活着的”烈士;通过参加斗争,ta们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ta们被认为将抛开前世,并进入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在招新仪式上,入伍的游击队员向烈士和Öcalan宣誓,并从烈士中获得呼号,例如Mazlum,Egîd, Zilan,Berîtan等(Rudi 2019, 202)。Ta们向神圣世界的过渡将从参加斗争开始,以英勇牺牲结束。
牺牲的馈赠(“无债之赠”)需要一种超验的行动,而牺牲的债务(“无赠之债”)则要求不懈的抵抗。在库尔德工人党官方杂志《独立》(Serxwebûn)1984年至1999年间刊载的游击队叙事中,可以发现“死于抵抗”(direnerek ölmek)这一主题。相对而言,“轻易”死亡的倾向被称为“自杀主义”(suicidalism),并遭到否定。游击队员总会担心死于自然灾害(如雪崩)等意外事故,而不是在武装冲突中阵亡,因为那将被视为“无价值的死亡”(boşa ölüm)。一种道德等级体系就此形成,将自我牺牲作为衡量其他形式革命牺牲的标尺。这种对烈士身份的高度推崇无意中使其他形式的革命牺牲变得隐形。然而,牺牲的“后世”使其他形式的革命牺牲,尤其是女性的牺牲,逐渐显现出来,并揭示出牺牲在重塑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民主化项目中所产生的多种不可预见的后果。
债务新世界
AN EMERGING UNIVERSE OF DEBT
像Berivan这样的库尔德革命者将1999年亲库尔德政党在Diyarbakır市首次赢得市政席位视为一种胜利。“我们几乎不敢走进去,”她注视着市政大楼说道。“我们几乎不敢”这一短语是对土耳其语否定动词“kıyamamak”的不完美翻译,这个词描述了由于对某人或某物的爱而无法对其做出某种行为的情感。对Berivan而言,市政当局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也是一个被她和库尔德社会其他人温柔呵护的对象。这是一次替代性主权的实验,它很快成为了牺牲与债务评估的中心。
1999年是库尔德革命政治的分水岭。在被土耳其安全部队捕获后,Öcalan[5]为库尔德工人党制定了名为“民主联盟”的新政治纲领。这一新纲领放弃了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将激进民主重新定义为库尔德政治的新方向(Öcalan 2015)。通过追求多样化的直接民主形式,并捍卫性别平等、生态复兴以及公民政治的价值观,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及中东的其他民族将逐渐在各自的国界内建立起成熟的自治体系(Akkaya and Jongerden 2013)。Öcalan的开创性声明与土耳其国家在欧盟入盟过程中转向民主化相呼应。2002年,紧急状态被解除,对库尔德身份的表达限制有所放松,尽管呈现出“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状态。
自1999年起,亲库尔德政党开始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城市(如Diyarbakır、Mardin、Van、Hakkâri等)赢得市政席位。在这一时期,像Berivan这样的革命者从地下活动转向了市政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例如水资源管理、公共交通、公共关系、学前教育和女性庇护所。Ta们的工作推动了库尔德政治从革命化的军事抵抗向城市公民民主体制治理的艰难转型。然而,在土耳其国家政策为市政工作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中改造库尔德(和土耳其)社会的要求使得这一转变充满争议。尽管冲突仍然在以某种形式延续:例如以停火的形式中断的土耳其军事封锁和驻扎在伊拉克山区保持警惕的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试图用“笔杆子的斗争”替代熟悉的“枪杆子的斗争”使得革命牺牲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变得模糊不清。
市政的胜利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在法律框架内运作带来了许多优势:市政预算、机构建筑、数千名员工以及塑造公共话语的权力(Watts 2010, 162)。由亲库尔德政党管理的市政机关的就业成为该地区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在1999年之前,只有非革命的库尔德人才能成为公务员。对于库尔德革命者来说,成为公务员现在意味着努力重建库尔德社会,在实现革命与民主社会及道德秩序之间的平衡的同时,也过上了经济上有保障的生活。
随着社会和政治资本的增长以及冲突的放缓,政治的替代性形式逐渐显现,烈士的可见度也愈发提高。库尔德工人党烈士公墓得以建造(这些公墓后来在2015年后冲突重新爆发期间被摧毁)。重要抵抗领袖的雕像被树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尊是Dersim的Seyyid Riza雕像(Ilengiz 2020, 87–88)。库尔德青年作为城市革命政治的新兴主体,为这一牺牲政治做出了贡献。库尔德青年传播ta们自己和/或亲属所遭受的暴力故事,并通过将烈士定义为英雄的方式再现革命牺牲的道德等级(Neyzi and Darıcı 2015, 62),将自己想象成身处于“生者与逝者的神圣交融”之中(Neyzi and Darıcı 2015, 68)。失落、内疚、希望、绝望、喜悦与庆祝,以及最重要的,负债感等复杂情感塑造了牺牲的后世。
一个反映负债感的核心术语是“bedel”。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意为“某物的代价”,例如面包的价格。然而,从库尔德革命的道德世界的角度来看,“bedel”表示为了某一事业——自由的库尔德斯坦——而作出的牺牲。库尔德革命者常用的短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çok bedel ödedik)强调了牺牲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并确认这些损失在“事业”这一神圣目标的形成和维护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在和平进程期间,无论是在土耳其媒体对库尔德人所遭受国家暴力的公开报道中,还是在人权组织会议上的闭门讨论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声明频繁出现,见证了库尔德人民为此做出的牺牲。
这种迫切负债感增加了事后偿还的可能性。最初的评估充斥着性别、道德和阶级差异,这些差异在革命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一种关于政治家(与政治)的二元话语开始形成,将“真正”作出牺牲的“革命者”与“职业主义者”区分开来。对象征性、社会性和文化资本的引用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区分:后者拥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说没有口音的土耳其语,有些还会说英语。Ta们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新建的高档封闭社区中。相比之下,革命者们居住在像Bağlar这样的拥挤社区中。Ta们没有漂亮的简历,因为ta们在冲突最激烈的1990年代就辍学了,要么是为了投身斗争,要么是因为库尔德工人党要求ta们离开“殖民者的学校”。对于女性来说,去美容院做头发、染发等行为可能被视为特权和缺乏牺牲精神的象征。牺牲与新形式的资本之间日益密切的日常联系表明,牺牲的后果聚焦于在新秩序中的债务偿还上,而这些争论的核心是烈士的家庭。
具象化的债务
EMBODYING DEBT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遇到了许多已故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员的亲属。在这座饱受数十年冲突摧残的城市里,几乎很难找到没有烈士亲属的家庭。然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公众和组织中有更高的可见性,ta们被冠以“价值家庭”(土耳其语为“değer ailesi”)或“烈士家庭”的尊称。这些价值家庭组成了以团结为基础的社区和组织,其中之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失亲家庭援助、团结与文化协会(Mezopotamya Yakınlarını Kaybeden Ailelerle Yardımlaşma Dayanışma ve Kültür Derneği,简称MEYA-DER)。该组织明确的目标包括帮助家庭确认已故游击队员的埋葬地点、组织葬礼和悼念帐篷,处理游击队员死亡或家庭成员被监禁后与法律相关的繁杂事务,以及安排前往监狱的交通。此外,该组织还承担了一项对这些家庭至关重要的任务:帮助ta们寻找子女,无论是生还是死,这需要与库尔德工人党保持沟通畅通的沟通渠道。
该协会位于贫困的Bağlar社区,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所处的市中心有约30分钟的步行路程。一块写有“MEYA-DER”的小牌子被钉在公寓墙的一角。当我爬上楼梯接近大门时,一股浓烈的饭菜香味从里面传出来。在一位MEYA-DER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们进入了被ta们称为“办公室”的房间。里面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还有几把椅子。我的受访者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后面,摆出正式会谈的姿态,而我则坐在访客椅上。会谈后,我看到其他房间的氛围与我们的正式会面的房间截然不同:两个大房间被布置成了起居室,配备有可展开的沙发床,供来自外地的价值家庭来此地探监、向国家机构提出上诉或参加葬礼时使用。在另一次拜访中,我看到这个空间被改造成了一座悼念厅,因为一位已故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员的遗体刚刚运抵此地。
这个由住宅改建的办公室距离城市和政治中心的偏远位置,鲜明地体现了Berivan及其他人感受到的牺牲被边缘化的现实。然而,通过同时开展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化政治实践,价值家庭赋予了牺牲一种新的集体形态和生命力。我的一位对话者Ayşe描述道,ta们“在痛苦中团结”(acıda birleşen)。所有工作人员都出身于价值家庭。Ta们承诺“将斗争继续下去”,这主要通过保护亲人的遗产、过模范生活(Işık 2023, 263–79),以及对烈士保持虔诚的态度来实现。出于对烈士的亏欠,ta们彼此照顾,包括提供每月的食品补贴、为子女提供奖学金,或协助安排葬礼。尽管ta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以至于如果我听了一个“母亲”的故事,我就能理解其他人的痛苦(参见Karaman 2016)。在价值家庭群体内,通过包办婚姻结合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位受访者表示,她和丈夫并非因爱情而结合,而是因为共有的失落感和痛苦将ta们维系在一起。通过宣扬对烈士的负债感,并默默从事幕后革命工作,价值家庭以各种形式延续着牺牲,例如认领游击队亲属的遗体、举行正式葬礼、揭露国家对游击队遗体的死亡政治处理(Bargu 2019),或以更加“平凡”的方式如照顾家庭的遗留成员。Ta们承受着国家不断施加的、使ta们感到负债累累的机制(Biner 2020)。正是在这种无尽、集体且多样化的痛苦和债务复杂性中,价值家庭创造出了牺牲的“后世”。
随着价值家庭去中心化、安静却持续的经验中债务与牺牲的融合,牺牲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英雄式的、具有抵抗性的自我牺牲。“牺牲的礼物”不仅面向一个神圣的未来,也面向现在,要求重塑政治与道德秩序。牺牲的后果将牺牲与神圣联系起来,它将“代价”(bedel)转化为一种诉求、一种主张和一种期望。价值家庭的经验将焦点从牺牲的开端(聚焦一个人的牺牲是否是纯粹的)转移到其结果:即牺牲如何融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并成为一种不可预测的力量。
治理牺牲
GOVERNING SACRIFICE
回想革命在Diyarbakır日常生活中的扩展如何促成牺牲的多样化“后世”。市政当局的就业政策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衡量领域;对于库尔德革命者来说,将ta们的战斗精神转化为新兴的专业化和效率化语言构成了新的挑战。不懂得专业术语成为ta们被解雇的理由。面对“你毕业于哪所学校?”的问题,或者无法准备漂亮的简历,这些从战士转变为公务员的人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ta们的革命斗争工作与城市政治的相关性。
将价值家庭纳入就业政策推动了一种在牺牲“后世”中以计算逻辑为基础的现象。21世纪初期,市政当局实施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招聘政策,为价值家庭成员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设定了非正式的配额。这一配额的依据是,幸存家庭成员和战士的照护和赡养被“托付”(emanet etmek)给了该运动。这不仅是道德良知和革命团结的问题,还将为与运动关系密切的库尔德城市政权赋予道德力量。有传言说,某一时期的工作申请表上包含一个部分,询问申请人家中有多少烈士。尽管我尚未见过实际的表格,但如果真的存在,可能也早已被迅速撤回:这种简单粗暴的官僚化可能会剥夺烈士身份的神圣性,这是运动无法承受也不曾有意为之的。
尽管有这种传言中的错误,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对牺牲真实性的审视,以及根据雇员的革命经历、家庭中烈士的数量和家庭对运动的投入程度进行的适当性评估与判断,已然成为了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牺牲的馈赠被通过计数、计算和量化来衡量:一个家庭为事业付出的烈士数量、一个人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以及身体经历的酷刑手段的多少。什么程度的痛苦才足以获得某种职位?应该为价值家庭成员分配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既不削弱ta们的道德地位,又体现其贡献?这些是新社会秩序中出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指标,其正与土耳其国家的威权债务逻辑相伴而生:任意选择“值得”的公民,并惩罚其他人(Yoltar, 2020)。类似的道德判断也为库尔德社区带来了困境;对某些革命者来说,价值家庭“要求”和“索取”被视为纯粹的“自私”和“不了解斗争及其价值”。讽刺的是,牺牲的神圣性无法被任何社会形式所还原,这一立场最终将牺牲从新兴的政治和道德秩序中剥离出来。这种不断在牺牲与补偿之间画出的对应和比例关系既是革命性的,又充满痛苦,因为如果无法将二者协调,革命本身将变得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牺牲的可能性在新政治和道德秩序的边缘徘徊。
可以认为,就业政策是库尔德人市政治理试图超越我称之为“民族主义牺牲的剧场”的一个例子,意图创造一个革命牺牲的后世。在土耳其,这种“剧场”正在上演;尽管参与与库尔德工人党战争的土耳其残疾退伍军人获得了大量国家资源支持,但ta们在社会中仍难逃被边缘化和忽视的命运(Açıksöz, 2019)。寻求将价值家庭融入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方式,可以超越仅仅将ta们视作过去时代的代言人,并将ta们变成日常政治中的真正行动者。然而,就业中根深蒂固的计算逻辑给将痛苦和损失转化为社会再生产形式带来了挑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安排价值家庭成员从事“卑微”的工作,比如垃圾清理员。
在牺牲的余波中,只有当牺牲的损失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一次性事件时,道德与社会、过去与现在、永恒与时间束缚之间的分离才是可能的。然而,问题在于,牺牲并非如此:损失是具有生成性的,它很少停留在原地,因此牺牲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成为其特征。牺牲馈赠的“纯粹性”并不能保证它的完全他性。库尔德人的市政治理需要进行回报:通过公民政治进程建立的新秩序,不仅在于延续革命,还意味着通过建设一个后世来回馈许多牺牲。在扩展牺牲的公共评估及其回报时,ta们尝试了包括就业在内的多种方式,但最终面临了在新政治中再现原始牺牲道德世界的困境。这些实验未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烈士的牺牲如此难以还原为日常的社会形式和时间性,以至于ta们的生物亲属——这些亲属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永恒烈士的化身——很难在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那么革命还剩下什么?在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即我开展研究的时期,库尔德运动通过市政当局所施加的政治权力被这一道德困境所削弱,摇摆于衡量和无法衡量、测量和评估之间。
平凡的牺牲
MUNDANE SACRIFICE
除了市政政策之外,在革命群众中,牺牲后世的潜能以安静、杂乱和渐进的方式萌芽。牺牲余波的多样性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到其他形式的牺牲,这些形式在围绕烈士所带来的神圣性构建的道德等级中一直处于隐形状态。这些牺牲可能非常平凡,例如无法怀孕、无法继续学业、无法旅行或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生活在Diyarbakır高度军事化的环境中;目睹亲密朋友的死亡;无法远离政治和战争;或者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无法以更放松的态度对待生活”。我将这些称为“平凡的牺牲”,以强调其与烈士牺牲的区别以及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它们将自己的时间性融入到斗争之中,将对乌托邦未来的等待转化为革命的当下。
正如Leyla Neyzi和Haydar Darıcı(2015)的民族志所言,牺牲债务在塑造库尔德青年群体受创的集体身份中发挥作用,但它也能在库尔德社区内帮助建立富有生成性、流动性和关怀的关系。牺牲作为一种礼物融入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遗忘债务,而是通过这些形式建立起其他责任与照护的关系。例如,一位名叫Gûlasor的年轻女性,她的父亲在她两岁时就去了山里。她对债务有着不同的理解,她认为父亲的牺牲是他的个人决定,并不应该作为价值家庭的一员而提出要求。相反,她觉得更欠母亲的情,一位单亲母亲和活动家,她计划“为母亲做很多事情”。Gûlasor通过在Diyarbakır的日常生活中与母亲建立照护关系来回馈自己背负的债务。如 Krystalli 和 Schulz (2022, p. 15) 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照护“工作”既体现了革命政治的政治工作,也揭示了“在暴力过后重塑世界的实践和政治”。
牺牲的后世使革命的不同主体性和行动能力变得可见,同时也展现了其性别化的经验。在田野调查期间,我遇到了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早期的青年时期加入运动的受访者,ta们只在山里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甚至根本没去过山里,因为ta们的家庭“已经牺牲了足够多”。有些人参与了城市激进活动,帮助为新兴的公民组织建立草根网络;有些人在监狱中度过了很多年;有些人因失去亲密朋友而受到创伤;还有一些人远离了运动。我将这些革命者标示为“普通”革命者,以强调ta们非英雄化的抵抗形式以及ta们在运动边缘的位置。Ta们形成了日益强烈的要求终止“代价话语”(bedel dili)的声音。
其中一位普通革命者Sevgi是一位40岁出头的库尔德女性,从事干部工作,这意味着她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斗争中。在山里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并被监禁两年后,她被指派在城市中负责公共关系工作。她是一名出身低微的革命者,从贫困和压迫性的婚姻中逃离。虽然她的故事是一种赋权的象征,但也包含了许多“平凡的”牺牲:在激烈的运动期间无法怀孕,不能像希望的那样照顾生病的母亲,作为离婚女性无法与新伴侣公开关系,因为干部职责无法拥有私人空间或稳定的生活等。她说:“我从来无法对自己的生活有任何计划或项目。我付出的代价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上的(manevi)。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一直为此付出代价,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已经放弃了要孩子的想法。我本可以有一个孩子的。你知道的,我也是个女人。在情感和性方面,我也有需求。但现在我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这也是一种付出。” 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中,她听起来很绝望,但在第二次见面时,Sevgi宣布她正在迈出人生的重大一步;她将安顿下来,住进自己的家,和她的新伴侣一起生活,这两项举措都是隐私之举,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波及她在运动中的地位。
在“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这一道德责任感的推动下,这些普通的革命者将神圣的时间性融入到ta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现在改变当下成为可能。在我们的访谈中,Sevgi正在努力扭转她在不孕治疗期间经历的过度医疗化对身体的影响。她的生活改变并非明确为了转变运动中的政治话语,而是通过照护和创造性地慢慢重塑世界(Kurtović and Sargsyan 2019)。像Sevgi这样的普通革命者将日常生活转变为一个维系革命的空间,牺牲的后世在此得到延续。对ta们而言,神圣与牺牲时间性的交汇一方面挑战了牺牲的道德等级,但也不必放弃牺牲的道德意义。同时,它也使时间、价值和行动之间原本遥远的领域实现了交融。
脱离革命牺牲的道德等级迫使人们在转译中发挥创造力。凭良心拒服兵役的以色列前士兵重新定义了民族主义牺牲,将ta们的边缘化和落魄纳入其意义中。Ta们将自身在军国主义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平凡”牺牲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从内部实现变革(Weiss 2014, 402)。这样的干预可以使得牺牲变得“酷儿化”;土耳其的库尔德跨性别性工作者借助“变色龙式主体性”,采用了既来自革命又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话语的策略(Karakuş 2022)。创造力包含了不确定性:牺牲总是面临不被承认的风险,而ta们可能被指责为“叛徒”或“自私的人”(Schäfers & Düzel 2020)。
通过公开表述ta们的平凡的牺牲并为补偿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像Sevgi这样的普通库尔德革命者寻求结束围绕“革命牺牲才是英雄的牺牲”的道德等级的可能性。这些表达召唤了一种不同生活的可能性,其目标是获得社会地位、社会资本、就业机会,如隐私、亲密关系、恢复健康、重新受教育的机会、旅行时间等不太明显的资产,或脱离政治规范的可能性。这种牺牲的多样化使库尔德革命者能够表达ta们过去和持续到现在的苦难与损失。Ta们将“代价”从游击队的空间带入到自己的非游击生活中,并将牺牲的叙述从山中的英雄转移到普通革命者——既非英雄亦非卑微的受害者身上——及其城市日常生活的牺牲中。随着ta们将革命牺牲从英雄式的死亡拓展到其他形式,社会生活也对革命敞开了大门。通过平凡的牺牲与回报,革命转变为一种对新生活的日常重构。
通过无数种相应的行为将牺牲从英雄式死亡的超然高度带入平凡生活的琐碎中并非宣告革命的“终结”。革命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未定的文化现象,只有通过承认牺牲的信念以及“当牺牲看起来完全无意义时的信念消散”(Haugbolle and Bandak 2017, 202),才能理解。在民主化时代,普通的库尔德革命者重新夺回了牺牲的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诉诸霸权的公共话语,这反而为通过道德能动性提出ta们自己关于革命意义的构想打开了可能性。
在权力和影响力斗争以及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国家之间持续冲突的背景下,终结牺牲的想象显得遥不可及。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平凡的牺牲形式,“代价”仍然是一个过时却无处不在的道德锚点。即使人们抱怨对“代价”的过度使用——“又是bedel?真的吗?这套说辞够了吧!”——也清楚地意识到它潜在的扩展能力。如果将革命与新秩序相提并论使得关于革命相关性和结果的尖锐问题被抛出,它也同时提供了关于正在被铸造的新社会-道德秩序的线索。
结论
CONCLUSION
一位交流多年的朋友曾说过:“革命夺走了我的一切,也给予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生命是被赋予的,生命是一件礼物,这一切都凝聚在一个革命的身躯中。牺牲的后世就像革命经验的记忆、叙述与延续一样多样。价值家庭的经验揭示了牺牲的核心矛盾:它既是作为追求目标的神圣存在,又是为建立新政治道德秩序所需的平凡之物。库尔德城市治理在将牺牲馈赠融入新秩序的尝试中,再生产了新自由主义的量化逻辑。而普通的革命者则悄然地将自身的牺牲与债务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沿着这些痛苦、破坏性且转变性的道路,我们认识到了牺牲的后世既充满混乱,又为革命潜力提供了深刻洞见。
在革命的余波中,等待、恢复身体、照料年迈母亲等新时间性,与神圣时间交织在一起。我的访谈对象通过创造性、照护性、渐进性的转译行为,不断地在不同的时间性之间穿梭往返——从仪式到日常生活、从社会到政治。这些转译充满了多种矛盾,例如挫折、绝望、希望和关爱等,但正是在这些转化之中,革命得以呼吸并延续。
“牺牲的后世”这一概念试图超越对过去“幽灵”的存在与力量的简单肯定。这些幽灵在不寻常的空间里维系革命(Wilson, 2023),激起希望与绝望(Salem, 2020),并推动伦理自我转变,形成抵抗性主体(Yonucu, 2023)。然而,本文指向一种更复杂的状况:革命塑造了牺牲,而牺牲的后世反过来也塑造了革命。我将“牺牲的后世”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比较操作工具,以凸显革命承诺的交叉性、不均衡且不断变化的时间性。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看见,革命如何通过看似隐形但却具有生成力和多样化的损失与牺牲形式,获得新生。重新思考革命的时间性揭示了重新调整道德等级的尝试、新政治实践与关系的引入,以及对牺牲“另一面”的探索(Mayblin and Course, 2014)。因此,牺牲的后世为革命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之中,损失与关怀、毁灭与治愈、完美与不完美能够共存。
在这篇民族志中,普通的库尔德革命者通过“代价”(bedel)叙述ta们的生活,并将其转化为对补偿、重视和认可的诉求。Ta们清楚地认识到,在无法为革命持续创造可能性的当下,牺牲的后世可能会受到限制。道德上的困惑与转译的脆弱性愈发难以承受。在这样一个可能性逐渐减少的环境中,普通牺牲无法被保证会得到认可。2015年的冲突重启使这一切成为了现实。数月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山中,也波及库尔德人占多数城市的历史城区,深入人们的家园之中(OHCHR, 2017)。2016年,大多数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库尔德议员和市长因紧急法令被逮捕,地方政府被指派托管(kayyum)。包括Berivan在内的许多受访者被免职。当面临死亡的可能性,生活在被重新占领并受围困的城市中,且无法继续参与合法的政治形式时,库尔德革命者不得不重新评估重回紧急状态与暂停牺牲后世的意义。
注释
NOTES
[1] 所有名字均为虚构,以保护访谈对象的匿名性。文中所有翻译均为作者本人完成。
[2] 这一时期划分旨在标示:(a)库尔德运动斗争中的主要条件(紧急状态);(b)运动主要指向的方向(民主化)。
[3] 由于土耳其法院对亲库尔德党的反复取缔以及其以新名称重新出现的循环,本文章中提到的亲库尔德党事实上是同一个党派。为避免混淆,本文统一将其称为“亲库尔德党”。
[4] 尽管库尔德工人党最初主导了库尔德运动,但在本文中,我使用“库尔德运动”一词指代一个由民间与武装组织组成的大型联合体,其中多数组织通过不同且常常冲突的方式支持实现“激进民主”。
[5] 奥贾兰(Öcalan)因叛国和分裂主义指控于1999年6月被判处死刑,不得上诉,后改为终身监禁。至今,奥贾兰仍被单独关押在İmralı岛。
(引用略)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