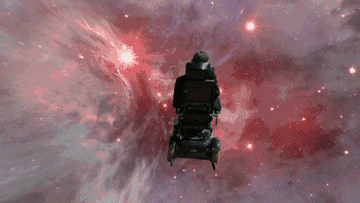
Specter in the chair
王文林 /文
某些名字会投射出一片阴影,将它们自身吞灭。
——雅克·朗西埃
在他惯于夸夸其谈、自言自语的某部爱情电影中,伍迪·艾伦曾把人生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可怕的(horrible),包括遭遇先天不幸、致残以及疾病等事故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度过这一生,或者,他们会度过怎样的一生,这是不可思议的(incredible);另外的人则都是可悲的(miserable)。因此当你度过这一生时,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可悲的人,因为你运气好,你才能成为可悲的人。
斯蒂芬·霍金没能交上人们预想的好运,他的一生因为渐冻症而被扭曲。我想,应当以他擅长的简要形式开始这篇简明的(brief)文字,甚至当回想起horrible、miserable及额外的incredible这些字眼时,我就已经确立了这个方向。这些字眼不是什么值得沉思的哲学概念,需要做出某些哲学思考,它们仅仅是某些话头、某个提供言谈的有趣装置。
假如人们把疾病这样的事故看作可怕的,把人生看作可悲的,那么,霍金的一生将超越正常与健康的想象,变得不可思议。如果你亲密地围绕这些词语,你便发现:
关于霍金的人生,人们只了解到他所患的可怕疾病,疾病事故给他带来的可怕影响,却丝毫未曾了解他的生活本身的可悲。不单疾病本身是可怕的,霍金的生存、他的形象、他的存在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可怕的。
并且考虑到他的成就,他和疾病的斗争、妥协与依附,这些不可思议的经验,就不应该只招徕那些浮夸的赞美、惊叹,更不应该得到简单片面的处置。
没有什么比一厢情愿故作浪漫的想象更令人不适,更没有什么比沉痛哀悼来得轻松。
霍金的人生、对宇宙的思索、种种的趣闻逸事,无论如何,都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编为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纳入一种传统到令人作呕的叙事当中。这类故事不断重复着一种简单的思考:人的意志、信念、好奇、追求将会战胜残缺破损的身体。他去世的消失散播之后,大量的哀悼文字验证了这个共享的前提,仿佛内在的意志能够挣脱身体的牢笼,让意志独存,而让身体的阴影愈发浓重。
让人惊讶的是,不仅媒体报道采用了这样的叙事,甚至连科学群体、科学家们也欣然接受这点。当然,某种意义上,科学家们表达这种哀悼恰巧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而言,笛卡尔可能是他们熟知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他妥善地“解决”了困扰人们从事科学探索的灵与肉的问题。而在大众传媒或日常话语当中,这个问题被轻巧地冠以“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的博弈。
不管是高贵的精神、意志,还是有趣的灵魂,不管是通过映射、表现、超脱等方式,总之,它们都将身体置入了黑暗的阴影,从而要么重复那些伟大人物的道德学说,要么宣扬一种变相的宗教复活论(霍金研究的宇宙、黑洞、时空等主题使他们自然长出了幻想之翼)。
如今,霍金的去世向你们揭开了这个真相: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离开了霍金,绝非是霍金离开了人们。人们避免和他可怕的遭遇,并避免遭遇他的可怕,人们逃避这个侧身陷进轮椅里面,有着古怪面孔、扭曲的身体、发出极不自然的声音的科学怪人,并忽视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在轮椅上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的事实。即便在那些关注霍金种种的趣味爱好,涉嫌以“你所不知道的霍金”这种形式吸引目光的文章中,你依然无法抱有期望,因为在审美考据癖者的眼中,审美经验仍旧是独立于身体经验的。
然而,轮椅就是我的身体,我的绞刑架,我的救赎方式。 我通过“身体-轮椅”的装置获取感知、度量时空、与世界沟通。
在他生命的晚期,霍金再也不可能摆脱轮椅,离开轮椅,他就不过是一颗坚果。以至于,当医生宣告他患上渐冻症时,可怕的命运便已经降落到他身上,剩余的时间不过是让他的身体、意志或者灵魂进入轮椅。
因此,他,霍金,这个轮椅中的人,并没有让他的意志、思想和灵魂离开过轮椅,就像他的身体也没有从中脱离,毋宁说,他将自己的信念意志、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和身体等等和他的轮椅统一起来,最终,这才是他的生命既可悲又可怕的不可思议之处。
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坚定的意志、崇高的信念或艰深的思想能够脱离他的身体,身体只是身体,就如同他的身体也没有完全摆脱轮椅、轮椅的塑造和感知。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够说明,霍金是居住在轮椅上的人。我们直面这个人,而非不断重复他的成就、他的简历、那些死去的话语以及媒体的叫卖和推销(hawking),正如我们会不断地思考阁楼上的疯女人。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惊讶于他所拥有的身体,这是怎样的身体?这具身体传达出怎样的经验、感知?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它如何思考?我们应该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从生产的身体到身体的生产,而不是相反。
和阁楼上的疯女人相似,轮椅上的人也是当前促使人们思考的重要形象。
目前为止,浪潮般汹涌的声音正在退去。媒体的喧嚣,专家的阔论,最具社交年代特色的群众的缅怀和纪念,随着新闻热度的冷却,这些声音逐步地平静。其中,在大量的文本里面有两张图片格外引人注意,出于对某些荒谬观念的呈现,它们看上去显得既荒谬又有趣。我将向你们展示这两幅图片,并分别说明它们的好笑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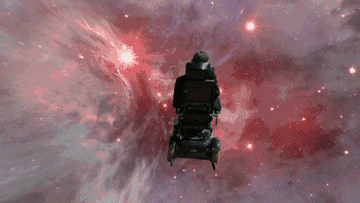
这张图清晰地显示出霍金离开了我们将要去往哪里,基于他的职业,人们想象他会驾驶着自己的轮椅摇摇晃晃地飞往黑洞,飞向其他星体或在宇宙漫游。背景里的星尘、烟云等等同样让人自然地想到时空隧道的场景。因为它是人们关于离开的想象,确切说是关于死后生活的想象,故而它也不免令人想到复活这个主题,假如图中的景观被进一步视作天堂或地狱的绚丽场景。
长久以来,在宗教末世论的主题下,复活的身体或荣耀的身体一直是神学中非常重要的章节。这个问题可以粗浅地说成:人死之后在另外的场景中得到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针对复活的身体的本质和特征问题的追问,使得神学家们陷入了持久而又琐碎的争论当中,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复活的身体的身份问题、复活的身体与尘世身体之间的物质同一性问题。神学家们未能给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直到被视为异端的奥利金(Origen)提出了形象/形式(eidos)复活说。通过宣称复活涉及的是身体的形象、形式,奥利金,进而是阿奎那,中止了这些无休止的讨论。这种身体形象或形式上的同一并非物理数值的完全等同,而是身体与其自身的相似。当身体的同一性问题被成功解决了之后,剩下的便是复活的身体和物质身体间的区分问题。在这一点上托马斯·阿奎那的阐述极尽详细甚而繁琐,简要言之,阿奎那废止了尘世身体的功能性,在复活的身体或荣耀的身体上,身体的物质功能被废除,呈现出物质的纯粹无功用性。
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身体的形象或形式,是身体自身的相似性,与实在的肉体、尘世身体相比,它显现出了身体的无功用性,它将器官的去功能性、物质的无功用性独立出来。但是,我之所以引出、引用关于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的谈论,并不是作为一种知识的补充,也不是关注一种宗教仪式或祭祀行为指向的更崇高的存在领域:复活与荣耀是一个特殊领域,它悬置了生理机能和肉体的器官功能,将其转化成为一种永恒状态,例如在宗教的节日仪式当中。谈论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方法、途径,是对于人类身体的反向思考: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从肉体的死亡迈向复活(素朴的宗教叙事),而是从复活的身体观照物质的身体(弥赛亚主义)。
并且,
或许在某个位置或姿势当中,我们将物质身体和荣耀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和悬置结合起来,成功地开启当下的行为实践蕴藏的潜能,进而呈现一种新的身体的使用。
但是,即便你不太懂上面这一连串的说教,你也不会不懂这张图的好笑。霍金驾驶他的轮椅开始了一场迷幻之旅,不管这是太空之旅、时间之旅还是复活的旅程,自始至终他都和自己的轮椅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任何一趟旅程来说都是荒谬的。
这张有趣而荒谬的动图,在我眼中,它揭示了关于霍金的身体的真实,他的身体的本质和特征即是他和轮椅结合的形象,是“身体-轮椅”的形式。

同样和人们的想象、身体的形象有关,与第一幅图相比,这张照片显得更加激进,更具有图式论意味。它干脆抹去了霍金已经萎缩的肉体、他的眼神和面孔,取而代之,存在的只是一把扭曲的椅子,歪斜的靠背如同轮椅上的霍金日复一日所重复的姿势。这把椅子摆放在一个普通的房间角落里,与之相关的两面墙上分别有白色的室内暖气和貌似一排白色插孔的东西,总之这是一间普通得不能再过普通的房间了。
然而,照片的拍摄者由于害怕观众没能成功地展开想象或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后期加工的过程中,她/他在白色插孔的那面墙上用技术手段打上了数字“1942-2018”。这就给观众的观看带来了麻烦,因为无论如何,不通过技术鉴定手段,仅凭自己的眼睛我就无法断定椅子歪斜的后背是否也经过了修饰。但相对于画面整体而言,这还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真正的困难反倒是这串数字带来的危险的增补,也就是说,观众能够辨认这是霍金的身体形象或形式,是由于(修饰的)椅子聚集了他全部生命的姿势,还是因为这行明示的数字,或者是二者之间的互相印证?假如仅仅放置一张后背歪斜的椅子,或者一张普通的靠椅,你能直观到这就是霍金吗?拍摄者也许模糊地预料到了椅子即是霍金的身体形式,尤其是背部歪斜的姿势所具有的潜能,因此她/他取消了实在的肉体、器官。
椅子承载着空,在拍摄的当下,它是一把无人坐上去的椅子,一把悬置了功能的椅子,一把无用之椅,纯粹的身体形式。
相较于其他人,拍摄者的行为更加激进。
不过,正因为她/他恰巧聪明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她/他就比任何人更加激切地想要展示自己,存在的艺术与展览的悖论应验于此,源于摄影者激切地想要展现自己的艺术,艺术的品味、修养,艺术的表达等等,于是她/他所可以展示的仅仅是她/他自己,而放过了她/他曾可能捕捉到的事实。激进而激切,正如荒谬又好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做多余之事其实是一种美德。
一把背部歪斜了的承载了空的椅子,并不是一把空着的椅子,等待其他人坐上去侧躺着歇息,赋予或调整它的姿势。况且,这把坏了的椅子,自然也就不再有用,像哲学家说的那样,它脱离了正在使用的上手状态,进入了在手领域。在哲学家那里,这种不再有用的工具却分外的令人着迷、不安,甚至,如前所述,让人感到可怕和震惊。现在,面对这把背部歪斜的椅子,这个脱离了使用功能的客体,哲学家会冒险求助于物的内在性或建立和内在性相关的仪式,他试图在言词缺失、破碎的地方,进而是无物存在的地方言说,于是这种内在性代表了缺失的言词、纯粹的空无,这样的物唤作无物之物或空无一物。
不过,与其使用繁复的辩证思考构建一种无物之物,倒不如坦诚这样的空无,而人类语言当中内在的喑哑或寓居在语言中的无言或空无,是纯粹的姿势。何谓姿势?
姿势无言,它大约在你呼唤、命名的刹那扼住了你的咽喉。或者,正当你说话时,某样东西填塞了你的嘴巴,打断了你的话头。姿势是无声的呐喊、挣扎的双手和扭曲的面孔,此外,姿势中断了预先排演好的对白,逼迫台上的演员即兴表演。
总的来说,姿势就是在每个表达行动中保持不被表达状态的东西,并且通过在表达内部建立某种核心的空无,唯有如此,言语和书写才得以可能。
姿势标示了这样一个点:在此点之上个体完整的生命、她/他的活生生的存在遭遇到了词与物,同时,它以空洞、抹却的方式把自身毫无保留地掷入语言游戏。
好了,就此打住,我不想在此做进一步的哲学探讨,这不是我想在霍金的姿势、他的身体形象上试图进一步追问的。我们面前的这把后背歪斜的承载着空的椅子,这样的姿势是轮椅上的霍金一生所重复的姿势,是聚集了他全部的生命力量的姿势,由于这种古怪的姿势,物体显得不再有用,并且由于姿势在言词和物之中确立的空无,使得话语取消了朝向沟通的目标。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那么你们肯定也能看到:
当死亡抹去了他的肉体,并保持在一种尚未泯灭的、已死的空无状态时,霍金,这个幽灵,对他来讲,他并没有获得解脱,离开他的轮椅和椅子的束缚,他的姿势和身体形象反而必然地与椅子完全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幽灵并非在椅子上,而是在椅子中,它寓居于椅子,成为了椅子承载的幽灵或轮椅中的幽灵。这无疑会让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驼背小人。只是如今它站在世纪的门槛上,瞩目着遥远的未来的使命。
幽灵一方面指向死亡的空无,另一方面则指向活生生的、普遍的生命,恰如姿势凝聚了个体生命的力量,恰如在身体的形象和形式当中,当生理机能和器官的功能被悬置时,身体便具有了朝向共用的、普遍的生命的可能。
普遍的生命从未被全然占有,从未得到全然的言说,也从未被隐喻化或进入“表征-再现”的系统之中。斯蒂芬·霍金在哪里?在那些简历、档案标注的在场中吗?在他的亲友、弟子乃至人们口口声声的传颂中吗?在他自己撰写的传记的现实中吗?或者在将来会由某个更细心专业的传记作家所写的某部传记中吗?当然不是。一个卑劣的举措是将霍金隐喻化,令他的生平故事成为某种寓言,令他成为身残志毅的代表,正如蜜蜂的勤劳、狐狸的狡诈、猫头鹰的高贵等等。
去隐喻化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假如没有现代科技的发展,霍金可能提前死亡,或者至少霍金绝不是今日的霍金。他破坏了自然法则,扰乱了预知的时间,同时在他身上、他的身体形式中,人们难以区分有机和无机、肉体和机械、电路和神经系统。技术作为一种中介,从未如此深刻地介入人类的身体,霍金向人们广泛传递了这个信息,从这个层面来看,霍金毫无意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英雄,甚或推动着拓展化、增强型的人类研究领域的发展。
但是,打造新型人类未必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情,即便你家中的U盘、网线、路由器等等看上去并没有丝毫的隐喻价值,也不表征什么,可电子器件的功能是要传达清晰明确的指令,而通过电子技术制造或改造后的人究竟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