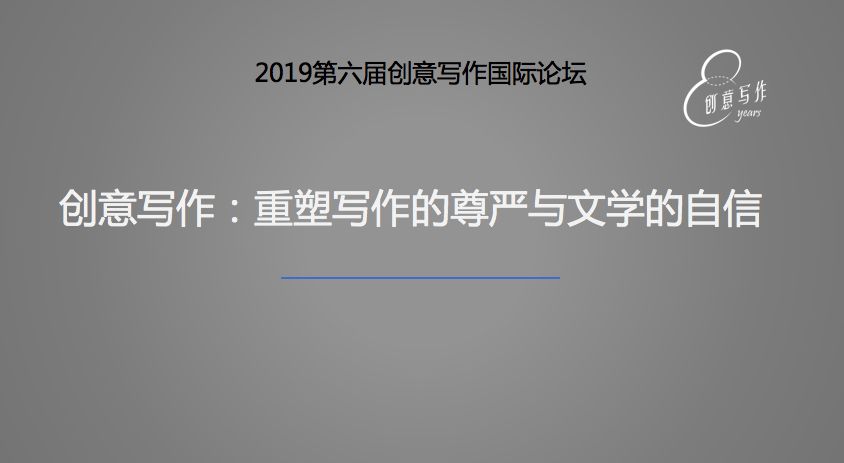
“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信,或不信。认真地听朋友说一件事,他说的时候都未必完全相信自己的叙述,而你事实上也同时听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而好的文学,也许就是那些没有被直接说出来、却藏在海面之下的八分之七的冰川。
”——文珍

文珍,青年作家,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十三届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第十四届十月文学奖、出版小说集《柒》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散文集《三四越界》。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部分小说、诗歌被译成英、法、阿拉伯文等,即将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语种译介至海外。
文珍:
写作者永远徘徊在怀疑与相信之间
2019第六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
/
首先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看到今年论坛的主题是“重塑写作的尊严与文学的自信”,文学的自信当然和文化自信一样好,非常好,但我怀疑,文学的生发恰恰是从不相信开始的。
然而我自己其实一直是个轻信的人。
比方说,我一直喜欢人,也喜欢那种对他人全盘托出的依赖感,尤其相信人性的光明面,那些振拔向上温暖友善的部分,一旦相信就会投入所有的激情、想象和善意去接近对方。
可最近某位朋友却评价说我不太玩社交软件、朋友圈也发得越来越少,似乎也和别人一样,很好地把自己藏起来了,似乎也没那么信任人世间了。
我说,可能我最近没什么表达欲。
这朋友想了想又说:
你是作家,你怎么可能没有表达欲?
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宣泄的渠道尚有写作。
可是,当我再动笔时,这个朋友的问题就突然浮现出来让我心念一动:我究竟还有没有足够想说的话?我究竟还相不相信人和人是可以沟通的?我究竟还相不相信文学的力量?
就用聊天来打比方。很多时候,我们在和别人交谈时,一开始是全心全意倾吐心声的,说着说着,也许对方的一个表情,也许对方的一句不中听的话,会让你突然短暂地产生怀疑:我在说什么?他又听到了什么?他怎么理解我说出的这些事实,他会相信那都是真的吗?同时,因为这怀疑的暗生,我们会突然注意到朋友说话种种不自然的地方。他真的对我说的话感兴趣吗?他会不会走神在想别的事情?疑窦产生之后自然而然越来越大。这些注意和发现都会动摇我们对之前某些事情的笃信,这些事情可能包括一个朋友、一段关系,甚至是特定的年代。
但是,就在这样的怀疑之后,你也许会决定先说,等轮到他说的时候也不打断,听完以后,你发现你重新被他说服了。你决定再次相信他是你的朋友。
我们这些最初的相信、中间的怀疑,还有那些在濒临崩溃之后仍然信仰的东西,也许就是文学悄然发生的时刻: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亮照进来的地方。
我本科学的是经济。经济学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建立经济模型,简称建模。每当巨大的经济危机来临之后,经济学家总会尝试建模来解释之前的经济何以崩溃,然而,这往往都是马后炮。
马后炮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相信是有的。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的危机会不断涌现,新的投机者仍然会找到现有制度的空隙,但经济学家明知无法预防,依然还是一代代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光需要理解这个客观世界,尊重他人的选择。更要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了解大多数人可能是怎么选择的。
这种相信和怀疑的过程,就开始非常接近文学:本质上文学也好,经济也好,其实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的人在同种情境之下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们假定某些东西,比如经济规律、经济模型是存在的,然后再不断地以现实社会的反例来推翻这种规律。
我们不断地相信某些东西,我们一直尝试确立自己与世界的稳固关系,然后这些相信和联系又不断被一些非常细小和偶然的东西去冲击、去改变。这些微小的冲击总会在某一天生长成巨大的力量,将我们曾经坚信的东西从内而外地冲垮。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新书发布会,第一次面对读者发言时就提到:人生充满凶险,需要寻找更持久、更让人相信的东西,但同时我一边说,一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人生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现世安稳,而会迷恋很多的动荡不安,因为特别无常,所以才特别美。
就在刚上台前的十几分钟前我刚好看到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一位贻背之年的台湾老奶奶多年来一直照顾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在她80多岁时,老伴儿去世了,自此以后她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潮人,有无数幅墨镜、身着各种潮牌。到90岁时,她成为一个每天更新Twitter、Facebook、ins的人。我觉得这种巨大的改变,背后一定有巨大的怀疑。她在怀疑人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在怀疑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信,或不信。认真地听朋友说一件事,他说的时候都未必完全相信自己的叙述,而你事实上也同时听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而好的文学,也许就是那些没有被直接说出来、却藏在海面之下的八分之七的冰川。
回到写作,说说小说。
写作者,尤其是虚构文学的写作者,也许都是一些无法笃信什么的不大幸福的人。他永远在关注什么,怀疑什么,猜测什么,寻找什么。他长久在相信与不信之间的灰色地带徘徊着,徜徉着,寻找着证明自己猜测的蛛丝马迹——但最不可靠的,又恰恰是他自己的猜测,他自己也知道。
就在这样的来回动荡不安之中,强烈的倾诉欲就此发生。写作者开始和想象中的他人交谈,向整个外部世界发问,不断地打破之前的成见……我相信写作过的人都有过一种体验,真正写出来的东西和想要表达的东西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不可控因素,成功的时候可能会激发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隐藏更深的东西,也有可能极尽艰难,言不达意,面临惨败。即便是诺奖获得者,写作下一部作品的时候,即便之前有很多经验,也未必能复制。自我剽窃也是剽窃。以前的成就看似是一座雄伟的高峰,但也同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还有一种自信,是很多写作者会悄悄怀疑自己到底有无天赋,或者灵感最勃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自己若干年来毫无进步,甚至已经江郎才尽。这个时候,文学需要的自信就出现了:我们需要不断给自己鼓气加油,要相信每个人的个体经验都不尽相同,每种风格的写作者都有存在的必要。只要坚持下去,坚持多读,多想,多写,这种不信很快就会转化成相信。一切都功不唐捐。
就在这个“
重塑写作的尊严和文学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