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讲述了关于王小波的讨论,包括他的影响、作品、生活和他的遗产等话题。王小波去世后,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持续增长,人们对他的生活和作品进行了一些反思和评价。
王小波去世多年,他的影响力依然持续扩大,他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并引起讨论。他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受到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人的喜爱。
王小波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幽默感和深刻的思考,他的作品关注个体自由和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深受读者喜爱。
王小波的生活经历丰富多样,他曾在不同的领域工作和生活,这些经历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考。
王小波的遗产包括他的作品、思想和精神,这些继续影响后人。他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和思想的热爱,他的思想和精神鼓舞人们追求自由和创新。

1997 年 4 月 10 日深夜,北京郊区某小区,深夜传来两声惨叫,年仅 45 岁的王小波因为心脏病发猝死,他头抵着南墙,弓着身子,倒在地上,当时周围没有一个人。
二十年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他并没有被时代遗忘。许知远说,他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一部分。
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会怎样?
许知远采访了文学评论家李静、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他的外甥姚勇,都在反复问这个问题。他活着,会喜欢发微博吧;他的文章在今天没法发吧;他......

许知远谈王小波
他骨子里是个启蒙主义者
他是一个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塑造我、影响我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进入你的血液。他也是在自我寻找,他塑造了你,而且确实是他指的那条道路,不管是穆旦也好,杜拉斯也好,他们都奇怪地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方法。它像是一个自我的寻找,但是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寻找给我带来的感觉其实没那么强烈。
我以为它会更强烈一些,但或许因为一些东西已经内化到你身体里,你反而没有感觉了。它不再是个他者,而变成你熟悉的一部分,你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很多伟大的启蒙者一个普遍的特质,就像你读卢梭的东西不会再惊叹一样,因为他说的这些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了,所以对我来说他可能也是这种感觉吧。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王小波内化成我个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身上代表的那种气质和精神在这个时代仍然是特别稀缺的,特别独特的,甚至是更为闪闪发光的一些东西,尽管这个世界的杂音比以前更多了,但是他身上的那些东西很高贵,独特而丰富。在这个时代仍然是非常稀缺,我觉得可能比十年前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而且其实王小波并没有被好好探讨,可能很多人在探讨,但一方面是被过度探讨,另一方面似乎又没被足够的探讨。

他对人的生命的概念,就是启蒙运动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又似乎被他那种很可爱的很幽默的语言淹没,但他骨子里其实是个启蒙主义者。我们是有一脉相承的,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只不过所用的语言方式不一样而已。小波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乌托邦坍塌,因为整个理想主义坍塌,所以他表达了某种理想主义,但是他需要换种语言方式来表达,对我来说我可以更直接地表达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的幽默感还是了不起的,幽默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介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如果他的作品在 80 年代就被认可,成为那批的新生作家之一,他可能也不会成为那个王小波,他被保存了。我觉得个性始终很重要,你并不愿意跟很多作家做朋友的,可能他书写得很好,但是他作为个人来讲,没那么有意思,但小波是有个性的。他跟时代总是错位的关系,因为错位,他没有被真正地消化和理解,就保存下来了。

李银河谈王小波
他如果活着,也成不了神话
许知远:王小波去世已经 20 年了,思念他的频率还那么多吗?还是变化了?
李银河:他根本就是我的一段历史,和我的生活中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很难说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没想起。
许知远:现在这些年想起他,最常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李银河:因为我并不是外人,我跟他太亲密了,反而说不上来,可能是他这个人整个灵魂的模样吧。
许知远:他的灵魂是什么样的,可以描述吗?
李银河:我觉得就是像个大孩子。
许知远:20 年来,您对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吗?
李银河:偶尔会,我一般看书从来不爱看第二遍,但有时突然机缘巧合看一遍小波的小说,比如前不久我看了一下《 2015 》,就觉得特别好,大笑了七八次。有一次冯唐说他看一本书好不好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他笑,他说王小波的书让他笑了两回,我就说你肯定没看《 2015 》吧,这本书超过你所有的小说。

许知远:要是他看到您的小说,他会是什么反应?
李银河:他以他的标准来说,我肯定写得不好,可是大概我也只能写成这样了。但是他能看出来我喜欢的是什么,能从我写的东西里看出我是一个什么人,他能知道什么东西会让我快乐或者让我痛苦,但他不会觉得这是好得不得了的文学。
许知远:如果十年算一代的话,现在两代人过去了,还对他有这么强烈的热情,这种生命力超出您的预料么?
李银河:应当是在预料之中,可能从我第一次看到他写的《绿毛水怪》,那时候我还不认得他,还是朋友圈里传的手抄本,那本书也算是我们俩的媒人,当时一看就很震惊。尽管那个东西写得还挺幼稚,但我就看出来这个人写东西是早晚的事,不急在一时。我觉得这个人生来就是干这个的,从没动摇过。

许知远:您怎么理解他的文学趣味的形成?有没有一个核心?
李银河:他挺喜欢法国新小说的图尼埃尔,还有卡尔维诺的《住在树上的子爵》,他大概就是喜欢所有跟他的气质接近的作家。我有时候看达利的画,马上就想起王小波的小说,所有的细部都是真实的,但一看整体又是超现实的,比如飘在空中的大象。这个就是他的风格,他喜欢的是这种东西。
许知远:您觉得这个时代更理解王小波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他的知音不少,我还写过一篇文章,《王小波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好多人都喜欢小波,他们互相认出来,我认识有一对女同性恋就特有意思,她们俩谈恋爱,就是在王小波的墓上遇见的,她们俩分别去给王小波扫墓。

许知远:如果他仍健在,您觉得他会对这个时代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最可笑的一回是我编了一套文集,把王小波和许纪霖、何怀宏这些人放在一起,结果王小波没通过审查,后来说可能是题目没选对,当时选了他的一篇文章名叫《知识分子的不幸》,这个名字选坏了。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反感这个,幸亏那个时候他的全集已经出来了,按现在的标准,一篇也出不来。
许知远:他会写博客用微信吗?
李银河:我觉得他应该会,因为他有想说的话。一个好的作家,写杂文或者写小说,就是他有话想说。
许知远:他会接受自己成为一个神话的现实吗?
李银河:我觉得他如果活着,也成不了神话。
他让我成了一个富有激情的人
许知远:您觉得他这 45 年里头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
李银河:他最高兴的可能还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吧。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因为他在街道工厂,我在《光明日报》,我给他写信,用的是《光明日报》的信封,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全厂都轰动了。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社会地位有那么大差别,当然他很得意,他们家亲戚还觉得天上掉馅儿饼,捡个了大宝贝的感觉。

许知远:看您的回忆说,你们关系从来没有紧张过?
李银河:没什么冲突,可能他的脾气太好了,有时也是他要求不高,比如我做饭的水平就不怎么好,从小我们家都吃食堂,哪会做饭啊,瞎做,然后他也就凑合吃。后来他给我讲故事,挺会自我解嘲、自我安慰,就说有一个女博士,他老公让他下挂面,结果把拖鞋下锅里了,他说你至少还没做出这种事。
许知远:您觉得他懂你么?他全盘懂你么?
李银河:他应该懂吧,我也没啥秘密,我也不深奥,我很简单的,我的心思不用猜,特直来直去。
许知远:那您都懂他么?
李银河: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他是一个非常清澈的人,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或者太多的想法。或者就是他不愿意说,我始终没问出来过,有的时候我能够从他写的小说里察觉到一点他的心理,问他受了什么气,问不出来,他也不说。我觉得他心里有一股挺大的劲儿,这种劲一定是从一些挫折上来的,但这个挫折具体是什么,我没问出来过。
许知远:所以您也没有搞清楚他内在的驱动力?
李银河:对,我看他写的东西,有时候会觉得他一定是受过大委屈。

许知远:他生前恐惧过死亡吗?
李银河:他很少提这个事,还是相当突然的。他没怎么想过,倒是我还是挺喜欢想那些虚无的东西,比如说宇宙和人生的无意义,爱想这个的人比较苦,常常有失重的感觉,人就是宇宙里的微尘,真的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是挺幸福的,他不怎么想,他好像只顾着兴致勃勃地做他那些事情。
许知远:他的遗憾呢?
李银河:他的遗憾就是活得太短了,我觉得他应该再活两倍那么长,活到 90 岁就好了。
许知远:当时是怎么从失去他的痛苦中复原过来的?
李银河:还是我那种一贯虚无的世界观把我救了吧,我会觉得 45 年也就是一瞬,再活 45 年,也就是比他晚了一小会儿。你要是这么想的就比较容易过去,把时间拉长了看,他就是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了。
许知远:新的爱情会帮助您从这个痛苦里走出来?
李银河:跟大侠认识以后,我就感觉他是上帝派来救我的,因为他也爱得很激烈,跟小波完全不同。本来我根本就没这个想法,还有谁能超过王小波?王小波要是一瓶醋,其他人在我看来就是半瓶子,你说我怎么能看上。结果这个家伙是一瓶酱油,没有任何可比性,从来不看书,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阶层,甚至是另外一个性别,从身体到精神,一点都不像。这反而挺有趣。但他也挺嫉妒的,王小波已经去世了,他还嫉妒得不行。

李银河和现在的伴侣大侠(左)
许知远:我看他追您的时候,也读小波的书,他是什么感觉?
李银河:那时候他是出租车司机,就是为了追我才读的,他哪儿有那兴趣,他老开车,老搁在挡风玻璃那里,晒得都开胶了。虽然他真的下了点功夫,但他有他的生活,平常差不多天天晚上打麻将打到半夜,是这么一个人。
许知远:您觉得他后来理解您和小波的感情吗?
李银河:他很理解的,我觉得爱这个东西都挺像的,发生了激情之爱,他当然就理解了小波对我的爱是怎么回事了。

许知远:现在回忆起来,那 20 年的时光,他对您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呢?
李银河:他使我变成了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不过也我初恋时也挺有激情的,虽然是单恋。我最近看到福柯,他跟他男友德菲尔同居几乎一生,他说了这么句话,这 18 年我们一直处于激情之中。看了这个以后,我很震惊,原来我以为激情是会变的,就像熊熊烈火,很快就变成柔情,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保持激情呢?小波和我跟实际上也一直保持了激情状态。现在我不太能够忍受没有激情的生活,我愿意一生保持激情,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这是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昔日的李银河与王小波
许知远:那您对他的改变呢?
李银河:也许我让他实现了自我吧,在他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我还是帮了他的。好多人都说我是慧眼识珠,特别早就看出了他的天分。也有很多天才后来就被扼杀了,我看《卡夫卡传》里,他一直想写,可是他就是公务员,好不容易可以去哪儿独自写半年一年,后来也没实现。在小波的生涯里,我可能就是给这个天才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他辞职,可以整天整天地写,没有逼着他去赚钱、养孩子,没有给他一点压力。从留学的时候开始,他就是去陪读,可以写小说,两个人花我一个人的奖学金。让他能够把他的才华写出来,不用在谋生上花时间,这个是我可能对他最大的帮助了。

李静谈王小波
编者按:李静,辽宁兴城人。1989-1996 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1996-2000 年在《北京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2000 年供职于《北京日报》副刊部至今。她是国内最早认识到王小波的文学和思想价值并刊发其作品的“推手”之一。
他的启示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
许知远:在他生前,你觉得什么是最让他抑郁的事情?
李静:最让他抑郁的事情,第一是作品无法正常的发表。同时这种状况影响他正在进行的创作,因为他心情不好,各种信息告诉他,他的东西很难发,因此他很难跟人去好好的交流。其实他是一个特别看重交流的人,他觉得这种精神交流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土壤,他写作就会非常状态不好。他还特别看重朋友的意见,特别看重感情,王小波从来没让我觉得失望也是这个原因,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是一个那么朴实、善良、有爱的一个人。

李静
许知远:他去世之后变成一个神话,你意外吗?
李静: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意外。王小波的表达方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非常出色的表达,这个价值认同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对于他这种表达方式本身的艺术性,有非常强烈的体验。我觉得 50 后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对于我们 70 后,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启蒙。
许知远:人文知识分子是非常明确的给他评价,小说家好像又在回避这个问题,是不是?
李静: 看他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先是被他的幽默打动,然后被他的稀奇古怪的想像力打动,说一定这个人是特别有意思。看完了就发现,他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但是又抓不住。后来我想到一个词,就是“点彩派”,我觉得他《黄金时代》那本书里的那几篇,尤其是他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每次看好像都感觉不一样。

许知远:把他放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里,你怎么看他?
李静:王小波的艺术性和启示性、他的思想的能量,我觉得起码是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的,他的小说,包括他的杂文。作为一个文学的成果,鲁迅和王小波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鲁迅的小说也不多,甚至比王小波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到说,鲁迅他有一种原形能力,我们到现在会指认谁是阿 Q,某些人是九斤老太,是他的这些人物有一种极强的概括力,这种概括力是穿透古今的,他是对一些灵魂类型的勾勒,然后这种灵魂一直在活着,像雕刻家一样,他的那个刻度极深极深的,王小波也是这样。
许知远:他们俩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李静:最不相似的,其实还是如何看待个体自由的价值上。王小波虽然不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个人优先,这是一个前提,而且在他来说,个人的创造力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指标。鲁迅不是的,鲁迅最后会明确说,平等要比自由更重要,在鲁迅那儿,个人的自由不是必须要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在个体自由这个概念上,鲁迅还没有太自觉,他会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有牺牲的义务,他会由此推己及人,他会要求精英阶层牺牲掉自己,去为大众,去为更苦难的人去做事。

许知远: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大家对他的记忆还是在减弱,和 2002 年五周年或十周年的时候相比?另一方面他的重要性又在增强?
李静:你说的这个太对了。而且恰恰这彼此还有点因果关系,他的影响力在减弱,实际上是这种理性的自由的声音和力量在衰减,但它越在衰减,其实就越需要它,在慢慢地向这种噤声不语、无声的中国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
许知远:其实回到九十年代初,《黄金时代》出版,先锋文化兴起,他也是其中的之一,这个气氛后来就慢慢都消失掉了。
李静:对。其实你看实验文学是八十年代非常火的,等于说 1985 年,我们学就是说八五新潮,那时候就像中国的文学大爆炸似的,那些先锋作家都在 1985 年突然冒出来,但那时候小波不是在美国,他没有参与这个。
所以他就说,在九十年代大家都不想文学这回事儿的时候,他才写小说。他说,我这个完全都和热没关系,就是因为我想写小说,我觉得我有这个才能,然后我就写了,我也不管这个时候文学还热不热。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在文学评价体系里非常尴尬,不知道把他往哪儿归,因为那时候大的文学潮流是在向世俗化、平庸化来转变,就是什么新写实、新体验,都是写鸡零狗碎的那些事儿。他完全是一个另类,大家还会觉得还这么搞文学实验,这不是是我们玩儿过的事儿了吗?
许知远:一个浪潮之外的人?
李静:对,他就是一个荷戟独彷徨。

姚勇谈王小波
编者按:姚勇,王小波的外甥,他叫王小波的母亲姥姥。姚勇经常同王小波见面,那会儿,计算机只是新事物,王小波的号召力,并没能真正被他的亲戚们觉察,所以在姚勇看来,他只是一个说话幽默,为人有趣,还关心自己,同自己谈未来的舅舅。他只是一个和蔼的长辈。当时高中时的姚勇,因为喜欢摇滚学习一团糟,王小波同他聊了好几天,对他一生影响巨大,后来还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开头是: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
姚勇在清华,靠着这篇文章,吸引了很多女孩儿。他后来成为知名乐队“水木年华”的成员,后来离队,创业做游戏公司至今。
他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服从主流
许知远:你觉得他要晚生个十多年二十年会去创业吗?
姚勇:不知道,这个东西想过,但是完全做不了假设,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遇。
 王小波故居
王小波故居
许知远:小波去世这么多年了,很罕见的一个作家可以有这么长的生命力,而且是一个很具体的生命力,你觉得什么原因呢?
姚勇:其实这事我想了很久,首先,我没想明白。第二,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对他的一些话比较印象深刻,他说他把人分成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我的阴阳两界》,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一看就是属于我们的人,有些人一看就是他们的人。后来因为我也在社会上等于是打拼了,最后总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其实这个世界上,你假如粗浅地分,有一部分人追求功利,功名利禄,这种物质或者这种权力。因为金钱、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主流。然后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比如说知识、智慧、精神、艺术,关于怎么去生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许知远:你觉得小波要活到现在,他会喜欢这个时代吗?还是更反感?
姚勇:我觉得他在任何时代可能都那样,我现在都四十多了,我还是觉得都是命,他有他的追求,他的追求我觉得在什么时代都会是那样,因为不服从主流,必然会受到一些障碍。
许知远: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纪都快接近 45 岁了,他离开的那个年纪了,对他的理解会有什么轻微的变化,或者感受?
姚勇:这个问题,分成两边说。一个角度其实是家属的角度,有时候想起来比较唏嘘,亲人突然离世的这个感受,这个感受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其他人也不会有,这是作为家人而言,而且他没有孩子嘛,我是这边可能最大的,所以一直跟他接触,他也挺喜欢我。然后一方面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特立独行的东西,我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创业者,或者到一个企业家这个过程,我还是觉得他一直会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或者是被少数人所推崇的一个东西,不会是一个大众的东西,就是你对社会认识越深入,你会发现其实他追求或者追寻的这一套东西依然是很小众的,非主流的。
许知远:他倡导的东西仍然没法被更多人接受。
姚勇:是的,而且咱们 70 后,70 年代、80 年代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正在转,等到这十几年,其实我原来以为它会越来越不被人所知,然后直接就被淡出,但实际上没想到(生命力越来越强烈),这点没想到。

童年时代的王小波
许知远:你说比起 90 年代,你觉得这个社会是理想主义色彩更淡了,是不这种感觉?
姚勇:那肯定是更淡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诗意的感觉,有一些,当时还看看诗什么的。这个年代,这个房价蹭蹭往上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竞争很激烈,那这样的话,你精力自然就放不到精神生活层面一部分了,先满足物质这个层面再说,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后来我从事的职业呢又是为青少年,或者是说并不是说很有钱去娱乐的那部分人去工作。其实做游戏产业,它是一种最便宜的娱乐方式,你要了解这批人,你要了解他们什么生活状态,他们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去满足他们的想法和娱乐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中国绝大部分主流人群其实活得还是不很富裕,真正说能有机会去看看书,去了解、体验一些精神层面的人群太少了。

许知远对话姚勇(左)
许知远:你觉得小波看到这个会怎么评价呢?
姚勇:还好吧,我觉得还好,我曾经很多时候就想,他在这个时代,首先他的小说形式肯定会按他的想法,会多样化,不管是纸质的、电子的,还是多媒体。第二就是说,其实新兴的科技呢,社交、自媒体其实给他的机会也会更多。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活得更好一些。
他最后的创作遇到了瓶颈
许知远:你觉得他内心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吗?你还回忆起来吗?
姚勇:作为晚辈其实不太了解,但是通过看他的那个《黑铁时代》,我才知道那个状态是怎么来的。现在文章也都说,他最后那个阶段创作方面可能碰到一个瓶颈,然后导致身体也不好,情绪也不好,肯定是进入抑郁状态,抑郁状态反过来又有影响。他老婆也不在,所以就是滚雪球一样,越来越恶性循环。每周我都会回来跟他聊,看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最后一年,嘴唇全是黑的。我当时记得特清楚,姥姥就说,(小波)你去看看,你肯定不对,健康有问题,后来出事了就发现确实是这样。

许知远:春节是你们一块过的是吗?
姚勇:对对对,最后一个春节,还放炮来着,说去去晦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指的什么,但是肯定是诸事不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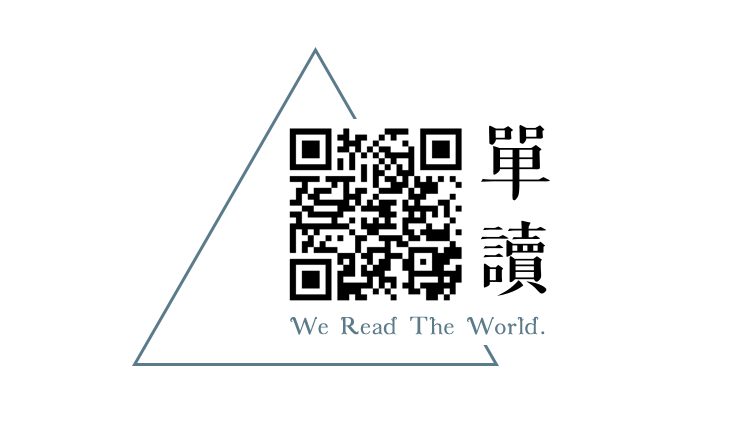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王小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