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春松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孔教国教化及其争论
民国初年,孔教会试图使儒家重新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就是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依托,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
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梁启超、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提出:“周、秦之际,儒学大行,至汉武罢黜百家,孔教遂成一统。自时厥后,庙祀遍于全国,教职定为专司,经传立于学官,敬礼隆于群校。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 他们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意”的方式来论证应该将孔教定为国教:“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有必然者。或疑明定国教,与约法所谓信教自由,似有抵触,而不知非也。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于是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孔教会的请愿文发出之后,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回应。黎元洪和浙、鲁、鄂、豫等10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都先后通电表示支持。 当时普遍认为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和道德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家之退出制度化体系而造成的价值真空。黎元洪称:“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 而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对此的设计显然更为详细。他说:“比年以来,我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议者,靡不曰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绳。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说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此厚根柢之说也。(二)以孔子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此崇信仰之说也。”这段话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孔子思想排斥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种批评。
在社会上积极响应孔教会的请愿书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有政界和知识界的,也有宗教界的,比如,基督教人士马相伯,置其他宗教普遍存在的奉献制度于不顾,而对孔教会的“交会费”和试图通过主持结婚仪式收取费用的办法污蔑为将孔夫子当成“财神爷”。议员何雯等则从儒教的特质和信仰自由的角度认为不应定孔教为国教,理由是:“(一)中国非宗教国;(二)孔子非宗教家;(三)信教自由宪法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四)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孔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国教和信仰自由之间的关系,的确是支持和反对孔教国教化的论辩焦点,而康有为、陈焕章在辩驳中也必然会说明孔教与信仰自由之间何以并不冲突。
基于宗教和政治立场差异而产生的争议也呈现在具体的宪法操作之中。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二十三日,赵炳麟议员提议立孔教为国教,表决之后列入议题。二十七日继续讨论,陈铭鉴、汪荣宝等人表示赞成。而何雯和伍朝枢等人表示反对。
其实支持和反对孔教并无明显的年龄和党派背景之差别。所以民国初年国会中关于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体现的是社会思想中对于儒家的矛盾态度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儒家重新制度化的努力最为突出的方式就是试图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这是一种在现代宪法的框架下,将儒家制度化的方式。与传统的将儒家独尊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解决现代宪法中的信仰自由原则和将儒家定于一尊之间的矛盾。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议主要也集中于此。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以孔子之道为风化之大本”的提案。
1913年10月13日,议案付诸表决,出席者有四十人,首先表决“宪法中应规定孔教为国教”,赞成者八人。其次表决“中华民国以孔教为人伦风化之大本”,赞成者十五人;第三次表决“中华民国以孔教为人伦风化之大本,但其他宗教不害公安,人民得自由信仰”,赞成者十一人。因议案需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赞成才能成立,因此这三个议案全部被取消。
10月28日,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二读已过,汪荣宝又提出在十九条后加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之大本”,引起争议,后改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三十一人表示赞成,获得通过。
袁世凯死后,旧的国会又恢复了,1916年宪法的修订继续进行,这时陈焕章再度提交了一份《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理由基本上与前一请愿书一致,不过这一请愿书认为这些那些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议员们还不如“袁(世凯)氏之真能代表民意于万一”,并将那些建议取消祭天祭孔的议员称为“败类之议员”。“夫以中国最可宝贵之孔教,为全球所仰望,而吾国所恃以自豪世界者,而竟不甚爱惜,不定为国教,则其所爱者,果安在哉?想亦不外其个人之生命财产耳,其有丝毫国家之观念存乎?若是者诚可谓无教之禽兽矣。” 陈焕章特别强调孔教的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将孔教视为保存“国性”的重要指针。“焕章等敢大声以告国人曰: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故吾民之请定国教也,非独尽忠于孔教也,其尽忠于中国尤挚。盖孔教虽不立为国教,孔教未必遂亡,虽立为国教,孔教亦非独占。若专就孔教言之,固无大加损也。然而其影响之及于吾民吾国者,则大莫与京矣。是故苟不定孔教为国教,则吾民不得复为华民,吾国不得复为中国,只合为隶属国而已。”
191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陈焕章为会长,康有为和张勋是名誉会长,并组织请愿团来解决国教问题。
议员们似乎没有被请愿团的热情和军阀们的气势所压服,情况甚至更糟,且不说立孔教为国教,就是《天坛宪草》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一妥协性条款的存废问题也引发争议。
张鲁泉、何雯等人建议从宪法中删除这一条,理由是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与民国的国体不符合;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合;国民教育问题属于行政范围,不应由宪法来规定;修身属于道德领域,与宪法的性质不合,而且国民教育是强迫教育,如果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那么别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就会被视为非法。国家如要尊重孔子可通过别的途径,而不必争此一条文。而汤松年等人主张维持原草案中的规定,他们认为不能将孔子之道视为宗教,因而与信教自由无关;全国人民依然信仰孔子,而孔子之道是培养社会道德的基础。原先的宪法中已经有这一条,随意删去恐给人以别的联想,而且在别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还以外国教堂中读四书五经等来证明孔教并不会导致与别的宗教之间的争端。
对于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也继续展开争论,双方的理由与第一次辩论基本一致,经过投票双方的提案均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最后双方做出让步,达成如下妥协:删除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但在原十一条“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1913年和1916年二次关于是否在宪法中规定以孔教为国教的争论,并非是一股空穴来风,这里面所包含的问题很多,有政治和道德之间的问题,也有新体制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在儒家制度化体系解体之后,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人的思维深处依然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儒家在失去其制度体系的支持之后,如何寻求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困难。而新制度和旧伦理之间的紧张及如何克服这种紧张之间的分歧,恰好体现在这些争议之中。
但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军阀和议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民初政治生态的独特景观。或许是认定了儒家价值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军阀们有意地利用这种心理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作为民国首任总统的袁世凯在他的总统就职宣言中,便将传统的纲常礼教归纳为“忠”“信”“笃”“敬”,并根据严复的提议,在1914年11月3日颁布的《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中宣布“忠孝节义乃中华民国的立国之精神”。在利用社会舆论对“君主立宪”和“共和”制进行对比之后,鼓励筹安会对于“国体”问题的所谓“自由”研究。最终袁世凯还是走向了对帝制的复辟。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张勋的复辟与孔教运动
在晚清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的时候,原先在社会势力分层中处于边缘的地方军事势力,特别是汉族的地方军事势力完成了“中心化”的过程,而急剧膨胀的军事权威成为无序化社会的主导者。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虽然不能将外国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的地主或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简单的类比,但是“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的确是对近代中国权力生成方式的最为简洁的表述。
任何权力的确立都会本能地去寻找其拥有权力的合法性依据,而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军阀们显然不能将暴力作为依据,势必会按自己是“民意”的代表的模式去包装自己。然而,作为真正“民意”的体现的直接选举和议会制度并不适合军阀们的“本性”,按袁世凯的说法就是太麻烦。就在1912年7月18日,临时参议院否决他所提出的国务员的名单时,他就已经很不耐烦了,马上通令各省,认为议会“乃自党见既兴,意存制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一度政府成立,疏通动须数月。求才则几熏丹穴,共事则若抚娇儿,稍相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难于登天。……而国会纷争,议案众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民主程序与专制独裁之间是天然的敌人,看上去烦琐的程序为后来袁世凯解散国会,解散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埋下了伏笔。确切地说袁世凯完全是以传统的政治价值观来理解他的政治权力的,因此任何的反对和不同意见都被视为是对他的政治权威的否定。这从他对“民主”“自由”“共和”这三个词的解释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在1913年12月15日发表演讲说:“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 袁世凯所面对的困境来自多重原因,比如权力的来源、比如国民党试图用议会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等,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旧军阀对于如何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国家,都缺乏基本的了解。
基于对于新的共和政治的陌生,以及对于程序性秩序的抵触,军阀们倾向从传统中寻求资源。而在他们的观念里,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强调上下尊卑的,所以,对尊孔运动乃至孔教会表示同情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特别是中国军队的成员来自于农村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新观念的了解相对滞后,所以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
如此一来,康有为的孔教会的设想与军阀们追求权力合法性的诉求有了共鸣。袁世凯在接受政权之后,就借助改革礼俗的时机,重新厘定祭孔的仪式,对孔门后裔进行册封。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虽然罗永绍等议员以“违反约法信仰自由”对这项命令提出质疑,但是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依然发布“规复祭孔令”,规定“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长官主祭。……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致祭” 。同年2月20日又发布了《崇圣典例令》,其中第一条规定:“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有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规定:“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并每年可从国家获得固定的祭祀费用和设立专门的“圣庙执事官”。

在这段时间,袁世凯与康有为也有一些互动,1913年冬袁世凯致电康有为,希望他回国主持“名教”,而康有为亦回电希望袁世凯尊孔拜圣。特别是1913年11月29日《覆袁大总统电》中,曾说:“伏王明公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议,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 虽然动机不同,不过康有为的这些建议似乎都被袁世凯所接受,并转化为具体的行政措施中,蔡元培所推出的比较激烈的将孔子及经学从一般的教育体系排斥出去的教育纲领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终止。由此而来,各地尊孔读经之风复燃,并被认为是解决日趋活跃的学生运动的手段。在许多呼吁恢复读经的请示之中汤化龙的《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年)最具代表性。他说:“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说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虽然表示要避免孔教的狭隘性,但在同年6月,教育部便发布指令,要求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1914年12月,教育部提出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核心也就是恢复读经。“中小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 而1915年,袁世凯政府又出台了《特定教育纲要》,提出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办学宗旨,这样学校尊孔读经又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人亡政息,民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随着袁世凯的死去也很快被取消,1916年,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表示,要确实执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即回复蔡元培时期的教育方针,撤销袁氏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和《特定教育纲要》,再度废除小学读经。
显见之,袁世凯之尊孔是无可置疑的,孔教会也希望袁世凯支持以孔教为国教,但是,康有为是坚决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举动的,原因在于康有为并不认为袁世凯堪为新国家之象征。黄克武先生指出:孔教会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陈焕章和严复,都不支持帝制,康有为专门写过劝袁世凯退位的文章,而严复之参加“筹安会”则是被迫的,所以说:“一、就帝制与尊孔的关系而言,袁氏帝制运动并没有企图诉诸民众的情绪,他们的理论基础虽然是政事取决于民意,但他们深信民意可以轻易地制造出来,因此他们似乎不是有意地以尊孔作为‘思想的前哨战’,袁氏尊孔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以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秩序。二、袁氏提倡尊孔应无疑问,但他并不完全支持孔教运动,孔教会的成员也不支持他的帝制运动,因此‘袁氏利用孔教会以推行帝制’的说法实属谬误”。 但孔教会和帝制之间恐怕不是很容易脱离干系,首先,普遍的看法是袁氏尊孔,意在当皇帝。 其次其他的孔教团体的确有“劝进”的举动。
将孔教会和帝制复辟彻底挂钩,并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攻击对象的直接原因张勋和孔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在1913年陈焕章等人提出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请愿书之后,张勋就马上发表通电支持。并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在1916年重开国会,陈焕章再度提出相同要求的请愿书之后,张勋联合曹锟、张作霖等人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口气就十分强硬,认为应废除三分之二人赞成通过的原则而改以各国的通例直接定孔教为国教。“今欲定宪法,自不能不立国教,刻已列诸议案,后经人民多数之请求,而竟遭摈斥,不获通过,非特拂逆民情,或恐激生他变。窃谓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国教又为宪法之根本,问题何等重要,非另组特别制宪机关,直接取决于多数之民意,不足以称完善。断不能用国会中寻常议事法则,以院内少数议员,三分之二之多数为多数,所能轻言规定者也。即按法理而言,并以各国成例证之。”该通电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怀疑《临时约法》所赋予国会制定宪法的权力的合法性,并认为如果由于没有定孔教为国教所造成“危及国家”的社会问题将“治以重罪”。通电说:“国会由宪法产生,本无制宪之权。我国今日之国会,早逾法定期限,已失人民信仰。徒以《约法》所规定,为制宪机关,使能体察民情,为我国制定良好宪法,人民犹将谅之。乃少数议员等,既不亟图补救,甚复妄有主张,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1917年6月8日,张勋带着辫子军进京,胁迫黎元洪 解散了国会,在康有为参与下,7月1日,张勋正式拥戴溥仪复辟。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发出了贺电说:“日月重光,毅然殊猷,普天同庆。” 孔教会的核心成员均在新“朝廷”获得了职位,如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沈曾植任学部尚书,劳乃宣任法部尚书。
张勋复辟所坚持的时间只有12天,却将尊孔和独裁政治的联系进一步建立起来,并在陈独秀等人的宣传下,成为一种论说模式,从而使儒家日益成为科学、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陈志让说:“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任大元帅(1912年到1927年),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部尊孔。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27年张作霖下令制定礼制,次年祀孔。在这两个年代之间,许多军阀公开扬言要以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下的各省下令读儒家的经典,特别办学校来发扬儒家传统。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佣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发表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词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例如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段祺瑞打败张勋挽救了民国,理由也是儒家的纲纪。”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孔教会和军阀们之间的互相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激进知识阶层对于儒家的攻击,同时也使之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社会进步的对立面。 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儒家依然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但在现代社会将儒家重新制度化已经十分困难了。对此鲁迅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鲁迅的话虽然刻薄,但对于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与军阀政治的复杂关系的刻画却也是入木三分。

本文受权摘自《制度儒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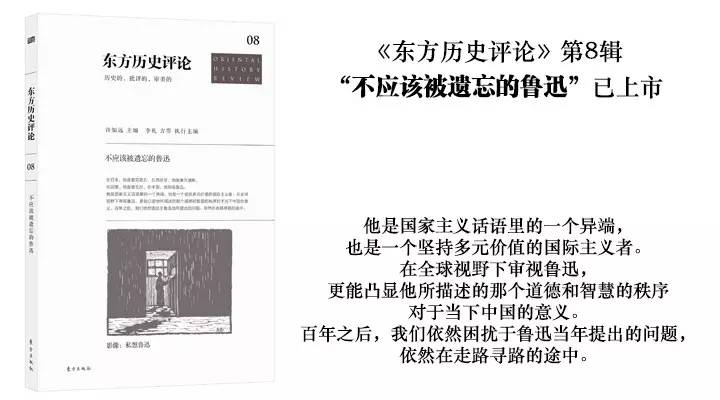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