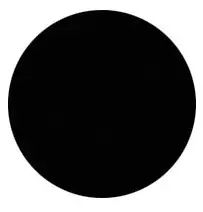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是一首来自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节选,《基韦斯特的秩序观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1934)。在2011年,杰·帕里尼将这首诗排在了所有美国诗歌的第二位,仅次于沃尔特·惠特曼《我的歌》。
Oh! Blessed rage for order, pale Ramon,
The maker’s rage to order words of the sea,
Words of the fragrant portals, dimly-starred,
And of ourselves and of our origins,
In ghostlier demarcations, keener sounds.
(诗歌全文参见: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3431/the-idea-of-order-at-key-west)
诗的故事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个岛屿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包括海明威和弗罗斯特在内的许多文学家,经常访问基韦斯特,以期从那里获得灵感,史蒂文斯也是其中之一。这首诗在哲学上是复杂的,想象与现实相互依存。全诗描述了叙述者和他的朋友看到一个女人在海边唱歌的场景。歌声与大海之声亦真亦幻,她是歌者,也是缔造者,她心中仿佛一无所有,却缔造了歌中之境。一曲既终,叙述者转过身,面向现实中的小镇、灯火、渔船与夜幕。
这首诗的出版时间比这本书早了近一个世纪,但它们都在讲述关于秩序的故事,故事中都包含着一股巨大的张力。前者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无疑是重要的写作背景。战争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岌岌可危的旧秩序,而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西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诗人在各种意象之间,勾勒出战后真实世界中的失序、分裂、破碎与无意义,而透过诗中海边女人的歌声,仿佛又缔造了一副想象世界中的山岚、海风、星光与地平线。在真实与想象的张力中,诗人发问,“雷蒙弗尔南德斯,如果你知道,就告訴我吧,为什么一曲既终,我们转过身,面向小镇,为什么闪烁的灯火——停泊在这里的渔船上的灯火,在夜幕低垂之后,在空中倾斜——雄踞黑夜,平分海洋。厘定了明亮的地带和炽热的两极,摆布着、低沉着、魅惑着的夜。哦!可怜的雷蒙,保佑对秩序的狂热吧,缔造者狂热地把大海的语言排列成序,这是芬芳之门、星光隐约的语言,这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起源的语言,在更为朦胧的界限中,在更为锐利的声音中。”
后者,也就是劳伦·本顿与利萨·福特的这本书,Rage for Orde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0-1850,探求的则是历史中“不为人知且不同寻常”的故事——大英帝国曾试图通过对法律的重新设计,为19世纪早期的世界,重建全球秩序。而本书的最后一章,又以“大无序(A Great Disorder)”为题,以“大无序即秩序”为最后一节,揭示了作者对这一秩序的解释核心,可能恰恰就在于一个悖论,即这种秩序的本质就是无序。大英帝国通过法律构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偶然和混乱的过程。在这种看似悖论的解释中,我们能读出作者对帝国秩序的重构与批判。而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国际法的诞生有了全新的“史前史”叙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国际法史的研究都依赖于经典文本,或是理论著作,或是重要判例,通常集中在思想史领域,但作者的关注点在于不同政治体的关系、动态博弈和具体实践。作者通过对法律实践、法律多元主义和管辖权冲突的研究,重构了帝国秩序的面相,并剖析了这种帝国秩序如何影响国际法的发展。
作者从调查委员会、殖民地请愿书和内部备忘录这些尘封已久的琐事入手,描述了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进程: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英国于1815年成为全球性强国,并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在此期间,新老英国臣民开启了一项狂热的、发端于多个中心的努力,即试图通过法律变革,为民众、地方以及从拉普拉塔河岸延伸至波斯湾和广袤的太平洋群岛的商业交易构建秩序。而英国对秩序的渴求,对殖民地的内部和外部治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借助跨越文化与政治隔阂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这一通过法律为帝国重构秩序的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它改变了世界格局,使帝国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枢,并构建了一个政治上碎片化的区域性法律体系。
而在面临如何解释19世纪末 “帝国法” 向 “国际法” 的转变这一问题时,作者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路径。即要么把19世纪欧洲帝国力量向全球的扩散和欧洲法律实践在殖民地的翻版过程,解读为19世纪的国际法形成历史,要么把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自下而上的人权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普世的、共同接受的国际人权法基础,视作后来正式国际法的起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抓住的既不是“顶层设计”,也不是“底层反抗”,而是殖民地的中级官僚阶层(mid-officers)。作者认为这股中层力量,或许才是国际法诞生的关键。
与此同时,另一种对国际法史的研究路径,与当时“崛起中的帝国——美国”有关。学者们将美国宪法描述为一份深受万国法理念和实践影响的文件,《独立宣言》使某种政治实体的内部行为呈现出实证国际法的特征。《邦联条例》与《联邦宪法》本质上属于北美各州之间的和平协议,而其思想基础在于将联邦主义视为多层次帝国主权结构的一种变体。这一传统深深根植于欧洲,实现了政治实体间“内部”和“外部”秩序框架的融合。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大英帝国宪法的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就在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连通。
最后,作者回到了帝国秩序的合法性批判。很显然,帝国秩序无法阻止暴力的出现,也无法实现国家间的平等——“在大英帝国的法律政治影响下形成的区域性体制蕴含了难以根除的暴力,同时,它们也使国家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具体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英帝国对法律秩序的重构,仿佛反思性地塑造着今日为人们所熟悉的正式国际法,但它所指向的世界,是一个约翰·奥斯丁认为永远不会出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