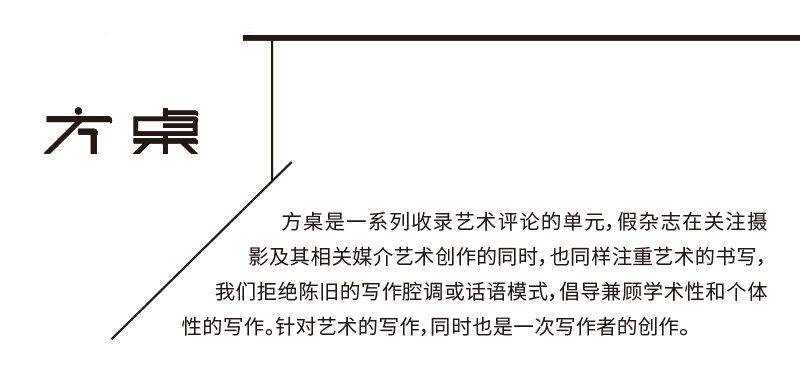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无头照片”了。事实上,根本不只是现在,自从两三年前或者更早,无头照片就几乎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图式,仿佛,因为不具更多考证和定向含义的潜质,可以让它可以毫无违和被纳入到各式结构中来,这种流行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频繁的出现,让它看起来像极了一场自发的、毫无导演性质的、且空前的形象祛魅的运动。可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种破坏呢?我没有办法做过多揣测,那么在这里,我想展开一次对消失的脸作为一种图式的“怪谈”。
像破案一样,无论这样一张照片多么的迷人或吊诡,剔除掉的面部总是要充当关键线索的。那么,一张“脸”究竟可以意味着什么?

©Katrin Koenning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他人的脸》中曾讲述了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失了脸的男主人公身上发生的离奇故事。在男主的认知里,脸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如果脸烂掉了,没有了,或者换掉了,那么他作为某人的内在同样与之匹配的应该是腐烂了,消失了,或者变成他人了。在这些叙述中,伴随着从陷入绷带中的脸到在面具下生活之间,他的心态变得困惑和扭曲,也正因此他认为越过法律和道德而没有节制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所认为的他的真实身份是无法为外人所辨别的)。安部公房从这种心理转变的描绘,来引发关于真实、自我、存在、身份等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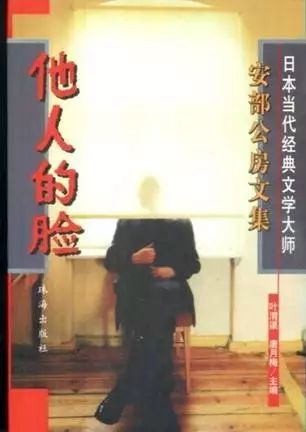
小说《他人的脸》封面, 安部公房
珠海出版社, 1997年出版
“如果说用衣裳来包裹肉体是文明的进步,那么,也就无法保证将来蒙面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小说中安部公房写下这样如预言般的句子来作为隐喻。而几乎作为一种“回应”,当面对在摄影(或其它类型的图像)中出现的一幅没有脸庞的肖像时,它能指向什么?又是如何在各自构筑的体系里生效的呢?我们在阅读这样一张照片时所能获得的感受仅仅是出于对身份无从辨识的恐慌和猎奇吗?我想,远远不止这样。
我们当然无法像看安部公房的小说那样通过揣测心理的变化来思考问题,而就是这样一张肖像,我们却又似乎可以在仅有的线索下(创造的时代背景、话语建构及其系列的其它图像)来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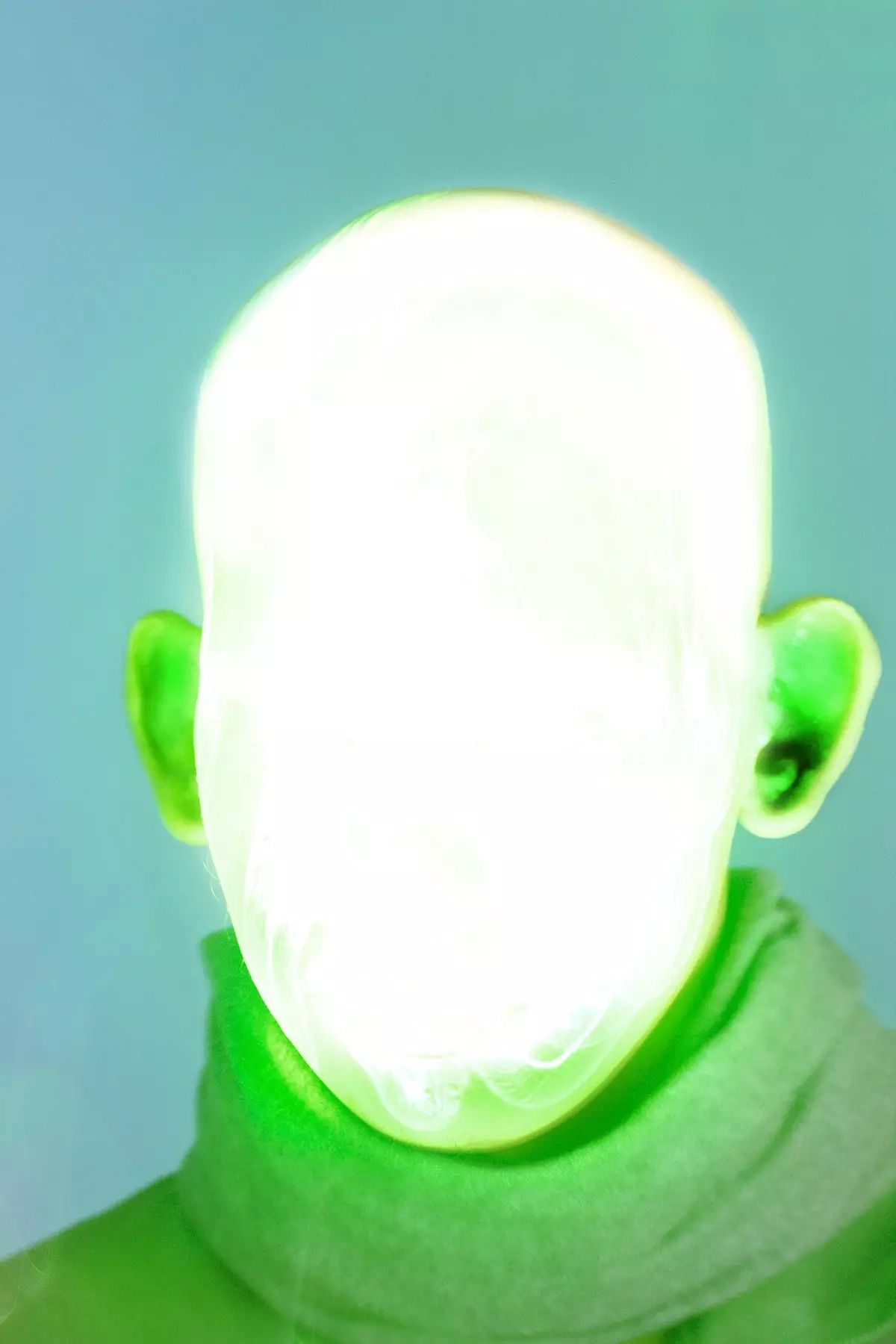
©Debashish Chakrabarty
首先,正如几乎所有人能够达成的共识一样,由于“脸”作为最直接的辨识特征将人类身份与存在显现并连接起来,这也使得一张“无头照片”很难不和身份的议题产生关系。这种情况下,许多实践者将这样的图式充当了对某种政治状况抵制的方式。
比如西班牙摄影师Julián Barón的作品C.E.N.S.U.R.A.展现了一系列领导人在政治场合进行会议的照片,而他选择的方式是通过闪光灯的高倍输出加上一种极具新闻式的拍摄方法,以求得这种光线溢出的甚至有点南辕北辙的非常态新闻照片,来以此达成个人的抵抗。
在Barón所提供的情景来看,领导人出现在会议厅(这种实行决策权的场所)可以说是其政治身份获得最大化体现的地方,而他们的脸几乎可以等同于一种政治观点和立场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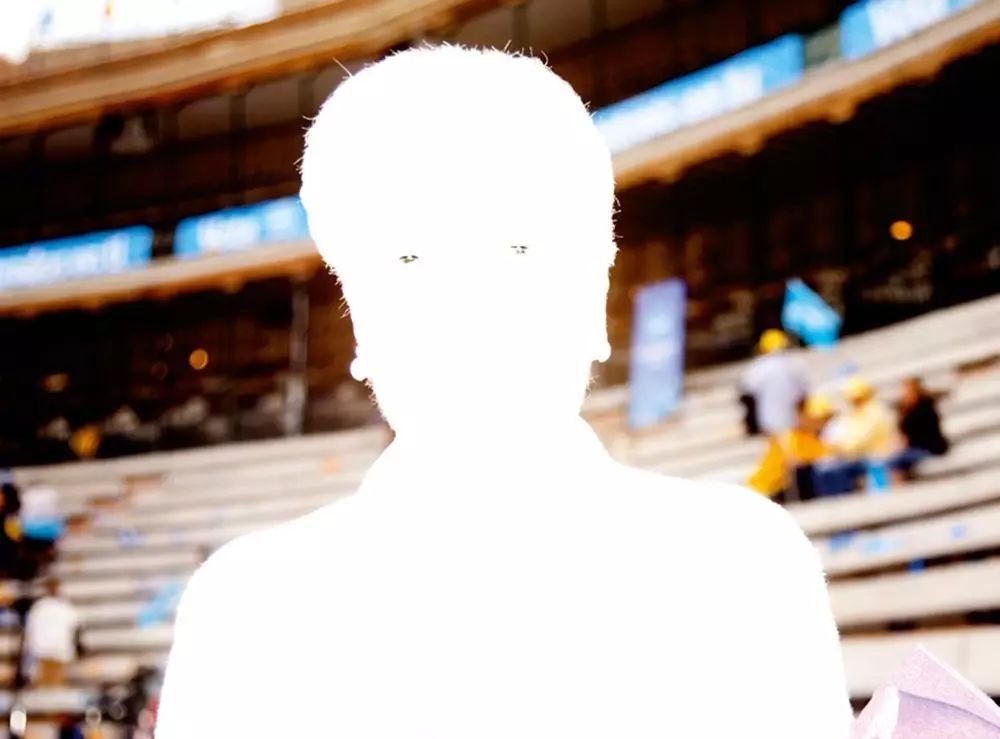
©Julián Barón
于是,在Barón这里有一个听起来有趣的尝试就是,他作为摄影师企图想要通过一个技术性策略来消解掉这些形象,这便预示了一次想要通过摄影语言发起攻击的可能性,是的,尽管“用摄影语言攻击政治”听起来颇具唐吉坷德式的色彩,而反过来讲,一种政治观点或者一次政治活动通过图像化以后进行传播,又何尝不是一次借着摄影机的干预呢?
对于无头肖像的拍摄,在Barón的实施策略中似乎同样意味着,一幅脱离环境的无头肖像实际上很难名副其实,因为平面静止的图像本身已经极具多义性,再加之当形象消失,面对图像的指涉更加让人无从谈起了。

©Julián Barón
如果时间向前推,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早观看到的无头照片是张照堂在1962年于板桥拍下的,背景是空荡的水面和远山,男人的身体放浪形骸占据前景,并颈部与水面和远山的交界处持平。而阅读这张照片既没有“系列其他”作为参考,也没有阐述话语进行考究,只能将时间拉回五六十年前的社会背景和创作者的状况进行判断。1960年的台湾正是处于政治高压和极度苦闷的年代,19岁的张照堂则活跃于地下先锋运动同时进行摄影创作,以抵抗低迷和紧张的社会关系以及官方设定的沙龙美学。那么,如此看来,即使对这张照片进行一种脱离神话色彩的描述,我们仍然能够大概察觉到他所要展示的那种具有疏离感的气氛,以及规避当下主流的预设。至于说,无头的形象倘若变成了一张回望远山的背影,作为调侃,我真的很难不把他同一种乡愁式的情结脱离开来。那么,在这其中,似乎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反差,即是尽管剔除面部信息(或头颅)像是一种阐释的解放,但在这张照片里却因为这个剔除的动作显得愈发坚定了,坚定地将抵抗以声嘶力竭的方式描述出来。

©张照堂
这是两个年代下通过无头肖像的拍摄来各自达成个人对某种政治状况抵制的方式,这也同时意味着,一定情况下(无头)肖像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身份发生关系的例子。
而无头肖像的本质则意味着一种“形象的消解”,轮廓化和模糊化变成了一种粉碎性的破坏运动。那么,谈及形象的祛魅,一向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概念艺术运动中心人物的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在80年代开始使用几何状的色块将那些电影剧照和新闻照片里的主体人物(的脸)进行涂抹,则同样是一个消除神话的动作,是的,在这个究竟是消除还是强调都难以区分的动作下,来将人们对于照片以及其联动的照片背后的注意力重新分配。

© John Baldessari

© John Baldessari
对于肖像轮廓化和模糊化的处理,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在绘画中的案例。时间再向前追溯到16世纪,有一位名为乌戈·达·卡皮(Ugo Da Carpi)的画家于1525年所做的《维若妮卡置身在圣皮耶尔与圣保罗之间(Saint Veronica between Saints Peter and Paul)》的画作尤其有趣,到并非是绘画的技艺与风格有多么的出挑,而是因为历史上众多描绘与“维若妮卡(veronica)”有关的绘画中,画家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法或处理方式,都会清晰地描绘出维若妮卡所持的裹尸布上的基督的脸,而Ugo却因为笨拙而粗糙的手法,让画中的维若妮卡所展示的完全不像是一张基督的肖像,而是凹陷在一个拜占庭式的图案中的一张模糊不清的脸。那么,正是这样一张轮廓化、模糊化了的脸所传递出的作者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无论它是否是基督的脸,人们所接受这样处理的恰当解释都像是,想保留一个圣物的“死气沉沉的”外表,而不想为受难的基督画一张活生生和更有“人情味的”脸。

Ugo Da Carpi, 维若妮卡置身在圣皮耶尔与圣保罗之间, 1525年

Albrecht Dürer, 维若妮卡置身在圣皮耶尔与圣保罗之间, 木刻, 1510年

Parmigianino, 维若妮卡置身在圣皮耶尔与圣保罗之间, 1524年
如此,以回溯的方式视检过往人们使用“无头肖像”的意图,尽管以现在的目光看来,当时的处理方式显得有些简单,但在当时的时期和环境下,我们是可以察觉到使用“消解形象”这一做法的理由的,而出于不同立场的考虑以及不同样本的选用则让其产生不同的效果以及不同指向的差异性。
而再次回归现在,在这种流行下(甚至说像是复古?),我愈发地察觉它更多地是被毫无理由地塑造成一幅绝对诗意的、充满浪漫的、不可解释的图像。那么,接下来要谈论的事情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Sarker Protick
我曾不止一次两次在不同摄影师那里看到对于这类照片,所使用的话语是简述为“关照短暂存在的或意想不到的闪光状态”这样偏诗性化的描述。但事实上,这样的描述不亚于一幅为了展示文字却无法清晰辨认文字的图像,或者一场为了塑造形象却因为演技拙劣而毁掉的表演。而当内在逻辑(或者说动机)变成了好似摄影师武器库中的一件常规武器时,这也让本应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指向降格为了一种在诗意与政治中双重不适的摄影图式。
尤其是当它已经变得如此盛行时,当我再看到这样一张无头肖像时,我该拿什么样的心情面对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