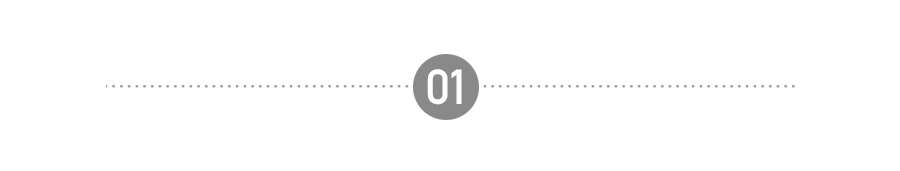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城市与创作
郑兴出道七年,发了三张专辑。作为创作歌手,他拥有天然的幸运:词曲氛围统一,音乐形象完整。三张专辑,三段故事,第一张《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2017)描绘自己在台湾政治大学的读研生活,第二张《眼泪博物馆》(2020)讲述进入音乐行业三年的所思所感,第三张《盆地》(2023)记录了因新冠疫情停滞的生活和重启的音乐路。
他至少与四个城市产生过深厚而紧密的联结:生于扬州,本科就读于北京,研究生阶段去了台北,现在定居成都。他的音乐在与城市的相处和碰撞中生发。
高中时,他在扬州写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城南》;台北的冬天,他在温热的气候里遥望北京,写出《听说北京下雪了》;定居成都后的某个春夜,他被暴雨吵醒,写下《盆地》——歌词第一句却是台北:“午夜这场瓢泼的大雨让我想起了台北,从车站到清晨的天台一样都有人喝醉。”
《盆地》制作阶段,曲目不断更换,最终留下的只有开场曲《麻雀飞去哪里》和结束曲《抵达之谜》,仿佛一开始就定下了这张专辑的主题:飘泊无处不在,未来悬而未决。
“我在扬州、台北、北京和成都都有一种疏离。在异乡读书,我是一个外来者。可是回到家乡,一起上学的同伴们都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再聚到一起也知道彼此不在一个圈子里。感觉自己有点边缘,在故乡和异乡都没有归属感时,无根的、没有确定性的感觉会非常强烈,有点恐惧,也有点迷茫,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流瓶。漂泊感背后的核心关键字其实是归属感。”郑兴说。
这些生活中的错位拉扯出心无定所的漂泊,成为他创作的一大母题。《盆地》里,他真的把走在天桥下的人比作漂流瓶,写他们“无处停摆,落入人海,化作一个谜”。
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交流无法当面进行,郑兴准备春季巡回演出时,新组了乐手班底。他白天搭高铁到南京,傍晚坐车回扬州,看似过着稳定规律的生活,但乐队的磨合、音乐的编排、公司人事的变动……交杂出复杂的情绪。南京玄武湖边的夕阳洒落,他写下《日落玄武湖》:“我不知道这一卡车的难题如何解开……这湖面的夕阳是否真的存在……绝望的人也搭上了最晚的一班列车……”这首歌收入了专辑《盆地》中,成为12首歌的歌名里唯一出现的地名。“原本他们很想换歌名,但是我想留住它,因为这是在玄武湖发生的故事。我任性地保留了。”
2022年春天,在扬州待了两年多的郑兴想换个城市生活,在成都和广州之间犹豫过后选择了前者。定居后,他发现春天的成都夜里总是下雨,但早上一定会停。一次打车时,司机告诉他,这是因为成都平原在盆地里,是正常的地理现象。他移情台北——同样潮湿、多雨,同样地处盆地,又想到那三年的生活,“两个地方完全不相干,但我刚好在这两个城市都生活过,通过这件事发现两个城市之间一种很个人的连接。”郑兴说,“盆地也象征着大家三年经历的停顿与空白,像生命的一块盆地、低谷。现在生活回到原本的状态,但三年留下的痕迹还是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他写下了歌曲《盆地》。这首歌也成为专辑的名字。
《抵达之谜》里,郑兴给出了对漂泊生活追问的答案:别回头望,不要慌张。“具体终点在哪里不重要,重点是挖掘内心的过程。”郑兴说。

▲2024年10月13日,郑兴在深圳演唱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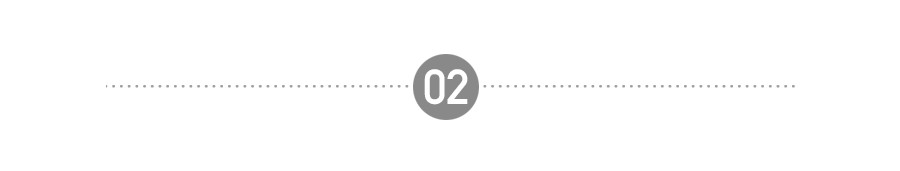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大陆歌手撩起台湾歌迷的乡愁”
2024年10月,我在广州白云机场接到郑兴,广州是他新一轮巡演的第一站。坐车去市区,机场大道往南开,车窗外太阳西沉,阳光透过玻璃落在郑兴脸上,他的眼睛忽明忽暗。“那时搭公车,行驶在台北桥上,就能看到这样的日落。”他第一张专辑中的《开往三重的慢车》就这么写出来,从木栅到三重,跨越了大半个城市,他一路看景,歌里余晖斑驳。
郑兴身上有浓烈的台湾痕迹。不只是他仿佛原生的台湾腔、平缓软糯的语调。他生于1992年,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童年里港台磁带、唱片堆积。高中时期,他被音乐人陈小霞的专辑《哈雷妈妈》吸引,作为《十年》《约定》《他不爱我》等知名歌曲的创作者,陈小霞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占有一席之地。“我非常喜欢,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作品的旋律里仍然有小霞老师的影子。”郑兴说。
大学期间,他作为交换生到台北学习了半年,学习之余环岛游,到期了回北京意兴阑珊,“不过瘾。”毕业时,他成功申请台湾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政大”)的研究所,成为第四批陆生赴台攻读研究生。
当“体验”变为“生活”,繁重的课业压力迎面而来。本科阶段,实操是郑兴的课程重点,他奔着学习“影像创作”进入研究生阶段,但政大更注重理论教学,第一学期他一度不适应。台北时常下雨,总是潮湿,与他的心情暗合。
他报名参加了政大的传统音乐比赛“金旋奖”——金旋奖由政大学生筹办、面向全台湾高校学生开放报名,是台湾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学生歌唱比赛,张雨生、陈绮贞、苏打绿……许多华语流行乐坛至今闪耀的名字都曾在这个比赛中出现——从这里开始,音乐渐渐成为他情绪的出口。
研究生二年级时,郑兴参加了在花莲举办的“东海岸音乐创作营”,由李欣芸、袁惟仁、陈建骐等知名音乐人担任讲师,他们弹吉他、写歌,与当地原住民交流音乐。原住民的音乐表达给郑兴带来非常大的触动,“我们学乐理,有一个理论体系。但音乐好像刻在他们DNA里,给他们几个音,靠直觉就能唱出来。处在那样的环境里,自己也会受到感染。”
他望着太平洋,身后是花莲的山,脚下是坚实的土地。一群人和原住民唱歌跳舞,把身体打开。“享受一种纯粹的快乐,作为人的很多框架都不再有意义。”郑兴是创作营里唯一一名大陆来的年轻人,大家都对他很好奇,最后成为了朋友。
创作营的最后一天有一场演出,学员们依次呈现这期间创作的作品。郑兴的作品是《爱人》,最后一句歌词这样写:“不是说时间会抚平所有的伤痕?可为何海峡不肯把爱还给我们?”
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多出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北投的清晨、淡水的黄昏,风吹过罗斯福路,夕阳余晖落向台北桥,花莲陆地伸向太平洋,海浪在静静翻滚。
临近毕业,他决定出一张音乐专辑作为毕业设计作品,即第一张专辑《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2018年,这张专辑入围第29届台湾金曲奖“年度专辑”等两项大奖,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提名了“最佳新人”,一举被推到了更广泛的听众面前。台湾一个电视节目采访他后形容,“来自大陆的歌手郑兴总能撩起台湾歌迷的乡愁。”
专辑筹备过程中,郑兴举办了一场“都市灵光快闪”音乐会,他租下从台北松山至宜兰列车的其中一节车厢:高铁上的乘客总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如果同一节车厢的人可以专注同一件事,那应该是不错的经历。”音乐会当天,郑兴坐在两排观众席间弹唱,他让观众写下想去的地方和想对旅伴说的话,中途一同分享。他将音乐会的前后过程拍摄成纪录片,作为毕业设计的一部分。
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作品《火车》给了郑兴很大的支持与动力,诗里写: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2024年10月12日,郑兴在广州演唱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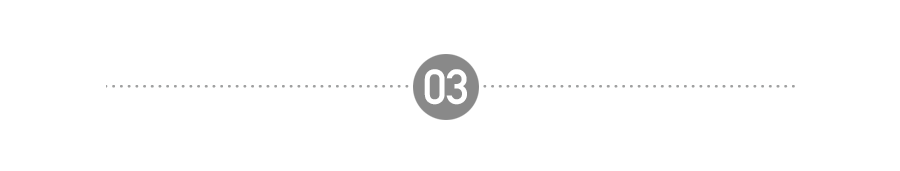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对话郑兴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很多歌词里都有雨,为什么?
郑兴:除了雨,我的歌词里也有很多气象、地理相关的意象,比如雪、海、盆地、高山。古代没有那么多的科技帮助人们去探索这个世界,人靠丰富的想象力,出现了水神、河神、山神……继而通过想象出现了很多故事,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当不从理科思维的角度去看世界,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会变得非常浪漫。
最早因为政大在指南山旁边,很容易下雨。我对这个事情就有很多的想法。我本来就是一个对于气象、气候很感兴趣的人,地理跟人文结合在一起,我就非常喜欢。我对于气候、空间相对更敏感、敏锐,是我创作过程中比较容易汲取到的养分,是我很多创作最早的动机和土壤。
这是我创作的一个惯性,我以前很喜欢画面感,喜欢通过镜头来描述一个故事,借景抒情。可能和我学影像有关。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想表达人的情感。
我最近想要尝试突破一下这样的思维,更直接一点把心里想讲的话讲出来,而不是通过写罗斯福路、写玄武湖表达情绪。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打开,更加勇敢去面对我想讲的东西?突破惯性很难。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歌曲《过于喧嚣的孤独》《抵达之谜》《雨季不再来》都是书名。你的创作有多大程度和你的阅读有关?
郑兴:我平时看的很杂,小说、散文都会看。最近在看黄灿然的诗。《过于喧嚣的孤独》是看了那本书,好喜欢这个标题,以此写了那首歌。赫拉巴尔那本书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能感受到他的笔触很温柔,他描绘的那种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一个回收废纸的主人公,透过他的眼睛去看那些以前的人们留下来的很宝贵的东西,这样的阅读感受很触动我,虽然那首歌跟这个书的内容没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举重若轻地描写人类的孤独很精彩。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歌听起来不会有特别昂扬、开心的情绪,有时会低落,甚至心情潮湿。
郑兴:心情好的时候好像不会写歌。比如我现在心情就很好,因为明天要演出了。这是我这次巡回的第一场,上一次在广州演出已经是三年前了,我迫不及待想让大家看到我这三年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