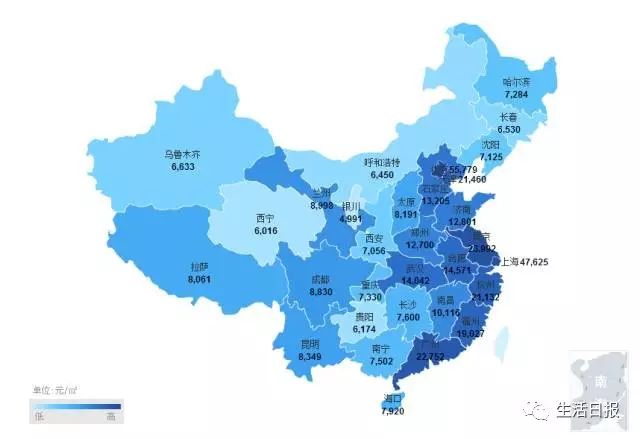正文
01
“好大的梦想”里的超我
一个共产党地下特工,在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年后,出狱了,那天,她来到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忽然痛哭流涕,她颤抖着说“这里就是新中国,我和我丈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看到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她的丈夫早已经牺牲在狱中。
这一幕为我们脑补了无数革命先烈缺失的情感释放,这个场景里,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自我“救赎”,因为有了这光芒灿烂的梦想时刻,二十年暗夜里的忍耐,直面人性的猜疑背叛,极端环境里缺失的爱情,时间,自由……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升华。
这个救赎的意义,对她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自我肯定。
超我人格的实现,带来巨大的能量。有如醉人的酒精,一朝抹去了无法容忍的生命灰暗。
的确最艰难的革命,有时候就是靠超我的偏执完成的。
这里指所有的革命,包括革自己命。
就像我的朋友创业者S,出生于一个东部的小县城,多年来靠自己的打拼,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总,在首都安家落户,享受最好的资源,现在又在忙着把老婆儿子送出国外学习,实现从国内到国际公民的跨越。二十年如一日,他每天8点到办公室,11点走,每个周末不是在谈生意就是在出差,虽然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出十岁不止,但他奋勇前行着。正是一个超我的梦想,激励着他前行,从小城走到大城,从中国要走到外国……
“一个人”和“一个好大好大的未来”,选择了这样的局面,无疑是把今天献给了一个梦想中的远方。
这里有牺牲,有生死本能,更有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迸发出来的反抗力,促成的超人梦想能量。
02
“梦想”里的模糊地带
好像是为了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要用尽所有的精神能量去专注于一个东西,催开这朵非现实主义的花。
一个人、和好大好大的梦想之间,有的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我想不想要,要不要付出这么多代价”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定义叫“价值观”,甚至是信仰。
一个人如果有健全的自我和本我功能,又有超我的加持,是真正勇敢的自我实现者。然而,
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加检视就知道,很多人执着于一个好大好大的梦想,则来自自我功能不足的表现。
比如很多时候,一个好大好大的梦想,你也不知道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在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中,文工团军人刘峰是个雷锋式的标兵好人,他也把成为圣人的理想放在自己身上,延迟了一切自我的满足。在爱上一个姑娘后,本我的欲望终于冲破了阻拦跑了出来,他陷入精神危机,并深陷由此带来的人际危机和命运转折。
严歌苓说,“
那时候我们还缺乏一种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
”她指出刘峰为代表的那群年轻人正是带着一种青春的冲动,常常觉得自己高大不了,所以要靠着一个庞大的理想来拔高自己,靠着借来的光芒来自足。
这是青春的局限。就像当年每个80后都想当超级女声、超级男声,如今每个90后都想要当网红、参与互联网创业一样,也像电影里演的,明明是残酷的战争,年轻人却把参军当作个人英雄主义的剧本来演……年轻时人们寻求个人价值的时候,其实态度是随机的,内容来自当时的主流社会环境,本质都是热血。
这时候“好大的梦想”不跟我们自己的选择有关,而是跟我们对现实的不满,对自我的强烈实现追求有关,我们就这么接受了眼前最大可能的现实道路,走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亦被时代所定义。
往往最极端的“革命者”就是最强烈的自我改造者,他们出身卑微,需要超我的引领,走到更远的地方。
严歌苓所指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获得一种做人的看家本领”。这个“看家本领”,是指
对生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我价值,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只是活在浮萍一样的个人命运里和懵懂的集体无意识中
。
03
梦想要有一次精神自觉
知乎上有人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隐居的高人吗?如果有的话,看到抗战、内战、文革这样的人间乱象,他们不出来主持公道吗?
答案是不会,即使有高人,高人的评价体系建立在更长远的历史坐标上,会尊重历史能量的自我更新。换句话说,高人不会自以为是超人,就要救世,而是能判断什么时候自己有用,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不出来。高人的梦想始终是跟客观发展观相连,不是跟超我的独大和自我的局限有关。
其实,人最难的就是如高人一样,生活在此时此地,却又找到这一点在过去未来的价值坐标。
心理老师曾这样引导一个抑郁症患者从更多角度看待自己和他人,“假设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你抑郁了,你怎么知道是你病了,还是时代病了,说不定是其他人都病了,你还当作自己病了。”
游离于均值之外,不是落后,还可能是先进。
天才和疯子都会在均值之外。比如梵高这样的天才,其衡量标准应该在历史的坐标系里。
由此,看来人的自我评价里是要有永恒价值的,否则在一个主流的局限里就会很快找到自我的上限。
所以你的梦想,未必要用当今的“很大很大”来计量,而是首先要从无意识的局限里自觉、自知。
窦文涛说一开始做《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那叫一个头痛,只要镜头一打开,他就变成了朗诵式播音腔,而他做的却是一档即兴谈话节目,日后将以创造轻松自然的聊天氛围开中国电视先河。他说到自己的“痛苦”,是有好多期节目他都在学着“说人话”,能在镜头前自然而然聊天对他来说太难。他说“没想到无意识习得的模式对我的影响这么大,我的职业生涯是从重新学习如何说话开始的。”
三十岁后选择出国去读书的传记作者范海涛,成为中国口述历史专业的第一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自立”。她发现过去三十多年身边无论干什么都有人陪伴,都有人告诉你现成的如何做是对,现成答案就在那里。然而在一个多国文化下多元化的文化话语环境里,在被允许的多元自由里,她要重新开始学会选择,选择自己是谁,成为谁。
这些精神上的破壳,是对自己的无意识的意识化,你不去看到过去的刻板,就只是惯性模式的奴隶,却还自得于自己梦想的伟光正。
精神的第二次诞生,是一次选择,在这次选择中,你个人意识苏醒了,真正的梦想价值才能浮现。
04
消解和重建梦想的意义
在小说《芳华》里还有一段,文工团的女兵们多年后相见,再次说到刘峰触摸女兵的事件,这一当年引起全团轰动、改变其一生命运的事件,多年后竟让大家都没心没肺地笑了,严歌苓写“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们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好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以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对,就那种笑。“
青春硝烟散去多年后,这种事后的笑,把所有当时当刻的严肃意义,都消解了,如今只剩了旁观者的心态。
是的,人都是历史的弃儿——最终都要有一种能自我消解的态度。
只是梦想的神圣化,深陷于我们的无意识中,有时候它是我们虚荣的拐杖,有时候又只是我们合理化内心冲动的高帽子,有时候只是一种话语体系,有时候又只是一种自由生活的代名词,有时候又只是一种想要变得不一样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