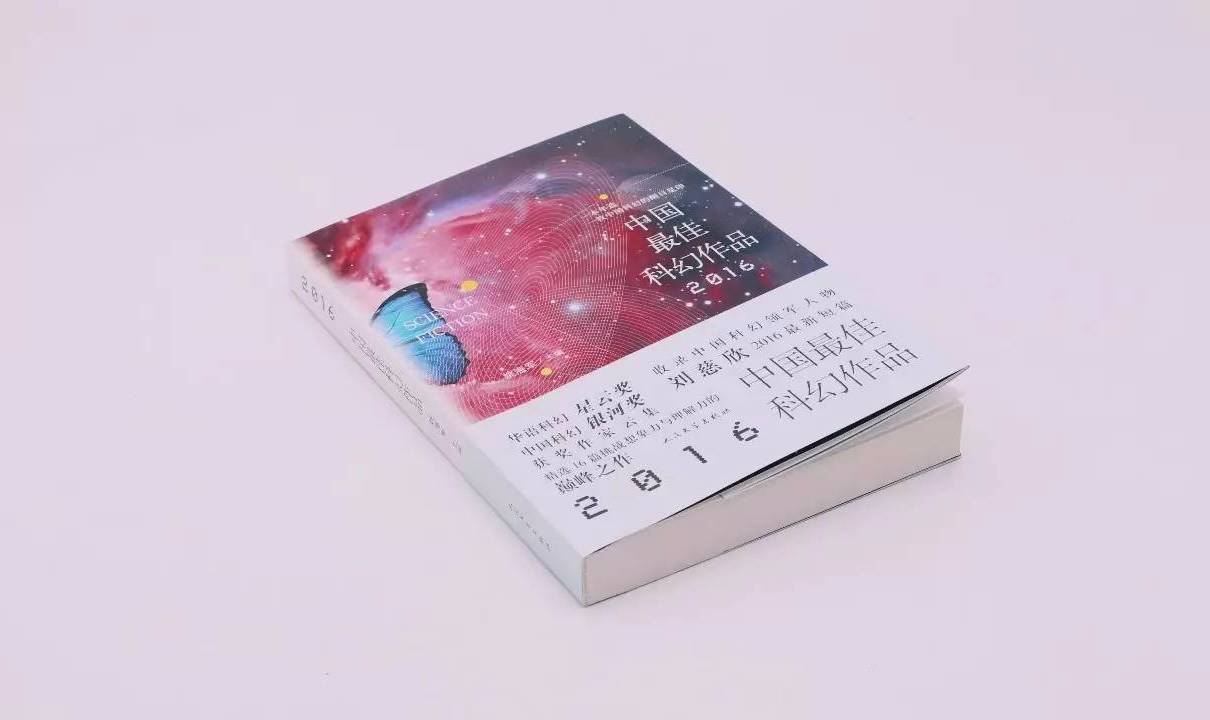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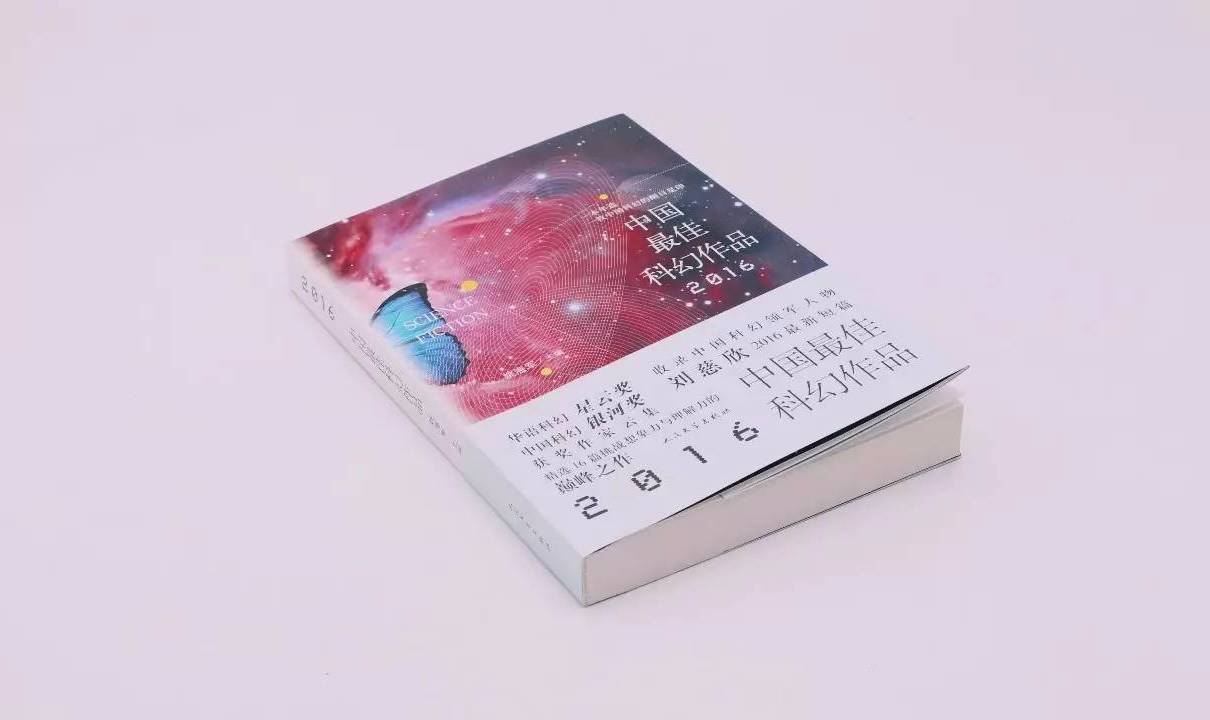
2016,科幻文学的现实与未来
文 | 姚海军
此文为《2016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序言
2016年的科幻文学,收获了更多荣光。至少有两件事将载入科幻文学史册:8月20日,郝景芳继刘慈欣之后再次捧得世界科幻文学重要奖项“雨果奖”的奖杯,世界科幻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9月8日至11日,北京举办首届“中国科幻季”,其间盛大的“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让人们对科幻文学乃至其背后的产业生出更多期待。
科幻文学自身也在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微妙改变。在某些传统方向上,以往的创作倾向与价值追求正被进一步强化;在某些未及深入探索的领域,年轻的科幻作家们展现出他们能够为科幻文学带来的更多可能;与此同时,一些微小且意义还不甚明确的突变也正在发生,略显纷杂却恰如其分地显示出科幻文学的盎然生机。无尽的可能性不仅是中国科幻当下的现实,更是未来的起点。编者期望这本年选能够对此有尽可能充分的把握与呈现。
一
核心科幻之路,对科学之美的持续追求
刘慈欣在谈到自己创作科幻小说的初衷时曾说,要“释放科学方程式中的美”。刘慈欣所讲的科学之美是一个并不单纯的概念,他的这一提法我们应该理解为表达的便利。科幻小说中所谓的科学之美,以刘慈欣最为推崇的核心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为例,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技术之美、逻辑之美,以及宇宙神秘、浩渺、和谐之美。科学之美应该是以上种种的综合。但即便如此,因为科幻小说这一名词中“科学”的地位,我们讨论时仍习惯于沿袭这一便利的提法。
刘慈欣如今已经成为科幻文学代言人式的作家,他所身体力行的充满科学之美的“核心科幻”,早已成为科幻小说自身众多发展方向中最成功的突破方向——因为其背后不仅仅有刘慈欣,还有核心科幻概念的提出者王晋康以及何夕、江波、陈梓钧等一大批优秀科幻作家,其年龄跨越老中青三代。可以说,“核心科幻”方向集中了中国科幻最精锐的力量。
2016年刘慈欣难得地发表了一篇新作,这篇名为《不能共存的节日》的超短篇虽然只有三千多字,却构思精巧、清新隽永。作品通过外星人对地球人节日的考察,揭示出人类选择外向发展与内向发展的不同结局。
刘慈欣曾多次表达对人类放弃宇宙,选择虚拟世界的忧虑。这篇小说可看作是他对这种忧虑的艺术化智趣表达。更重要的,即便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刘慈欣也表现出对浩渺宇宙的想往、对科技力量的赞美。刘慈欣借外星人之口,将宇宙中的行星形容为各种颜色的子宫,“智慧文明在其中孕育,在现实中成长,飞向太空,却在虚拟世界中熄灭,最终消失在暗夜里。”这种诗意与怅惘,恰是刘慈欣对科幻创作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的延续与丰富。
时隔五年,
何夕在2016年也发表了新短篇。这篇《浮生》与之前何夕那种在核心科幻框架内发掘故事与情感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像小说,倒更像是一篇宇宙随想录——关于上帝的底牌、生命以及宇宙的意义。
何夕的头脑里一定充满了关于这个宇宙的各种问题以及可能正确的答案。2011年他在《科幻世界》发表的两篇科学杂谈即是佐证。何夕的长篇处女作《天年》中也随处可见作者的哲思(相对于短篇,长篇作品显然容得下他一边遐想,一边推动故事)。尽管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讲,《浮生》缺少了作者以往所擅长的人物与情感冲突,但就核心科幻的建构来讲,却可算作2016年的重要收获。世界的对立统一,生命的有限无涯,在何夕笔下,呈现出物理法则统制下的诗意美。小说结尾,当布朗虫完成最后一次大规模复制,一座银色巨塔矗立在了地球原本的位置上。那是人类纪念碑。这样的经典画面,也是“核心科幻”的重要美学特征之一。
仍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梓钧,2016年发表了两篇引人关注的核心科幻《闪耀》和《海洋之歌》。两篇作品的科幻构想都相当有冲击力,本书选择收录《闪耀》,只因相较而言,这一篇更多一些科学探索的激情和我国科学家精神、生活状态的描写。
《闪耀》讲述的是一场惊心动魄太空营救:孙诗宁驾驶的木星探测飞船“波赛冬号”在木星遭遇电磁暴,迫降木卫二,以祁风扬为代表的中美两国宇航精英,必须在一百二十天内造出一艘飞船飞越八亿公里对孙诗宁实施救援。同刘慈欣一样,陈梓钧善于用冷静的语言描述震撼性的科学事件或宇宙奇观,他对神秘莫测的木星、木卫二的冰下世界、击中“波赛冬号”的木星磁暴,以及千钧一发之间数百艘接应光帆调整救援飞船航速与航向场面的描写,都是优秀核心科幻中才会出现的经典性画面,诗意而富于震撼力。陈梓钧在利用时空的错位与对比制造惊异感方面也颇得心应手。他描写那场孕育了数百年的木星磁暴偏偏在“波赛冬号”抵达木星的一瞬间暴发时这样写道:“那亚稳态金属氢的抛射物,宛如暴雨中池塘里溅起的水花,只不过每个‘水花’都有亚洲那么大……”“可能早在‘波赛冬号’的宇航员刚出生的时候,甚至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灾难(木星的这次磁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生动的比拟,让原本枯燥的画面与事件牢牢印刻在读者脑中。
腾野的《至高之眼》也是一篇想象丰富颇具赛伯朋克意味的作品,作品中所有人都生活在VR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世界。
有怀旧情结,就可以成为罗马市民;喜爱冒险,则可以居住在由魔法和巨龙守护的城堡……创造这奇迹的技术就是海洛蒙公司发明的神经中枢改造术:每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二十四小时内都要被注射一针“银剂”,那种混合了纳米机械单元和神经递质的液体,将改造新生儿大脑的神经中枢,确保所在人从出生起就能够连入模组城市。海洛蒙公司因此得以监视每一个人,摄像头就是每个人的眼睛。主人公一路探寻能够帮助人看到真实世界的“空白模组”,最亲手刺瞎了自己的双目。她看到了残阳笼罩下的暗淡世界,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只是海洛蒙公司制造的新的假象。“人们总觉得自己生活在骗局中,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与他们从前所见不同,而又合情合理的解释。”两名引导者最后的对话,引人沉思。这篇小说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则有些残酷的寓言。
仅从以上几篇作品观之,我们便可感受到以呈现科学之美为价值追求的核心科幻仍然充满朝气。
二
回归现实,探寻情感的温度
《闪耀》不仅体现了新一代科幻作家在核心科幻创作上的能力、对科学之美追求的传承,其实还让读者感受到了难得的情感温度。它是一篇平衡性很好的作品,让人想起戈德温的经典名篇《冷酷的方程式》,用冰冷的宇宙铁律,映衬爱之微光。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被认为缺乏对我们内心世界的关照,仅仅是一些奇思异想,却难以令人感动。大量阅读会帮助我们改变看法,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你会发现,科幻小说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存在,它能够更新你的很多观念,包括关于科幻小说本身。中国的科幻作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情感表达上或许会给人以略嫌笨拙的印象,但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不同的作家的各种故事中寻得他们的进步。
张冉的《冷棺时代》便是这样一篇印证进步的佳作。
《冰棺时代》取材于2015年的一则新闻:重庆出版社一位曾经审读过刘慈欣《三体》的编辑去世后冷冻了自己的大脑(这位勇敢的编辑生前对《三体》中向宇宙中发射大脑的情节印象深刻)。张冉巧妙地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演,讲述了50年后只有头脑的冷冻者醒来时母女的一场相见。母女的对话,预示了那个时代窘迫暗淡的现实。虽然经济条件有限,但为了实现母亲在可以克隆身体的时代复活的梦想,轮椅上的女儿不得不到吉隆坡那家冷冻着她丈夫和儿子的无执照人体冷冻公司,将自己和母亲一起冷冻到不确定的未来。《冰棺时代》中母亲的对话小心谨慎、情感内敛,当母亲提出再次冷冻的要求时,母亲不敢抬头看已经77岁的女儿,担心看久了忘掉27岁女儿的模样;而女儿的一句“你是我妈,做什么都应该。但这次一睡,咱们就再也见不着了。”便将读者的心拉扯、揉搓出难以止绝的血泪。科幻中也有现实主义,现实总是能够让科幻更有力量。
阿缺的《再见哆啦A梦》同样有着浓重的现实色彩。卖假酒的杨瘸子、不得志的杨方伟、柔弱的唐露,及至闯天下失败的主人公胡舟,正是他们在现实泥淖中的随波逐流与挣扎,抵消了穿越时空的虚妄感。
胡舟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作者有意借用“胡诌”的谐音,却恰巧让我们品味出作者的刻意回避。那惨淡现实映照下的朦胧爱情、《哆啦A梦》、少年愁苦,让人感伤。好在“每一个孤单的童年,都有一只哆啦A梦在守护”,世界因此才有了明亮之色与希望,尽管那希望寄生于幻想之上。
与《冰棺时代》《再见哆啦A梦》相比,
灰狐的《无数个新年》的情感色调明显温馨许多——尽管小说一开始的基调也曾让人感受到一丝冷意。该作中的现实,是传统农村生活失序、快节奏工作压力下全体生命的孤独以及亲人间心灵与真情的疏离。
主人公被困在大年三十下午到大年初一下午的时间旋涡之中,同样的一天已经重复了三百六十五次,仍不得逃脱,这样的循环像是贫乏日常生活的隐喻,而其间的单调与郁烦则更像是一场探求生活真谛的考验。因由之前的充分铺垫,小说后半部分反转显得颇有情感冲击力。当一大家人陷入争吵,主人公才发现自从有了新房就把自己的房间摆满床等待儿孙回家的奶奶坐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正在小声抽泣,“眼泪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滑下。窗外灰色的天空开始飘落雪花,就像奶奶瑟瑟发抖的满头白发。”这时主人公才想起,在这么多次的循环里,从来没有谁注意到奶奶的存在,而奶奶其实一直安静地坐着,看着这一大家子人来来往往。主人公心中积攒了三百多个新年的烦闷在此刻忽然烟消云散。当一家人将奶奶带上麻将桌,每个人都寻得了家的意义并重拾血脉亲情。
如果说《无数个新年》是通过乡镇生活透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异变,那夏笳的《铁月亮》则通过一组都市青年的生活,让我们对这样的透视有了铭心刻骨的理解。
该作品充溢着都市情调的前半部分,可视为被痛楚浸透的后半部分的铺垫。当主人公在环球中心九十二层酒吧中偶然相识的衬衫男开始讲述过往,故事才真正开始。大约十年前来到上海的衬衫男和女友小妤靠软件开发过上了事业顺遂的生活,但小妤却在自己的爱犬死后,执意开发一款能够让一个生命体验到另一个生命的痛的软件。衬衫男认为这个项目没有商业价值,背着小妤出没全国各地各种残忍现场收集将死之人的痛感,开发出一种能够人工制造多等级痛苦的玩具枪,并设计出一款以他人痛苦为乐的游戏,小妤则成功设计出她想要的手环,并号召人们戴上这种手环去参加亲身体验他人之痛的公益项目。衬衫男和小妤渐行渐远。当小妤死于车祸,衬衫男伸出手去触碰她的手环,刺骨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小说的核心就是这种痛。当我们无法去理解、体会他人之痛时,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小说结尾引用的那首二十四岁在深圳一家工厂坠楼辞世的打工者诗人许立志的诗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那种无处不在的痛。
除此以外,以情感取胜的佳作还包括钛艺讲述主人公对老管家机器人不懈挽救,凸显岁月感怀的《响》。
以上作品将科幻与现实充分融合,在展现科幻小说独特的批判现实角度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科幻小说的情感温度。
三
故事,新时代的惊奇故事
类型小说的核心要素是故事,大多数科幻小说也都是如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幻小说在美国兴盛之初,廉价的通俗杂志是科幻小说最主要的发表平台,也因此,现代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通俗文学属性。可以说,科幻新浪潮运动(1960年代)之前,讲述科技时代的惊奇故事一直是科幻作家们的主流价值追求。
对“惊奇故事”的追求,也是我国科幻的传统。自1980年代初短暂的科幻热潮始,这一发端于清末民初的传统便一直被强化。而收入本选集的大多数作品都可视为这种强化的延续。
新时代的惊奇故事与科幻史上早期的惊奇故事已有很大不同,“惊奇”内涵更为多样、立体,甚至超越了故事本身。
以犬儒小姐的《电魂》为例,在传统故事层面,是离奇曲折的情节:刺杀议员行动的失误、女主角娜塔莎的坎坷经历及其与议员夫人的感情纠葛、神秘的“电魂”计划、算无遗策的人工智能“黑猫”与其对手的智斗……
密集的情节线索与人物,交织成细密精巧的情节大网,让读者不能自拔。更进一步,惊奇还在于一系列高科技细节带来的未来感,未来世界种种观念、视觉、思想对读者的冲击。而未来世界的饱满而细致的立体化设定,其社会结构、经济与科技、国际形势等则让这种惊奇感有了丰厚、可信的现实基础。
索何夫的《神仆》相比《电魂》,虽线索和人物没有那么密集,但情节的紧张程度毫不逊色。强大的银河邦联分舰队片刻之间被杀得落花流水,一小队幸存者被强制引导逃到早已成为传说的地球,随即却被凶残万分的智能微型绞肉机几乎屠杀殆尽,而最终的两位幸运儿终于搞清了人类文明起源地太阳系所发生的一切。
整个故事不仅悬念丛生,未来感和惊奇感也颇为浓重:几乎将整体太阳系内行星笼罩其中的戴森球、星际时代人类的基因漂变、地球人为自己设计的算法无限却智能受限的守护系统……凡此种种,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索何夫习惯于让自己的科幻故事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样貌,而犬儒小姐希望透过故事勾画自己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但他们却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知识储备极为丰富。这使得他们在创作科幻故事的时候从容自在,从不被缺乏“建材”所困扰,宏大的科幻构思和科技细节描写信手拈来,娴熟自如。
凌晨的《404见龙在天》通过一件带有奇幻色彩的新闻事件,展现了都市媒体的微妙生态。围绕城市里出现了龙,媒体间相互攻防,一众新闻记者的生活也得以生动再现。
结尾的点睛之笔,“它展现给公众看的实体,只是公众希望看到的样子”,让这则都市新传奇也展现出了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不要以为有龙出没就不是科幻小说,作者对量子龙的解释其实已经改变了龙的奇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