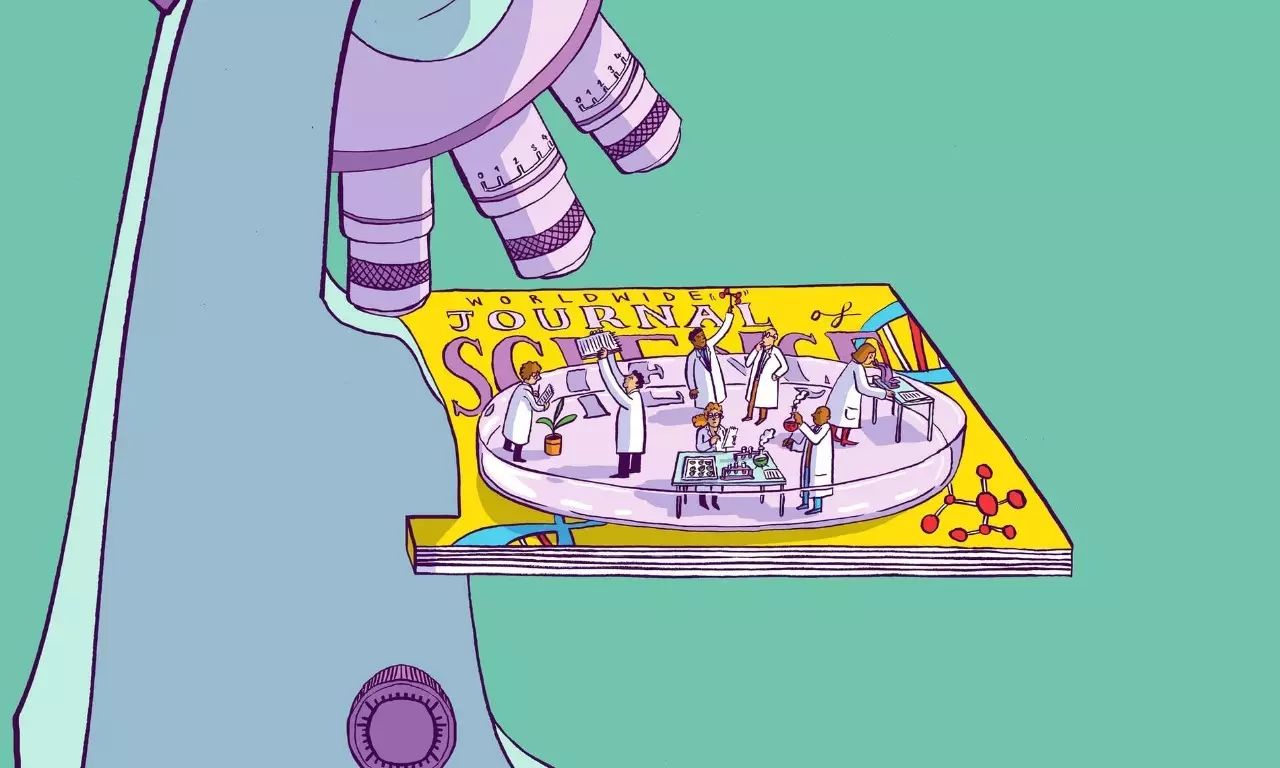
制图:Dom McKenzie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很难找到像学术出版一样匪夷所思的行业:无数科研人员为之免费供稿、审稿,却还要花钱看论文;来自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没有让科研人员成为高收入群体,却给出版商带来胜过苹果、谷歌的收益率;订阅费用压得预算喘不过气,高校却不敢不买;同类期刊多如牛毛看似竞争激烈,收费却稳升不降。
推动世界进步的科研人员,为何会“沦落”到无偿为学术期刊打工的地步?
作者 Stephen Buranyi(the Guardian)
翻译 费尔顿
审校 金庄维 张士超
2011年,伦敦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级投资分析师 Claudio Aspesi 打了个赌,他预测:全球最暴利产业的领头巨鳄将面临破产困境。他说的是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一家超大型跨国出版公司,年收益超60亿英磅,备受投资者青睐。它是少数几家在互联网时代成功转型的出版机构,最新一期公司财报显示,它们下一年的收益还将增长。然而,Aspesi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爱思唯尔对自家的前景预测,以及其他几份主要的财务分析都是错的。
爱思唯尔的核心业务是学术出版,以周刊或月刊的形式为科学家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尽管这些刊物的受众极为有限,但学术出版仍是单大生意。爱思唯尔每年的全球收入总和超190亿英镑,收益水平介于唱片业与电影业之间,但收益率更高。爱思唯尔科学出版部2010年的总收入为20亿英镑,净收入七亿两千四百万英镑—— 净利率高达36%,远超苹果、谷歌和亚马逊。
然而,爱思唯尔的商业模式着实令人困惑。对传统出版机构而言(以杂志为例),首先需要支出多项成本:给作者的稿费,给编辑的组稿、加工、校对费用,以及配送给订阅用户与零售商的物流成本。因此,传统出版机构所承受的总成本十分高昂,即使是经营状况较好的杂志,净利率也只在12%—15%左右。
学术出版在挣钱方式上大同小异,只是专营这一方向的出版机构会尽力压减成本。科学家根据各自的研究计划产出成果(这些计划主要由政府资助),然后再免费提供给出版机构。出版机构会聘用编辑评估论文质量、润色稿件文字。学术论文还需要经过同行评议,即检验科学性、评估实验等,而这一部分工作由众多一线科学家自愿从事。成稿后,出版机构便将期刊重新卖回给由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图书馆,最终读者主要还是最初投稿给期刊的科研工作者。
这就好比《纽约客》或《经济学人》要求记者免费撰写文章、互相编辑,还让政府出钱来买。非科研界人士听到这种运作过程时,大多都会觉得难以置信。2004年,英国议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在相关的产业报告中尖刻地指出:(学术出版的机制就是)“在一个传统的市场中,供应商要为自己提供的商品买单。”2005年,荷兰银行在报告中将其描述为“匪夷所思的”“三重收费”系统:“国家资助大多数研究,还要为评估研究质量的工作支付劳务费用,最后还得购买最终出版的期刊。”
科学家都清楚自己所处的被压榨地位。2003年,伯克利大学的生物学家 Michael Eisen 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厉声批评:学术出版“既不合理,也很冗余”;他认为这是一桩“应该公之于众的丑闻”。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 Adrian Sutton 告诉我:科学家都是“出版机构的奴隶。试问,还有哪个产业会从自己的用户那儿收集原始材料,然后让同一批用户监控这些材料的品质,最后再以高到不合理的价格将它们重新卖给这批用户”?
而 RELX 集团(爱思唯尔在2015年后的官方名称)的一位代表告诉我,学术出版机构“会根据研究团队所需来提供相应的服务,而这些需求对科学家本人而言,既无法做到也无力顾及。这一部分便由出版机构代劳,然后相应地收取合理的费用”。
很多科学家认为,出版业过度地干涉了他们的科研方向,长此以往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期刊喜爱新颖和吸引人眼球的科研成果(毕竟,足够的订阅数量才能保证出版商更好地运转),而科学家很清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发表,并会据此调整投稿策略。这可以保证稳定的论文产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意味着科学家可能会对自己的研究方向缺乏清晰的整体认识。期刊不会发表相关研究的失败案例,因此研究人员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死胡同,哪怕之前早已有同行误入同样的歧途。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几乎有一半的临床试验从未发表在任一期刊上。
有不少批评指出,期刊系统实则阻碍了科学进步。2008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由美国政府资助并主导的机构)的 Neal Young 博士警告道:鉴于科学创新对于社会的重要价值,“应该从道德层面重新考量科研数据的评估与传播”。
身为投资分析人的 Aspesi 听取了25位知名科学家与活动人士的看法,他渐渐相信,由爱思唯尔主导的学术出版业即将改变风向。越来越多的学术图书馆(大学里订阅期刊的机构)威胁道,他们的采购经费快被连年上涨的定价压榨殆尽,要是爱思唯尔不降低价格,他们就取消价值百万英镑的打包订购。诸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这样的国家机构,近来推出了新的备选方案,即通过免费的线上期刊发表研究成果。Aspesi 认为,政府可能介入这场产业转型,并保证向所有人免费开放公费资助的研究项目。爱思唯尔以及同行竞争者可能会遭到这场风暴的两面夹击:下有用户反抗,上有政府逼压。
2011年3月,Aspesi 发布报告,鼓励他的客户抛售爱思唯尔的股票。几个月后,在爱思唯尔管理层与投资方的电话会议中,Aspesi 就图书馆用户的流失风险向爱思唯尔的首席执行官 Erik Engstrom 施压。Aspesi 质问道:如果你的用户都如此沮丧,那是否该问问自己,“这家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而 Engstrom 回避了这一发问。接下去的两周内,爱思唯尔的股票蹉跌超20%,损失达10亿英镑。Aspesi 触碰到了本质的结构性问题,他相信,爱思唯尔还可以撑过未来5年,但整体事态已经在朝着他预测的方向发展。
可是第二年,绝大多数图书馆还是让步了,他们与爱思唯尔重新签订了合约;政府也没能顺利推出可替代的科研成果传播机制。2012—2013年,爱思唯尔的利润率超过40%。第三年,Aspesi收回抛售爱思唯尔股票的建议。“他和我们走得太近了,所以也变得很愤怒,”英国学术图书馆的馆长 David Prosser 分析道,他本人是倡导论文出版业改革的有力之声。
至此,爱思唯尔仍然屹立不倒。

制图:Dom McKenzie
Aspesi 并不是第一个误判学术出版业行将触顶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家利益导向的寡头企业,竟可以在规制严格、由政府资助的产业中长期兴盛,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但是,学术出版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入了科研领域的方方面面。现在的科学家都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取决于论文发表,学术地位也尤其仰赖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20世纪初,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常常埋头于漫长而没有方向的探索,可这显然已不适用于当下。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基因测序之父 Fred Sanger 可能永远找不到教职,因为他自1958年至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近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
即使是那些热切期盼改革的科学家,大多也没有了解到这一体制的根源:随着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大亨如何从科学家手中抢过出版大旗,并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不断扩张?没有人比 Robert Maxwell 更敏锐、更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他使科学期刊变身为无与伦比的赚钱机器,并凭此源源不断地夯实财力,逐步提高自己在英国的社会地位。Maxwell 之后还当选为议员,成为可以与 Rupert Murdoch 抗衡的出版业大亨,后者可是英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不过,Maxwell 的真实影响力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巨大。也许听起来难以相信,但坦白说,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如 Maxwell 那样深远影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1946年,年仅23岁的 Robert Maxwell 就职柏林,当时已享有不小的名气。虽然他出生自捷克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但二战期间却以欧洲流亡者的身份为英国军队效力,并赢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与英国公民身份。战后,他赴柏林出任情报官员,轮番利用自己掌握的9种语言审问囚犯。Maxwell 高大、傲慢,丝毫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功。一位旧相识这样回忆道,Maxwell 曾袒露他内心最深的渴望:“成为百万富翁”。
就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筹备了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的项目,这恰恰为 Maxwell 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当时,从发现青霉素的 Alexander Fleming 到物理学家 Charles Galton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英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英国的科研水平世界一流,可是对应的学术出版却相当疲软。当时的学术出版机构大多低效且入不敷出,常用低劣的纸张印刷期刊,内容也远远滞后于研究前沿。英国化学学会积压的稿件数量足够连续发表一个月,可还是要等皇家学会的拨款到位才能开印。
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让英国老牌出版社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现属于爱思唯尔)与声望极高的德国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结盟,为的就是依靠后者的专业性。巴特沃斯可以借机学习期刊发行的盈利模式,英国科学界也可以更快地发表成果。Maxwell 帮助施普林格将学术论文发往英国,并在从中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巴特沃斯出版社的主管层都是前英国情报人员,他们聘用年轻的 Maxwell 打理公司,让 Paul Roshaud 担任编辑(Roshaud 之前是一名冶金学家,也当过间谍,战时主要负责将纳粹的核武器信息经由法国和荷兰传回英国)。
他们可谓始于最好的时机。科学进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阶段;科研也从富裕绅士闲散、业余的知识追求,变身为备受尊敬的严肃职业。战后,科学更成了进步的代名词。美国工程师、曼哈顿计划的项目主管 Vannevar Bush 在1945年给杜鲁门总统的述职报告中写道:“科学插上了翅膀。它应该走入人类舞台的中央,因为我们未来的希望都蕴含其中。”二战结束后,政府首次成为科研领域的主要资助者,不仅关注军事科研,还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并加大了对大学教育系统的投入与开发。
1951年,巴特沃斯出版社一度考虑放弃结盟计划,就在那一当口,Maxwell 为巴特沃斯和施普林格分别注入了价值13 000英镑的股份,自己也凭此争得了公司的控制权。Rosbaud 继续担任科学总编,并将结盟后的新出版社命名为帕加马出版社(Pergamon)。这一灵感来源于一枚希腊古城帕加马的硬币,其上刻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侧面头像。硬币图案的简笔画之后也成了帕加马出版社的标志,代表知识与金钱。
在充斥着金钱与乐观的时代,Rosbaud 率先构思出带领帕加马走向成功的运作方式。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壮大,他灵敏地捕捉到,急需出版新的期刊来报道新领域的研究。传统期刊出版机构臃肿、低效,还常常因为学术界内部关于学科边界的争论而畏手畏脚。Rosbaud 则不受此约束。他只需找准并说服某一领域的顶级学者,该领域亟需一份新期刊来更好地展示科研成果;接下去只要任命这位学者为该期刊的主编就大功告成了。之后,帕加马便将新期刊开放给大学图书馆征订,这也意味着,他们瞬间就到手了大把的政府经费。
Maxwell 很快上手。1955年,他与 Rosbaud 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核能源安全使用大会。Maxwell 在会场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频繁出入研讨会与官方聚会,期间不断邀请科学家在帕加马发表会议论文,同时与他们签订独家合约,旨在为各路期刊招募专业编辑。其他出版机构震惊于 Maxwell 草莽的做事方式,北荷兰出版集团(North Holland Publishing,现属于爱思唯尔)的 Daan Frank 后来抱怨道:Maxwell 挖角科学家的做法“十分奸诈”,他甚至不看具体内容。
据传,Rosbaud 也常因 Maxwell 的利欲而心生反感。与低调的科学家不同,Maxwell 爱穿昂贵的西服,喜欢梳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说话略带捷克口音,会以令人生畏的高贵语气与人交谈,声如男低音版的新闻主播。如 Maxwell 所愿,他已俨然一副大亨样。1955年,Rousbaud 告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Nevill Mott,帕加马是他最珍爱的“小羊羔”(语出《圣经》,意为最宠爱之物),而 Maxwell 则是大卫王,只等着“宰羊”卖钱。1956年,这对搭档最终还是闹翻了,Rosbaud 离开了公司。
此时的 Maxwell 已熟知 Rosbaud 开发的商业模式,他适当调整,使其完全为己所用。以往的学术会议大多从简且了无生气,可等来年的日内瓦大会开幕,Maxwell 便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小镇科隆日-贝勒里夫租了一幢大宅,在那里以美酒、雪茄和游船之旅款待来客。科学家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帕加马的前副主管 Albert Henderson 告诉我:“他总是强调,我们竞争的不是销售额,而是作者。我们常专门为给新期刊招募编辑而奔走于各类学术会议。”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顶楼露台举办过盛大派对,曾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之行作为豪礼相赠,还曾包下整条游轮、前往希腊小岛共同策划新期刊。
1959年,帕加马已经发行了40种期刊;6年后,期刊总数达到150。这让 Maxwell 在产业中遥遥领先。(1959年,帕加马的对手爱思唯尔旗下只有10种英文期刊,10年后才发行到50种。)截至1960年,Maxwell 已拥有配备私人司机的劳斯莱斯座驾,还举家从伦敦搬到牛津,并将住宅和帕加马总部设在富丽堂皇的黑丁顿山礼堂,这里也是英国出版社 Blackwell 的所在地。
如英国流变学学会这样的科学学会,早已预见了自行运营期刊的惨淡前景,他们遂以非常低廉的金额将期刊全盘托付给帕加马。在《神经化学》(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供职过的编辑 Leslie Iversen,曾受邀前往 Maxwell 的宅邸共享盛宴;他回忆道:“Maxwell 很有个人魅力,有大企业家风范。我们共进晚餐,一起品鉴上好的红酒。末了,他掏出一张几千镑的支票,权当资助学会。这样的数额远超穷困科学家的想象。”
Maxwell 一直坚持使用宏大的期刊名,他最喜欢的名称便是《国际XX期刊》。帕加马的前副主席 Peter Ashby 称这为“公关策略”。这一细节也深刻反映了,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进行国际合作、在国际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学家积聚声望的新手段,而 Maxwell 早已在其他人意识到这一名声效应之前就垄断了市场。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西方科学家埋头在航空领域奋力赶超时,竟发现 Maxwell 早在10年前就与俄罗斯科学院谈妥,牢牢掌握了英文版的独家发行权。
“他有意进驻世界各地。我去到日本,发现他让一个美国人替他在那儿打点生意。我去到印度,发现他在那儿也有人,”Ashby 惊叹道。国际市场拥有更可观的利润空间。20世纪70年代,Ronald Suleski 负责运营帕加马日本分部,他告诉我:日本科学界当时为用英文发表论文而苦恼不已,所以他们大方地允许 Maxwell 免费使用他们的研究结果。
Eiichi Kobayashi(供职于帕加马长期合作发行方Maruzen,担任总监)在庆祝帕加马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回忆了自己与 Maxwell 的交往:“我每次见他都很高兴,他总让我想起菲茨杰拉德(注:《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的话:大亨非凡人。”
学术论文逐渐成了学术界向外界系统展示研究进展的唯一途径。正如惠康基金会(世界第二大生物医学研究私人资助方)图书馆电子服务部的主管 Robert Kiley 所说:我们每年投入数百万英镑,最终换得几篇论文。这是人类最受尊重的专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美国国立卫生院的 Neal Young 分析道:“发表论文是我们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陈述。一个好想法、一次交谈或邮件交流,即便是来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除非发表,要不然这些什么都不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只要控制了科学著述的传播,你就掌控了科学。
Maxwell 的成功来源于他把握住了学术期刊的特点:理解和复制每一项研究都要耗费数年时间。当同期竞争者抱怨 Maxwell 搅乱市场时,Maxwell 已洞察到,这个市场近乎无限——创办新刊《核能》(Journal of Nuclear Energy)不会抢走 North Holland 旗下《核物理》(Nuclear Physics)的生意,因为每一篇论文包含的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发现,每一篇都不可替代。若有重磅的新期刊面世,科学家只会要求所在大学的图书馆一并订阅。所以,如果 Maxwell 发行的期刊数量是对手的3倍,那么他的收益也是对方的3倍。
唯一可能的限制是政府资助放缓,但当时还毫无迹象。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资助航天项目;20世纪70年代伊始,尼克松“向癌症宣战”;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启了自己的核项目。不论政治格局如何风起云涌,科研事业都随着政府资助而水涨船高。

1985年的Robert Maxwell。照片来源:Terry O'Neill/Hulton/Getty
帕加马创办早期被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可否允许商业利益进入本该无私无欲的学术界,而帕加马恰好处于论战中心。剑桥大学的 John Coales 在1988年庆祝帕加马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提到:他的很多朋友最初都认定,“Maxwell 是迟早要被推上绞刑架的恶棍”。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商业出版模式已得到广泛认同,出版机构也被视为推进科研发展的必要助力。帕加马加快了出版进程,设计出更新潮的装帧封面,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版图。科学家一开始还担心放弃版权的后果,可最终还是抵不过帕加马提供的合作便宜,以及公开发表所带来的荣耀,而 Maxwell 的说服力也让他们无法拒绝。科学家们好像与这头自己放进门来的狼相处甚欢。
牛津大学的生理学家 Denis Noble(他也是《生物物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的编辑)坦陈:“他是个恶霸,可我还是欣赏他。”Maxwell 有时会唤 Noble 到自己的宅邸开会,Noble 回忆道:“每次去,那里都办着派对,乐团在演奏美妙的音乐,他的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没有界限。”议事期间,Maxwell 或恫吓或诱惑 Noble 将半年刊拆分成月刊或双月刊,这也意味着,在场的某位宾客可要支付更高的订阅费用了。
不过,Maxwell 终究还是以科学家的意愿为先,科学家也很感激他充当庇护人的角色。《真空》(Vacuum)的编辑 Arthur Barrett在1988年一篇回忆出版业早期岁月的文章中表示:“我不得不承认,了解到他极具掠夺性的宏图伟志之后,我还是非常欣赏他。”这种认识是相互的。Maxwell 与知名科学家悉心交往,对他们百依百顺。Richard Coleman 曾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供职于帕加马的生产部门,他告诉我:“Maxwell 早就意识到科学家的绝对重要性,甚至会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可这逼疯了其余员工。”根据《卫报》1973年的一篇报道:当帕加马面临恶意收购的风险时,编辑们以集体离职相威胁,表达了不会为新任主管效力的强烈诉求。
Maxwell 改变了出版业,但日常的科研工作几乎没变。绝大多数科学家仍将自己的论文投稿给相应的学术期刊,Maxwell 乐意发表任何一篇(甚至所有)经他手下编辑评估、认定为足够严谨的学术论文。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机构开始介入实际的科研工作,由此,科学家的事业评定与发表论文牢牢绑定在一起,商业利益开始强烈驱动研究转向。有一本期刊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我刚工作那会儿,没人注意你在哪儿发的论文,可自1974年后,《细胞》(Cell)改变了一切,”伯克利的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Randy Schekman 这样告诉我。《细胞》(现也归爱思唯尔所有)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专门介绍分子生物学的前沿进展。该期刊由年轻的生物学家 Ben Lewin 担任编辑,他兼具热忱之心和优秀的文字能力。Lewin 偏好研究大问题的严谨长论文,相关研究通常会持续数年,从各种途径衍生出许多论文。Lewin 摆脱了期刊被动传播科学的窠臼,被他拒掉的稿件远多于最终发表的。
Lewin 使科学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显学,科学家们也会按他的思路调整研究策略。“Lewin 很聪明。他深知科学家也有虚荣渴望,所以他们都想加入优质的会员俱乐部,《细胞》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你必须得在那儿发文章,”Schekman 说道,“我也曾背负同样的压力。”他最终在《细胞》上发表了与他诺奖研究相关的论文。
在哪里发论文很快成了重中之重。很多编辑都采用了 Lewin 的组稿策略,以期复制《细胞》的成功。出版机构还引入了一项名为“影响因子”的标准,这一概念由图书管理员、语言学家 Eugene Garfield 于20世纪60年代首创,旨在计算指定期刊中已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用频率。出版机构可以据此为期刊排名,也可以借此扩大期刊在科研界的影响力,而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也更容易获得工作和资助机会。一夜之间,科学权威性的确立有了全新的标准。(Garfield 后来表示,自己创建的这一词条“像核能一样……让人喜忧参半”。)
很难说期刊编辑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科学家的前程或科学本身的发展方向。Schekman 向我转述道:“年轻人总跟我说:‘如果我不能在 CNS(即 Cell/Nature/Science,生物学界最权威的三部期刊)上发表文章,那就找不到工作。’”他认为,追求高影响因子就和银行设立分红奖励机制一样堕落。他说:“这将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
如此一来,科学成了科学家与期刊编辑共同合作的产物,前者不断追求可以令后者眼前一亮的科学发现。现在,当科学家在选择研究方案时,几乎从不会考虑以下两种:如果是重复或反驳之前的研究,那就太过平淡无奇;花费数十年的功夫搞大项目,又风险太大。科学家们通常会折衷选择:深受编辑推崇,同时可以正常产出论文的研究。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Sydney Brenner 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学者们被鼓励为迎合这些需求而开展研究。”在 Brenner 看来,这样的机制简直“堕落”。
Maxwell 深知期刊在科学界已经有了“拥立新君”的能力。他心系扩张版图,继续以敏锐的视角观察科学进展,瞄准值得开拓的新领域。英国出版集团麦克米伦(Macmillan)前首席执行官 Richard Charkin 曾于1974年供职于帕加马出版社,担任编辑一职,他回忆道:Maxwell 在一次编辑会议上挥舞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结构的一页报告,向所有人宣布:未来属于生命科学,以及其中亟待解决的诸多小问题,而每一个问题方向都足以独立成刊。“我想,那一年我们大概发行了100份不同的期刊,”Charkin 说,“我觉得,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了。”
帕加马继而向社会科学与心理学领域进军。一系列以“计算机与……”开头的期刊表明,Maxwell 已觉察到数字科技的兴起。“永无止境,”Peter Ashby 形容道,“牛津理工学院(现为牛津 Brookes 大学)开设了一个餐饮专业,有一名厨师教员。我们就去找系主任,然后联系他创建了一份新期刊,名为《国际酒店管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世纪70年代晚期,Maxwell 需要应对日益拥挤的市场。Charkin 告诉我:“那天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我们围坐在一起慨叹:‘我的天,这些期刊真能赚!’”与此同时,荷兰的爱思唯尔也开始拓展英文期刊市场,在荷兰本国的市场竞争中一举购得一系列杂志,并以每年新增35个主题的速度扩张。
正如 Maxwell 所预见的,竞争不会拉低期刊售价。1975—1985年,期刊的平均价格翻了一倍。据《纽约时报》报道,1984年《大脑研究》(Brain Research)定价为2500美元,1988年则涨到了5000美元。同年,哈佛大学图书馆因为订阅学术期刊的预算超支高达50万美元。
为期刊免费打工的科学家会时不时地质疑这条硕大利益链是否公允,但最先觉察到 Maxwell 制造市场陷阱的是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们。这些图书管理员利用大学经费订购期刊,Maxwell 也充分了解这一资金流向。他在1988年接受 Global Business 采访时表示:“不比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科学家对金钱并不敏感,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加之他们无法订阅到更便宜的替代物,所以,如 Maxwell 所言:“(我们就是)一台永动印钞机。”图书管理员只能在上千份垄断市场的期刊中挑选。现在每年会发表100多万篇论文,无论出版机构标价多高,图书管理员都不得不全部采购。
如果在商言商,那么毫无疑问,Maxwell 绝对是个成功人士。图书馆这块市场已被俘获,荒谬的是期刊已将自己定位成科学权威的守护者,所以即使有新型分享方式出现,科学家们也别想轻易甩开传统期刊。密歇根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Robert Houback 于1988年在一份行业期刊上撰文:“如果不是那么天真的话,我们早就能发现自己身处的真实位置:高坐在厚厚一摞钞票上,聪明人从四面八方而来,想办法把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1985 年,尽管科研经费十年来首次出现连年下滑,帕加马的利润率还是高达47%。
Maxwell 没有继续打理他的商业帝国。他旺盛的进取心使帕加马终获成功,可也正是这种 “进取”,让他掷下了大单华而不实、值得疑问的投资,其中包括买下牛津联和德比郡两家足球队、世界各地的电视台,以及1984年买下英国《镜报》集团(之后他在《镜报》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1991年,为了弥补即将收购《纽约日报》的资金缺口,Maxwell以4.4亿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19亿英镑)的价格将帕加马卖给了早就静待一旁的荷兰对手爱思唯尔。
帕加马的很多前员工都在不同场合与我说,当 Maxwell 决意卖给爱思唯尔时,我们就知道玩完了,因为那可是他的心头肉啊。同年晚些时候,Maxwell 身陷一连串丑闻:逐日增加的债务、可疑的账目……美国记者 Seymour Hersh 甚至爆出惊天大料:Maxwell 是以色列间谍,曾参与多起武器走私案件。1991年5月,人们在加那利岛(Canary Island)发现,Maxwell 的尸体漂浮在他的游艇附近。全世界一片哗然。第二天,《镜报》的对手、知名小报《太阳报》通过夺目的标题引发众人猜测:“他是失足摔下……还是纵身一跃?”(想必第三种解释也已呼之欲出:他是被推下去的。)
Maxwell 的去世占据英国报刊各大版面长达数月之久,人们越发怀疑 Maxwell 是自杀。因为有调查表明,Maxwell 从《镜报》的退休基金中盗取了4亿英镑以偿还债务。(1991年12月,一名西班牙验尸官判定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事故。)各路猜测此起彼伏:2003年,在 Gordon Thomas 和 Martin Dillon 两位记者合著的书中,Maxwell 被断定遭到了 Mossad 的暗杀,因为后者要掩盖自己的间谍活动。彼时,Maxwell 已逝去很久,可是他开创的产业却在后继者手中如火如荼地发展,而且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该产业赚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产生了更深远的国际影响。
如果说 Maxwell 精于扩张,那么爱思唯尔可以说是长于巩固。购得帕加马旗下400多份期刊后,爱思唯尔已拥有1000份学术期刊,成为全世界毫无争议的科学出版之最。
收购帕加马期间,麦克米伦的首席执行官 Charkin 曾这样建议爱思唯尔的首席执行官 Pierre Vinken:帕加马的生意已基本定型,爱思唯尔给出的收购价格过高了。但 Vinken 很确信自己的决策, Charkin 回忆道:“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就算你啥也不干,这些期刊能有多赚。创建新期刊的时候,你要花时间组建优秀的编辑团队,支付他们丰厚的薪水,提供丰盛的晚餐。然后你把产品推向市场,让销售人员推广征订,这个过程耗时漫长且艰难,总之你得尽可能地优化这份期刊。这就是帕加马已经做了的事。然后我们买下了它,不用做任何事,收益却源源不断地涌来,你无法相信那有多美妙。’他是对的,是我错了。”
1994年,帕加马已转入爱思唯尔旗下三年,爱思唯尔将定价提高了50%。大学怨声载道,因为订阅费用已无限逼近预算上限。根据美国《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Weekly)的报道,图书管理员将爱思唯尔比作产业内的“末日机器”,之后他们也真的首次退订了部分冷门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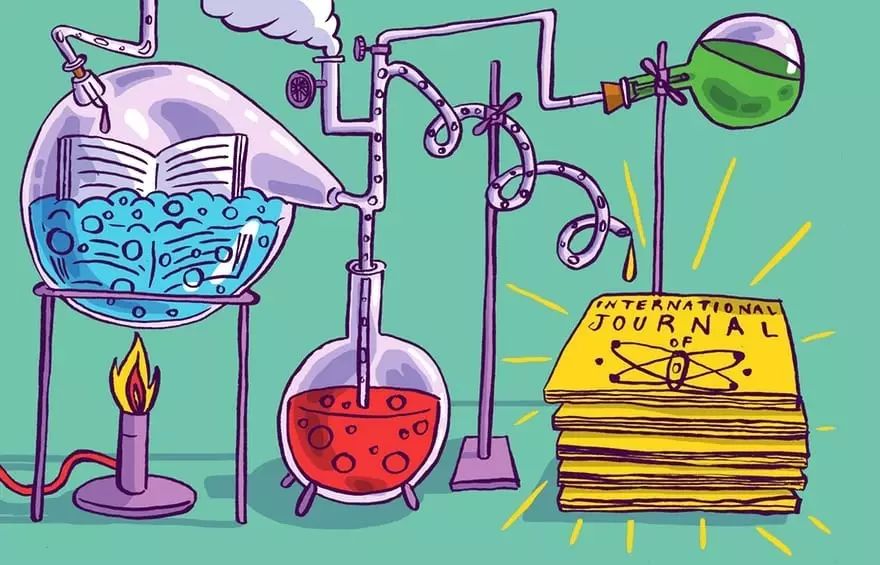
制图:Dom McKenzie
爱思唯尔那时的举措好像近乎自杀:互联网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免费的备选方案,它却惹怒了自己的用户。1995年,《福布斯》报道:科学家通过早期的网络服务器共享成果,那么爱思唯尔是否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牺牲品”?
不过,出版机构一如既往地比学术界更懂市场。
1998年,爱思唯尔推出了名为“The Big Deal”的网络计划。该计划允许用户一次性访问几百份期刊:大学每年支付订阅一整套的费用(根据一份信息请求自由报告,康奈尔大学2009年订阅费将近200万美元)任何一位学生或教授都可以在爱思唯尔官网上下载所需期刊。大学纷纷集体订购。
预测爱思唯尔营收下滑之人,大多认为科学家在尝试网上免费共享研究成果,总有一天可以替代爱思唯尔发行的期刊。可是,爱思唯尔却将 Maxwell 留下的几千份寡头期刊融合成像水库或电站一样的超大型基本资料库——这是大学机构单靠自身所无法企及的。付费,科研得以继续;拒付,那么高达四分之一的论文将隐没在黑暗中。由此可见,最大的出版机构手握无限权力,而爱思唯尔的收益也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迈向了数十亿大关。2015年,《金融时报》断言爱思唯尔是“互联网扳不倒的”。
出版机构现已紧紧缠绕在各个科研环节之中,因此单一环节的松动并不能彻底摆脱它们的影响。2015年,蒙特利尔大学的信息学家 Vincent Larivière 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显示爱思唯尔已占有24%的学术期刊市场,而 Maxwell 的昔日搭档施普林格以及同城对手 Wiley-Blackwell 分别占有12%,三者相加一下子就占去了半壁江山。(一位了解过这份报告的爱思唯尔代表告诉我,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爱思唯尔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6%。)
Randy Schekman 告诉我:尽管我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号,提醒大家关注这一产业问题,可是期刊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驱动该产业扩张的并不只是期刊收益,更关键的是它庞大的影响力,而这也正是最令科学家们沮丧的现实。
爱思唯尔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辅助科研人员的工作。一位爱思唯尔的代表注意到,去年全司合计收到150万篇投稿,最终发表42万篇;1400万名科学家选择通过爱思唯尔发表他们的成果,80万名科学家帮助爱思唯尔进行编辑和同行评议。全球策略网络的高级副主任 Alicia Wise 称:“我们使科研人员更高产、高效。这既有利于研究机构,也有利于政府等研究项目资助方。”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都如此敌视期刊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合作关系部的副主任 Tom Reller 给出的答案是:“他人的意图不由我们揣测。我们看数据说话(选择爱思唯尔的科学家数量),数据显示我们做得很好。”当我询问 Reller 如何看待针对爱思唯尔商业模式的批评声时,Reller 在邮件中回复道:“‘出版机构给科学研究附加的价值’都被这些批评者忽视了,而这种附加价值远超公共部门资助的贡献。”他认为,这才是爱思唯尔收费价值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表论文的要求的确严重影响了学术生态,可这并不是出版机构的错。当中国或墨西哥政府为高影响因子论文颁发奖励时,他们并非应了哪家出版机构的要求,而是遵从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的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既要尊重科学理想,又要协调规则主导者——出版机构的商业利益。Neal Young 承认:“我们科学家并没有深入思考这种环境,就像感觉不到水的鱼。”
21世纪初,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另一种订阅方式:开放获取。通过直接移除商业因素,开放获取有效地解决了如何平衡学术与商业的两难问题。开放获取期刊以线上模式运作,科学家们只需预付部分编辑费用,从而保证任何人都可以永久访问已发表的科研成果。尽管全世界最大的几家资助机构(如盖茨基金会和惠康基金会)提供了相关支持,最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学术论文在发表之时就免费向所有人开放。
要求免费公开是一种强烈的诉求,甚至会对现行出版机制造成巨大威胁:因为出版机构一直通过为获得学术论文设置门槛来保持巨额收益。近些年来,最激烈的异见之声发自一个饱受争议的网站:Sci-Hub。该网站堪比学术界的 Napster(在线音乐服务,以点对点形式共享 MP3),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下载论文的途径。该网站的创建者、哈萨克斯坦人 Alexandra Elbakyan 现在仍在躲藏,她在美国面临以黑客行为侵犯版权的指控,并被判处赔偿爱思唯尔1500万美元(最高上限)。
Elbakyan 是名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她在邮件中对我说:“科学应该属于科学家,而非出版商。”在一封给法庭的信件中,她援引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人人都有权“共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无论 Sci-Hub 何去何从,已有的质疑批评之声都已剧烈撼动了现行的论文发表机制。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押学术出版机构输是很有风险的。毕竟,Maxwell 早在1988年就已预言:未来只会留下几家巨型寡头出版公司,他们能以只手遮天之力,继续在数字时代开拓市场,那时已没有印刷成本,几乎可以说是“纯收益”产业。
这听起来像极了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jun/27/profitable-business-scientific-publishing-bad-for-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