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线收听
本节目,请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
↓↓↓
阅读原文
纳粹德国曾于二战期间研制核武器,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不过,其中的种种细节还有许多谜团尚待解开。为此,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经过数年潜心研究,于2005年在德国推出《希特勒的“原子弹”》一书
,
不仅解析了德国战时核计划的来龙去脉,还根据解密的历史资料得出了一系列颇具颠覆性的结论。
那么,德国在二战前究竟是否研制出了核武器?第一个试爆核武器的国家究竟是美国还是德国?如果德国真的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为何没有在二战结束前批量生产出来,以扭转战局呢?本期军史解密,李涵为您讲述:究竟是谁,试爆了第一颗核弹?

1938年圣诞节前夕,奥托·哈恩教授在德国柏林达勒姆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完成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他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结果惊异地发现,铀原子核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破碎”,成为不再是铀的两部分,这就是原子裂变现象。随后,人们意识到,在原子裂变过程中蕴藏着惊人的破坏力。
1939年1月6日,奥托·哈恩将其系列实验结果发表,立刻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3个月后,汉堡大学教授保罗·哈特克上书第三帝国军事部,提出关于开发核爆炸物的可行性问题,他说:“第一个利用这种核爆炸物的国家,将拥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
就军方而言,核裂变蕴含的重要性可谓非同一般,首先被推到前台的是主持德国陆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研发与制造的机构
-
陆军军械局。此时,担任陆军军械局研究处处长的是物理学家埃里希·舒曼。
1939年6月中旬,舒曼的上级卡尔·贝克尔将军召集了一次会议。贝克尔此前阅读过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文中做出了如下假设:“体积为1立方米的铀金属氧化物内部所聚集的能量,足以将体积为1立方千米
-
总重量为10万吨的水抬升至2.7万米的高度。”
这正是贝克尔感兴趣的。他指示舒曼等人,立即着手集结一个核物理研究团队,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征兵。没过几天,埃里希·巴格就接到了军械局派发的征兵令。这位年轻人是理论物理学巨匠维尔纳·海森堡的助手,刚获得博士学位,他被要求向舒曼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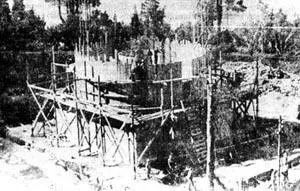
纳粹在建的核试验室
德国人选择的研究途径,有别于日后美国人和苏联人所走的道路。有关“铀项目”的研究工作,是通过分属19个不同机构的上百名科学家展开的。同位素分离和反应堆建造是最初的两项任务,它们被置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关键课题名下,其研究成果引导“铀项目”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建造生产能源的设备和制造核炸弹所需的原材料。
纳粹德国陆军、海军和空军也各有部署,三军分别拥有技术资源,在任务分配方面也明显涉及核物理学领域。军方研究小组定位明确,与一般的学术研究完全不发生横向联系。德国军方的期望是:开发出新型爆炸物和小型核反应堆。
那么,党卫队拥有独立的核物理研究小组吗?最初当然是没有的。后来,在野心的驱使下,纳粹党卫队也迈入了核物理研究行列。党卫队是仰仗其至高无上的特权而介入该领域的,他们想在社会各个阶层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知识分子被招募加入这个组织并被赋予“特殊使命”,在产业界、军界和科技界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与美苏两国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异,在纳粹德国,没有形成集中于某个特定区域的大规模综合性核计划,形形色色的研究小组像撒胡椒面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处。这种局面给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困难,但对保密而言却益处多多。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披露,二战最后阶段的
1944
年
10
月
-1945
年
3
月,纳粹德国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岛屿和中东部图林根地区,竟先后进行过三次核武器试爆,科学家们使用相对简易的方法成功触发了核反应。卡尔施和彼得曼通过研究分析二战时和战后已公开资料、查阅近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对依然在世的几位当年事件目击者和亲历者采访,以及邀请专业人士到
“疑似”遗址现场进行物理勘测和化学检测,最后在通过上述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就这个数十年来始终为一层神秘面纱所遮盖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关于
1944
年
10
月在德国北方波罗的海沿岸的吕根岛
-
或邻近某个小岛的“炸弹”测试问题,有一些目击者的采访证词和观测机驾驶员的审讯记录作为研究素材。同时,一位意大利老人的证词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他就是前意大利军事记者路易吉·罗梅尔萨,或许他是当时尚在人世的德国秘密核武器试验的惟一见证者。
罗梅尔萨
1944
年时担任意大利《晚邮报》战地通讯员,在接受彼得曼采访时,这位老者言之凿凿地表示曾亲临“北方测试”现场,目睹了核爆炸对波罗的海吕根岛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用罗梅尔萨的话说,这次“现场观摩”任务是墨索里尼在
1944
年
10
月
1
日
亲自向他布置并出具“推荐信”的,因为意大利领袖感到,有必要派个人去,对德国已拥有“可以将伦敦夷为平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华丽宣传辞藻”进行验证,于是罗梅尔萨便在
1944
年
10
月
12
日早晨
被邀请到北方某个小岛现场观看“炸弹”试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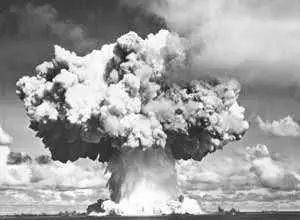
战后,罗梅尔萨将自己所见到的场景重复了多次,
20
世纪
50
年代还接受过几家杂志采访。可是那些倾听过他绘声绘色描述的人,大部分都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罗梅尔萨始终坚称,他所目睹的就是一次被称为“裂解炸弹”的爆炸物测试!因为当时还没有“原子弹”这个称谓。
关于所谓“北方测试”描述的另一份资料,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
9
航空队军事情报处情报官对德国空军军官鲁道夫·岑塞尔的讯问记录,时间是战争结束不久的
1945
年
8
月
19
日
。这份标题为《原子弹与德国人:调查、研究、开发和实际使用》的讯问记录,是关于德国“核武器测试”的更具重要价值的文献。岑塞尔向美国人交代了
1944
年
10
月间一次观测飞行的始末,并用生动语言描述了他所见到的“蘑菇云景观”,其中关于爆炸后出现的“极强光亮斑点、压力波、色彩不断变幻的蘑菇云和强烈电波干扰”等,与原子爆炸物测试后生成的典型环境相吻合。
应该引起人注意的是“岑塞尔讯问记录”的完成日期,是
1945
年
8
月
19
日
。而公认的第一个将原子弹爆炸过程公开报道的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但他的文章见诸报端的时间已经是近一个月后的
1945
年
9
月
9
日了。

经过数年调查考证,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认为,纳粹德国投降前两个月,在图林根地区的奥尔德鲁夫进行了两次核武器测试,时间分别是
1945
年
3
月
3
日晚
和
3
月
12
日
左右。其中第一次测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第二次则因爆炸当量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在图林根地区测试的这两件核武器,比同年
7
月
16
日
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上试爆的原子弹,在时间上要提前好几个月。
1945
年初春时节,纳粹德国俨然像一个“被夹在钳子里的胡桃”。英美盟军已跨过德国西部天然屏障莱茵河,苏联红军则在广阔战线上穿越波兰国土,饮马柏林以东的奥德河畔。鉴于战场不断向德国腹地压缩,“铀项目”重要机构和人员逐步从大城市疏散转移到相对偏僻的小城镇。格拉赫命令迪布纳撤离戈托夫,陆军研究小组科学家携带贵重原材料、实验设备和技术档案前往施塔特伊尔姆再安置。在动荡不定的迁徙过程中,德国研究人员坚持工作,其成果很可能就包括日后在奥尔德鲁夫引爆的被认为是“原子弹”的武器。
就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而言,
1945
年
3
月
3
日
的“图林根测试”应该具有指标性意义,除了希姆莱前军事副官格罗特曼在
2002
年接受采访时证实此事外,还有两名当年事件目击者克莱尔·维尔纳和海因茨·瓦克斯穆特的口述和证言。
2005
年,坐落于测试发生地不远处瓦森堡城堡的女主人克莱尔·维尔纳在回忆
60
年前那个晚间的场景时称:当时看见“一道极为炫目、辉煌耀眼的闪光,将周围景物照得如同白昼”。在她的记忆里,“烟柱迅速膨胀,很快就变得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爆炸发生的瞬间,甚至可以“通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来阅读报纸。

海因茨·瓦克斯穆特本来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后来被派到测试场充当劳工。战后,东德国家安全部特工对他进行了讯问,据他陈述,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他被分派的任务是负责清理和焚烧试验受害者的尸体。按瓦克斯穆特的说法,这些死者应该是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战俘或囚犯。另据一位名叫伯恩哈德·劳贝尔的波兰医生于
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称,战时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囚犯,包括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苏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此外还有部分苏军战俘。可以认为,“图林根测试”的执行者将这些人驱赶到试爆现场,目的是确定核爆炸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因此,奥尔德鲁夫的遇难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批核武器受害者。
关于“图林根测试”,另一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是苏军总参侦察总局的内部报告,其中有对爆炸效果的描述和爆炸物结构的推断。原件现存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在俄罗斯学者列昂·里亚别夫所编《苏联的原子计划,
1938
~
1945
》中有对其内容的引述。
事件发生若干年后被整理成文字的目击者证词,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难免存在记忆模糊和可能误读,但重要的是陈述中心要点是真实可信的。“格外炫目耀眼的闪光”符合核武器试验的指标性特征,发生在














